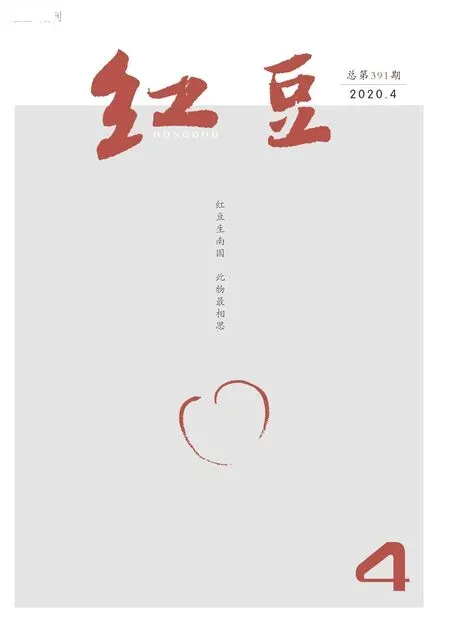南方韻致、幽微細節與命運困厄的交織
余思
閱讀秦汝璧的小說需要大段安靜時光,正如黃賓堂所言:“讀她的小說,需要靜心。”秦汝璧在創作談中多次提到自己的寫作狀態是“慢吞吞地寫著”。事實上,這位青年作家在文壇嶄露頭角的速度并不“慢”。秦汝璧一九九一年出生于江蘇高郵,二十五歲時于《鐘山》頭條發表處女作,隨即她入選二〇二〇年江蘇省“紫金文化人才培養工程”文化優青,成為江蘇省作家協會第十二屆簽約作家,結集出版的小說集《史詩》廣受好評。小說《華燈》于二〇二〇年獲“《鐘山》之星”文學獎年度青年佳作獎。
小說《華燈》是秦汝璧確立自己獨特文風和氣質的作品。她的語言和情感在《華燈》中展現出“秦汝璧式”的精微、纖細與優雅,小說因此散發著濃郁的南方韻致。小說里她寫了深圳這座城市,舒緩的敘述與這座特區城市飛快的發展節奏完全背離,徐徐展開的正是人物細膩復雜的情感褶皺。
《華燈》中的“深漂”青年崔吉甫在父親離世后陷入了無奈的分離和困頓的堅守,小說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憂郁感傷氣質。在《華燈》中,她寫崔吉甫深陷在父親離世的痛苦中,下班后跟著人潮去了食堂,路過一段被廢棄的路。她將這段路形容為“荒煙蔓草”與“長陂洼塘”的結合,形容傍晚近郊天空是“纖翳的晚意”,路燈背面是“青黎的幽影”,又如她形容許久不見面的熟人為“故人堆里的水蜻蜓,打著沙翅到處只停歇一陣”。她將陸梁娥去借錢時那個冬天傍晚的夕陽,形容為“天邊先抹了一層淡淡的蝦子紅,再上面是一層煙白,一層雨過天晴”,如“清冷冷的水里雨花石上的水紋”。秦汝璧大量使用蘊含古典意味的修辭去書寫現代故事,用一種早已陌生化的方言古語來書寫出現代都市的沉重苦難。
《華燈》的故事情節簡單,但所寫的是人世間最為悲痛的事——親人即將離世卻無法見面。作者用古典主義寫法淡淡地訴說故事,全文不見一處濃烈的情緒沖突,也沒有曲折離奇的情節。作者始終沒有進行任何強情節敘事,她似乎東寫一筆,西寫一筆,人物的出場和離開也呈現出跳躍而離散的狀態,人物情感推進則呈現為一種黏稠和彌漫性的淋漓。作者書寫這些并不連貫也不完整的碎片,由此拼湊出“崔家”在生離死別面前的種種困頓。
這種用古典意蘊書寫現代性困苦的反差構成了秦汝璧小說的美學特質。
秦汝璧的人物白描功底很好,正如黃賓堂在小說集的序言中對她的文字所評述的,她在瑣碎描述中傳遞著“刻刀般準確”。在《華燈》中,她數次用白描的手法刻畫不同人物的手,用以凸顯人物的角色性格。
對三雙不同的手的刻畫,完成了對《華燈》中最主要的三個人物角色的塑造,寥寥幾筆的白描,描繪出鮮明而獨特的人物圖景。她沒有直接描寫三個人的臉,而是借由對這三雙手的細致描摹,令讀者感知三個人物不同的內心世界,這也顯露出作者難能可貴的文學才氣與想象力。如她寫到崔吉甫在深圳闖蕩時無比艱辛的狀態,崔吉甫作為北方人在深圳水土不服,“瘦損大半”的手腕是那樣“微骨蒼冷”。他初到深圳卻聽聞父親離世,困于現實而放棄奔喪。在這命運的捉弄中,秦汝璧書寫了極為微妙的細節:崔吉甫害怕被老板辭退,他的手不小心被鐵框劃破,手指頭有“溫熱的紅粉可愛的一點心血”,而他“把破指埋在拳頭里止血”,以這一點手指被扎破流的血來映照人物內心的無奈與蒼涼。
第二雙手來自崔吉甫的妻子陸梁娥。她寫到陸梁娥在故鄉一個人拉扯孩子操持家務時,坐在窗戶邊撿菜葉子,她的手是“凄清的白骨皚皚”“手上沾滿了清濕的泥”。秦汝璧通過這雙手書寫留守妻子內心如坐寒窯的寡婦般的悲哀。
第三雙手來自袁傳芝。她是獨自帶著孩子在深圳打拼的女人,她沒有涂指甲油,手是天生的珠圓紅潤,冬天起的凍瘡印,到了夏天“深紫色已褪成淡粉紅”。她借著這凍瘡去寫袁傳芝的性格,由此寫出這個女人對崔吉甫隱約的誘惑,是“嬌怯的虛浮還在,一碰就破似的”。這些生動的比喻和白描寫法無不透露著作者敏銳幽微觀察生活的能力,這也是秦汝璧的小說在擺脫了“故事性”之后仍對讀者分外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在父親去世的長夜悲痛中,崔吉甫窮到連奔喪都捉襟見肘,妻子陸梁娥計劃讓他剪一綹頭發寄回去,她代他燒成灰寄托哀思。但命運的諷刺在于崔吉甫為了適應深圳的炎熱,前一日才剛剛把頭發推成板寸。連一縷頭發都無法歸鄉,他只好剪了指甲寄回去。這一細節將人物背井離鄉的苦厄充分表達出來。談到父親的死,崔吉甫想的是家里連招待吊唁者的像樣的茶具都沒有,沙發假皮套裂開了許多口子。于是他想到,“回去第一件要緊事就是買套陶瓷茶具,再做件沙發套子”,這是貧困生活對一個男人精神和尊嚴的雙重消磨,崔吉甫來不及消化父親的去世帶來的痛苦和絕望,這些生活的沉重表現在作者信手拈來的碎片真實中。
在這貧困的生活中,一切原本應有的倫理重負被苦難所消解。小說寫到崔吉甫與兩個女人的碰撞,在十方菜館里他看到那個低頭打算盤的女服務員袁傳芝。這讓他想起陸梁娥曾經談起過袁傳芝,她不動聲色,如同談一個遙遠的傳說。“四張嘴一張,四雙手一攤,八只眼睛就望著你了”,這是故鄉生活的壓迫,彌漫著麻木和掙扎。小說抽絲剝繭般展示了物質生活困境對人的壓迫。上夜班時,寂寥悲哀的崔吉甫仿佛出現了幻覺,看到“一根長頭發絲落下來不知道飄落哪里去了”。妻子陸梁娥看到同村的崔長海賺錢風光,竭盡全力將丈夫推向深圳,為此他錯過見親生父親死前的最后一面。陸梁娥親手推走了丈夫, 卻又意識到了情感危機,擔心丈夫會在袁傳芝身上花掉血汗錢,她想象中“他口中的深圳女人是這樣的恐怖”。
崔吉甫在深圳打拼多年,在公司中終于成了“老資格”,家里也終于有了可以喝茶的正宗紫砂壺。舍不得路費,害怕丟失工作,令崔吉甫缺席了父親的葬禮,而這些年來他缺失的何止這些?崔吉甫把錢帶回家時,陸梁娥穿著大棉襖坐著數錢,那幸福和滿足的感覺如“佛龕里踏著祥云的粉彩瓷招財男童女童一樣顴骨上抹了兩團紅粉”。陸梁娥在故鄉的寂寞和困頓中學會了打麻將,甚至打著牌因為“長久地盯梢鍋里的牌,漸漸得了近視眼”。她會忽地笑起來對丈夫說:“你那位深圳的女人不是替你生了個兒子嗎?怎么沒跟你回來?”崔吉甫也不反駁,仿佛聽了一個全新的笑話,反問與他疏遠多年的女兒:“真有了個弟弟,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沒有人回答這個玩笑,這使得崔吉甫隱約意識到自己缺失的不僅是父親的葬禮,還有兒女的成長。這語言的反諷碎片亦是對倫理的麻木。
這苦厄如此真實,這麻木也如此真實。作者借著《華燈》去書寫和表達她對城市底層民眾真實生活的探尋,正如在《華燈》結尾,秦汝璧直抒胸臆地感慨:“普通人的幸福大抵如此,否則連眼前的幸福都沒有了。”
在《鐘山》雜志于南京舉辦的第四屆全國青年作家筆會上,秦汝璧在總結自己的寫作觀時,表達了她對故事真實的看法。她說:“我總想著有一天我們這個地球毀滅了,無數的紙張在這個太空里飛散,由新的種類拾去的只言片語,我希望那是人類的一點真實。真實里的人那才是人,真實里的不合理與異態被揭穿,才有光與美的出現。”
責任編輯? ?藍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