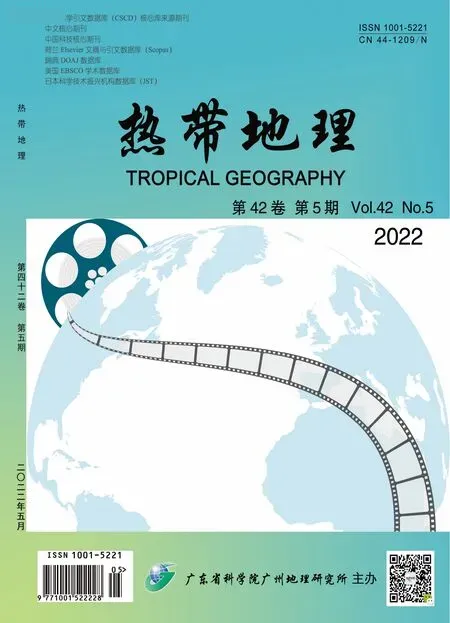基于企業動態的珠三角產業空間演化特征與路徑
黃怡菲,周素紅
(a.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b. 廣東省公共安全與災害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廣州 510275)
產業演化、轉型、升級是區域發展至關重要的一環(Martin et al.,2006;Martin,2010),厘清產業演化的特征和路徑能為區域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戰略參考。2010年國家“十二五”規劃明確強調進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地區產業在以宏觀經濟的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為目標的政策導向下,尤其在全球經濟環境變化背景下,其演化過程形成了怎樣的空間模式、路徑和規律?開展相關研究可為管理者因地施策提供有益參考。
珠三角地區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最早的地區之一。改革開放之初的“三來一補”“前店后廠”等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在給地區產業發展注入活力的同時,也存在發展后勁不足的問題(周春山等,2017)。近10年來,珠三角的產業進入快速調整時期,產業空間格局也發生改變,形成區域內產業衰退和增長現象并存的局面(葉玉瑤,2016)。即便如此,其在2015-2020年生產總值仍保持6.3%的年均增速(廣東省統計局,2021),人均GDP 仍遠超全國平均水平。因此,將珠三角地區作為典型案例,研究其產業演化的空間特征、過程與規律,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普適性。
產業空間的特征和影響因素是經濟地理學長期關注的重點。早期相關研究往往基于統計數據,刻畫不同空間統計單元中的產業規模、結構及其變化,分析產業政策以及資源稟賦、區位、交通成本、土地、技術、勞動力等不同市場經濟要素的作用,難以從過程上深入刻畫產業演化在空間中的路徑和規律。20 世紀90 年代在西方興起的演化經濟地理學(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EEG)為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工具。演化經濟地理學吸收了廣義達爾文主義、路徑依賴理論和復雜性理論,強調基于企業行為學和過程思維研究區域產業演化,涌現了一批如產業多樣性、產業動態、產業關聯性等概念的研究(Neffke et al.,2011;Boschma,2015; Castaldi et al., 2015; Frenken et al., 2015)。相關思潮也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并將其應用在針對中國的產業研究中(劉志高等,2006;賀燦飛,2018;賀燦飛等,2020),如在微觀上關注企業及其關系網絡的演化(賀燦飛等,2016;楊佳意等,2017;李珊等,2021),在中觀上關注產業集群演化和區域發展(劉志高等,2011,2016;顏燕等,2017),在宏觀上重視影響經濟發展的制度以及多元主體、跨尺度的關系空間(劉志高等,2016;蘇燦等,2021)。然而,上述研究較少從微區位的尺度揭示企業進入、退出和演替等行為,再結合中觀、宏觀尺度的分析以全面地探究區域的產業空間演化特征和產業演化路徑。此外,針對演化經濟地理學過于依賴內生解釋的理論缺陷,新近研究重新重視制度、政策等外生因素的作用,這一點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尤其值得關注,學界正呼喚構建一種“非西方”背景下的演化經濟地理研究框架(Has‐sink,2017;Zhu et al.,2019)。
在揭示產業空間演化的機制方面,國際演化經濟地理學界關于路徑依賴、路徑創造、區域韌性等經典命題的研究仍占多數(Fornahl et al., 2012;Holm et al., 2015; Grillitsch et al., 2020)。近年來,隨著“關系轉向”,中國深度參與全球生產網絡、嵌入全球價值鏈后進行的新一輪產業升級,以及生產網絡中的產業關聯成為新興研究熱點。在產業升級相關研究中,已有文獻大部分從經濟學角度出發,歸納出產業結構高度化、加工程度高度化、價值鏈高度化等3 種產業升級演化模式(朱衛平等,2011),并分析產業升級路徑及其對區域產業演化的效應(張輝,2004;劉逸等,2019),但較少從地理學角度研究產業升級對于產業空間演化的作用。在產業關聯研究方面,實證表明產業關聯及產業基礎對區域產業演化具有重要影響,細化為產業衍生、路徑分叉、路徑更新等過程機制(Coenen et al.,2015;李偉等,2021),在方法上一般通過所使用資源相似性分析、產品共存分析、產業網絡分析對產業關聯性進行測度(郭琪等,2018)。如Nef‐fke 等(2011)分析了瑞典70 個地區從1969—2002年的產業演化,發現瑞典產業演化有強烈的路徑依賴性,與區域既存產業具有更高技術關聯性的產業更有可能進入該區域,而關聯性邊緣化的產業更易于退出該區域。Boschma等(2015)發現制度對產業多樣化進程的方向存在影響,在協調的市場經濟中,關聯性對產業多樣化的驅動力更強,而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更多與原有產業關聯性不強的新產業可能會進入到該地區中。關聯性也會促使一些特定產業類型在地理空間上發生共同聚集(co-agglom‐eration)(Dumais et al., 2002; Duranton et al., 2005,2008; Briant et al., 2010; Ellison et al., 2010),于斌斌(2014)、于瀚辰(2019)等探究了制造業和一般服務業的企業選址以及二者之間的互動、集聚關系,Jacobs(2014)、Ke(2014)等則關注生產性服務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共同集聚關系。總體上,產業升級和產業關聯從內源和外驅兩方面共同作用于區域產業演化及其空間效應(Boschma et al.,2018)。
上述研究從多個不同的尺度和視角,探討區域產業空間演化問題,但因缺乏長時序、大范圍、全行業的企業微觀數據,已有研究未能從產業空間演化的主體——企業出發,透過其進入、退出等微觀動態(史進等,2014;朱晟君等,2020),超越某一特定集群或行業,研究整體區域產業空間中宏觀演化效應問題,并結合產業升級路徑和企業間的空間關聯探究產業演化的機理。隨著數據開放平臺的建設和大數據的普及,電子導航地圖興趣點數據POI(Point of Interest)、企業工商登記數據等應用逐漸成熟,為基于微觀企業數據研究產業演化提供了數據基礎(Li et al., 2017;李漢青 等,2018)。其中,POI數據空間粒度細、空間完整度高、靈活性強,突破了以往統計數據的空間不連續性和經濟數據可獲取性問題,是探索連續空間內企業行為的有力工具。研究企業行為的宏觀統計效應,可彌補以往研究就企業論企業、就區域論區域的缺陷,有利于兼顧微觀行為與總體效應的關系。
基于此,本文以POI數據為基礎,從企業的進入、退出、演替3方面動態著手,分析珠三角產業演化的空間特征,通過Apriori算法挖掘產業間的空間關聯規律,驗證產業升級和產業關聯2種動力對珠三角產業空間演化的作用,以期為科學地進行產業規劃與空間布局提供參考。
1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根據以下思路研究珠三角產業演化過程:1)首先,對企業POI點采用核密度估計法進行分析,揭示2010-2020年珠三角產業分布格局特征及其演化。其次,在統一坐標系下疊加2010 和2020年2個時間截面的POI點圖層,利用ArcGIS軟件的overlay 工具包分析同一空間點位(相同經緯度)上出現的POI點新增、消失以及所屬行業類型變更情況,分別對應進入、退出、演替的企業。例如,2010 年在某空間點位上不存在任何企業,而2020年該點位出現了一家A行業企業,即為該行業企業的進入;2010年在某空間點位上存在一家A行業企業,而2020年該點位無任何企業,則為該行業企業的退出;2010年在某空間點位上存在一家A行業企業,而2020年在該同一點位上的是一家B行業企業,則為A和B行業企業的演替。接著,運用局域Getis-OrdG指數法分析企業進入、退出、演替的熱點地帶,揭示三類產業演化趨勢在空間上的集聚特征。2)提取同一點位上企業的類型演化路徑,即該地點的產業在演替前后的類型變化,并對演化路徑進行分類統計,揭示產業演化升級趨勢。3)通過Apriori數據挖掘方法探索企業間的空間關聯規則,并基于產業升級和產業關聯規律嘗試解釋產業演化路徑。
1.2 研究區域與數據來源
研究區域為珠三角九市,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和肇慶。本文基于項目組采購的2010 和2020 年廣東省電子地圖數據,提取珠三角范圍內各地級市與產業相關的興趣點(POI)數據作為數據源。依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11)(國家統計局,2011)選擇第二產業中具有代表性的制造業;第三產業中的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文化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進行研究(孫曉華等,2012),共包含15 個小類部門,其對應的POI 類型見表1。為了保證名稱與真實數據的一致性,沿用原始數據的命名規則。

表1 珠三角產業POI分類統計Table 1 PRD Industrial POI statistics 個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估計法 采用不同年份各企業點的核密度分布呈現產業空間格局和演化特征(薛東前等,2011;張珣等,2013)。核密度是一種不受柵格大小和位置影響的概率密度估計方法(Silver‐man,1986)。以每個企業POI 點的位置為中心,統計落在設定搜索半徑內的企業POI點數量,并按照核函數計算每個企業POI點的密度權重,權重值符合距離衰減定律,距離搜索區域中心越近,權重越大。按此方法計算每個企業POI點的權重和,得出整個珠三角的企業密度分布(王法輝,2009)。
1.3.2 局域Getis-OrdG指數法 采用局域Getis-OrdG指數法識別企業進入、退出、演替行為的熱點區域。該方法是一種探索局部空間相關的方法(Getis et al.,1992),通過計算要素及其設定鄰域范圍內的要素總和與所有要素的總和來比較衡量該要素的局部空間集聚水平(陳蔚珊等,2016),可以識別空間要素是否存在高值聚類或低值聚類。相比同樣用于分析空間自相關的局部Moran'sI指數,局域Getis-OrdG指數更能準確地探測到聚集區域(張松林等,2007)。在實際研究中,通常使用標準化后的Z(G)值,便于解釋和比較(王釗等,2015)。為避免各地POI數據總量差異造成的誤差,分析前將每個網格內發生進入、退出、演替的POI數量除以2010年該網格POI數據總數,進行標準化處理,以反映地區間的相對差異。
1.3.3 關聯規則數據挖掘Apriori 算法 產業集聚是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普遍現象,在微觀上表現為不同的企業因為技術關聯、業務往來、共享市場、共享知識等原因呈現臨近分布與協同區位(colocation)(馮鵬飛 等,2019;陳嘉 等,2021),這種共同聚集現象體現了企業間的空間關聯(陳曦等,2015;關偉等,2019),而通過空間關聯關系的客觀變化能探究產業發展趨勢的轉變,穩定的空間關聯規律也能指導產業科學布局。
Apriori算法是關聯規則數據挖掘中比較常用的算法之一(陸麗娜等,2000),結合一定的空間位置約束能夠用于挖掘企業間的空間關聯。該算法通過逐層迭代、向下封閉檢驗思想搜索頻繁項集,并計算比較頻繁項集里各要素共同出現的概率生成關聯規則。將其用于企業空間關聯研究,即可以識別出頻繁發生臨近分布的企業類型,計算它們的空間關聯程度,通過對比不同時間截面的關聯程度,衡量關聯的穩定性。
Apriori算法計算流程為:首先,將珠三角地區劃分為214 870 個500 m×500 m 的網格,將落于每個單元格的企業的類型記為一個集合,得到27 966個有企業存在的有效樣本網格,形成由如{金融保險,電子儀器,機械零件,化工冶煉}集合組成的數據庫,共有15 種不同的元素,對應15 種產業類型。
其次,在數據庫輸入算法,計算15種產業類型兩兩組合的支持度(Support),用于衡量產業共現的頻繁度,其表達式為(廖偉華等,2017):

式中:Support(X,Y)為支持度;P(X,Y)為集合中同時含有X和Y的概率,一般設置一個最小閾值(Minimum Support)來剔除無意義的空間位置關聯干擾,保留支持度高的頻繁共現產業集群。組合中元素越多,支持度越低。為了不遺漏可能的頻繁產業組合,設定最小支持度為10%,滿足最小支持度方可認定為存在空間關聯。如在本研究中Support{電子儀器,機械零件}指同時包含電子儀器、機械零件的產業空間共現組合在數據庫所有集合中出現的頻率,若Support{電子儀器,機械零件}>10%,則滿足最小支持度條件,被記為頻繁共現產業集群。比較同一產業集群2010 和2020 年支持度,可以衡量其關聯程度的穩定性,若支持度增加,說明該類集群關聯增強、保持穩定發展甚至增長;若支持度減弱,說明該類集群關聯減弱、發展不甚穩定。
再次,基于頻繁二元組合迭代搜索所有滿足最小支持度的頻繁組合,也即所有具有空間關聯的企業類型組合,如{電子儀器,機械零件,金融保險}。搜索過程滿足“頻繁集合的子集必為頻繁集合,非頻繁集合的超集一定是非頻繁集合”的算法性質。
最后,在每個空間頻繁組合里尋找關聯規則,計算每個空間頻繁組合的非空子集的置信度。如{電子儀器,機械零件,金融保險}被認定為空間頻繁組合,則代表電子儀器產業、機械零件產業、金融保險產業之間存在空間關聯,若要衡量電子儀器產業和金融保險產業之間的關聯程度,則需計算{電子儀器→金融保險}的置信度Confidence,其表達式為(廖偉華等,2017):

式中:Confidence(X→Y)為置信度;P(Y|X)為在關聯規則先決條件X發生的條件下,關聯結果Y發生的概率;P(X)為先決條件Y的發生概率。例如,本研究中Confidence(電子儀器→金融保險)指電子儀器產業出現的情況下,在同一空間內也出現金融保險產業的條件概率。置信度是生成空間強關聯規則的第二個門檻,同樣需要設置一個最小閾值(Minimum Confidence)來繼續篩選,滿足算法設定的置信度閾值才可認為兩個元素之間空間關聯性顯著,本文按照常用規則設定最小置信度為65%(廖偉華等,2017),比較同一對關聯規則在2010和2020年顯著性、置信度的變化,衡量其關聯程度的穩定性。
2 基于企業動態的珠三角產業演化特征
2.1 產業空間分布格局的演化
對2010-2020年珠三角產業POI進行核密度分析(圖1),發現第二、第三產業主要集中在核心圈的5個城市,包括廣州、佛山、深圳、東莞和中山,產業活動主要集聚在中心城市的核心區,呈現明顯的“核心—邊緣”分布模式,近10年的發展進一步強化了穩定的廣深雙核心和廣—深(廣州經東莞至深圳)與廣—珠(廣州經中山至珠海)東西雙走廊的格局。在演化方向上,珠三角產業格局在圍繞核心擴散的基礎上,呈現重心東移的趨勢,東部的深圳、惠州增長明顯。

圖1 2010-2020年珠三角主要產業空間格局對比Fig.1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industries in PRD during 2010-2020
2.2 基于企業進入、退出、演替的產業空間演化特征
產業空間的演化在微觀上由進入、退出、演替三類企業動態組成,運用熱點分析方法識別珠三角產業上述三類企業動態的熱點區域分布,發現各自的集聚特征具有顯著區別。企業的進入行為主要集聚在珠三角地區經濟較發達城市的核心地帶,退出行為主要集聚在后發地區和昔日專業鎮轉型地帶,演替行為主要集聚在發展基礎深厚的傳統中心區。
具體地,企業進入方面(圖2-a),熱點分布在廣州、深圳、佛山、中山和江門等市的核心區以及深圳、惠州和珠海市的新開發區,如珠海橫琴新區,以上地區是珠三角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節點和戰略平臺;而冷點分布在佛山三水區、南海區、順德區以及東莞北部,廣州花都區。企業退出方面(圖2-b),熱點分布在東莞市、佛山南海區和順德區、中山市北部這些專業鎮地帶,以及江門市的后發地區如恩平市、臺山市等,發生不同程度的城市收縮現象(李郇等,2015;杜志威等,2018),企業退出熱點地區與企業進入冷點區分布情況相符;而企業退出的冷點位于廣州、深圳、中山、珠海的中心城區,也與企業進入熱點區的特征相符。企業演替方面(圖2-c),熱點主要分布在佛山、廣州、中山等市的中心城區,這些地區較早得到發展,是傳統的制造業中心、商貿中心,正處于存量更新過程;而冷點分布在東莞、中山、江門、惠州發展較為穩定的中心城區城區,以及深圳部分快速發展的新區。

圖2 2010—2020年珠三角企業進入(a)、退出(b)、演替(c)冷熱點分布Fig.2 Distribution of hotspots in entry(a),exit(b)and succession(c)of enterprises in PRD from 2010 to 2020
珠三角的產業演化特征在地理區位上呈現顯著分異,廣深兩極持續增長,而佛山和東莞同作為經濟發達地帶出現比較多轉型期傳統企業退出等局部收縮現象(杜志威 等,2017,2019;林耿 等,2020),惠州、珠海、江門等非核心圈層城市中涌現出企業更替、企業進入等增長,這些特征與對珠三角慣常認知中的極化現象、核心—邊緣模式有所不同。為探究其規律,嘗試從產業升級和產業關聯2個維度進行剖析。
3 基于企業動態的珠三角產業演化路徑
3.1 基于產業升級的演化路徑
區域在發展初期憑借特定的市場要素條件,如資源稟賦、外資條件或勞動力等,抓住政策制度、全球化帶來的機會窗口,形成初步的產業結構基礎。地區在原有產業基礎上,低附加值產業因不斷被市場淘汰而退出,高附加值產業得到發展并不斷地擠出低附加值產業,體現為低端產業聚集區出現企業退出,適合高端產業發展的集聚區出現企業進入,部分區位出現低附加值產業被高附加值產業替代等現象,形成產業升級的空間演化路徑(圖3)。這種循著價值鏈從低端到高端進行產業升級的規律在珠三角地區的企業空間動態中得到體現:企業的進入、退出方面,進入的企業中以金融保險業居多,占所有新進企業數量的1/4,遠遠超過其他產業(圖4-a),而退出的企業主要是電信通訊、服裝紡印、電子儀器、化工冶煉業(圖4-b),這與產業POI 分類統計(見表1)中顯示的珠三角2010-2020年各類企業數量變化趨勢相似,金融保險業企業數量接近翻倍,服裝紡印、電信通訊、化工冶煉、電子儀器、食品飲品、玩具禮品行業的企業數量減少。企業演替方面,通過統計每種路徑的數量并提取占比最大的前20條(合計占比>70%)形成三類產業類型演替路徑(圖4-c),可以發現,最主要的一類是制造業向生產性服務業、信息服務業演替,其次是制造業內不同部門循著價值鏈向更高方向轉化,第三類是服務業內不同部門的相互演替。這三類路徑總體上依然遵循產業升級規律。具體地,在制造業向服務業演替的路徑中,大部分制造業演替為網絡科技產業,電子儀器制造業和化工冶煉業也向金融服務業和商務與法務服務業演替;在制造業內部沿著價值鏈進行的演替中,呈現服裝紡印業向網絡科技、化工冶煉業演替,電子儀器、化工冶煉業向機械零件業演替的漸進升級路徑;在服務業的演替中,電信通訊企業向網絡科技企業演化,金融保險業與商務與法務服務業相互演化,網絡科技業也向商務與法務服務、企業管理與咨詢產業演化。總體上,珠三角產業演化遵循從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污染型產業向高附加值的技術或知識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的規律。

圖3 珠三角產業演化動力規律Fig.3 Driving forces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in PRD

圖4 2010—2020年珠三角各類企業進入(a)、退出(b)、演替(c)數量統計Fig.4 Statistics of entry(a),exit(b)and succession(c)of various enterprises in PRD from 2010 to 2020
珠三角快速工業化形成的早期產業空間布局,受產業升級過程的影響發生進一步的演化。在快速工業化時期,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污染型產業由于所需土地、勞動力等資源多但承租能力弱,多分布于地價和用工成本更低的珠三角外圍地區,形成一批專業鎮,而高附加值的技術或知識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由于對高技能水平勞動力以及完善的產業生態系統需求較高,且承租能力更強,多分布于珠三角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高的中心城市。低附加值產業方面,服裝紡印業、食品飲品、玩具禮品企業集聚分布在外圍的江門市開平縣、恩平縣,中山市大涌鎮、黃圃鎮、小欖鎮;電子儀器加工制造企業集聚分布于東莞市長安鎮等專業鎮區域;化工冶煉企業集聚分布在佛山市南海區、順德區。高附加值產業方面,網絡科技、金融保險等第三產業分布在珠三角各城市的中心城區,尤其是廣州和深圳,機械零件制造等高端制造業分布在佛山順德區以及深圳、惠州的新工業園區。然而,新的轉型發展階段促使珠三角通過產業升級來保持增長動力,隨著產業升級過程所帶來的不同類型企業的進入、退出、演替,珠三角產業空間也自然地發生調整和演化。
產業升級的過程也映射在產業空間布局上,遵循一定的演化路徑。一方面,低附加值的服裝紡印、食品飲品、玩具禮品、電子儀器、化工冶煉產業被升級,所以其產業集聚區出現企業退出現象,使得對應的東莞市專業鎮、佛山南海區和順德區、中山市北部,以及外圍的江門市部分后發地區成為企業退出的熱點地區;另一方面,高附加值的金融保險、機械零件、網絡科技、商務與法務服務、企業管理與咨詢產業作為升級的趨勢所在,適于其發展的地區便會吸引大量企業進入,使得對應的廣州、深圳、佛山、中山和江門等市的中心城區以及惠州、珠海的新產業園區成為企業進入的熱點地區;此外,廣州、佛山、中山的中心城區雖作為適于高附加值產業發展的區位,但存在產業用地相對緊缺的狀況,因而在產業升級和地區更新過程中成為高附加值企業替代低附加值企業的演替熱點區。綜上所述,產業升級使不同類型的企業在不同地區出現進入、退出、演替現象,大量的微觀企業動態凝聚成綜合效應,從而影響整體的產業空間布局。因此,產業升級是珠三角產業空間演化的重要路徑。
3.2 基于產業關聯的演化路徑
日趨激烈的全球化市場競爭以及宏觀政策制度等因素促使地區進行產業的轉型升級,與此同時,作為演化的基本單位——企業經過長期的市場篩選,積累一套基于自身性質的生產交易邏輯,包括對所使用原材料資源、勞動力技能、生產技術、文化環境等方面的側重和偏好(見圖3)。當兩類產業的需求或偏好相近、一致或互補時,這兩類產業便產生了內在的產業關聯,一些產業可能因所需資源的一致或技術、功能的互補而在空間上呈現鄰近分布,以便開展業務聯系。產業關聯的客觀存在,使得某些產業之間的聯系自然地比另外一些產業更緊密,它們在技術、功能上互補互利,并且在相近的資源環境下共享外部經濟,因此關聯緊密的產業集群能發揮良好的協作效應,展示出更具韌性的發展潛力,也使得彼此之間的產業關聯穩固、強化。產業關聯穩固、強化的集群一方面在內部具有更完善的產業生態,另一方面對外能展示出更有前景的發展勢頭或品牌效應,因而能吸引更多企業進入該集群及其所在地區;反之,產業關聯不緊密、不穩定的集群因缺少協作和前景,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已不能帶來邊際效益遞增,導致集群發展難以持續,出現企業的退出,或演替為更益于構建產業鏈協作生態的企業來尋求集群的振興。不同地區的集群產業關聯強度、穩定性各異,導致不同地區的企業進入、退出、演替情況存在差異,在空間上逐漸呈現分異,最后對整體的產業空間產生一定程度的改變。
珠三角地區客觀地存在上述產業關聯規律。通過Apriori算法挖掘2010 和2020 年珠三角產業的空間關聯規則和頻繁共現集群,并對比2個時間截面的關聯強度來衡量產業關聯的穩定性,結果發現:珠三角的金融保險、機械零件制造、網絡科技、商務與法務服務業之間產業關聯緊密且歷經10 a依然穩定,甚至強化(表2),而服裝紡印、玩具禮品、電信通訊、化工冶煉之間的產業關聯不緊密、不穩定。頻繁共現的產業集群也顯示出一致的結果:從2010-2020年依然保持穩定或增強的共現狀態的集群呈現“制造業+服務業”的配置,多數由金融保險、機械零件、網絡科技、商務與法務服務業這些產業組成,而10 a后共現狀態減弱的集群呈現缺乏生產性服務業的制造業集群特征,主要由服裝紡印、金屬陶瓷、電信通訊、化工冶煉產業組成(表3)。

表2 2010-2020年珠三角產業關聯規則Table 2 Industrial Relatedness Laws in PRD in 2010-2020

表3 2010—2020年珠三角產業集群共現頻繁度Table 3 Co-Location Frequency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PRD during 2010-2020
這些不同的產業關聯狀態會影響集群內以及集群所在地企業的進入、退出、演替等動態,成為產業空間演化遵循的另一路徑。具體表現為產業關聯穩固、強化的集群吸引產業進入,反之,則出現產業退出,或演替為關系更穩固的集群。珠三角不同地區的集群生態各異,如前文所述,產業關聯穩定、強化的金融保險、機械零件制造、網絡科技、商務與法務服務業主要集聚分布在廣州、深圳、佛山等中心城市的中心城區,產業關聯不穩定的服裝紡印、玩具禮品制造、化工冶煉產業的集群主要分布在傳統專業鎮、工業園地帶,如東莞市、佛山市、中山市部分區域,以及缺少第三產業發展土壤的江門等珠三角外圍欠發達地區。因此,“制造業+服務業”集群所在地,或能夠提供“制造業+服務業”組合配置的地區,也即廣州、深圳、佛山等經濟發達城市的中心城區因提供了良好的集群協作生態和品牌效應,穩定的集群發展狀態吸引大量企業進入;而東莞、佛山、中山的專業鎮地帶以及江門外圍地區的制造業集群因長期缺乏生產性服務業的支撐,容易過度專業化或陷入“低端鎖定”,這類集群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競爭中無法維持長期的增長,其逐漸縮小規模、解體改造的過程即內部企業退出、演替的過程。
綜上所述,產業升級和產業關聯均通過影響微觀企業的進入、退出、演替等動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整體的產業空間布局,是珠三角產業空間演化的兩大重要路徑,形成珠三角內部各不相同的產業空間演化模式(圖5)。

圖5 珠三角產業演化模式Fig.5 The industrial evolution pattern in PRD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借助演化經濟地理學視角,通過分析進入、退出、演替3種企業動態,探測珠三角產業空間演化的熱點地區,并結合具體的產業價值鏈升級和產業關聯規則及關聯穩定性分析,揭示珠三角產業空間演化的產業升級、產業關聯兩大重要路徑,并總結珠三角地區產業空間演化的特征與模式。
珠三角地區在改革開放初期憑借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自下而上的鄉鎮企業發展以及全球化浪潮外資注入的優勢,形成初步的產業結構基礎。進入轉型優化期后,全球化市場競爭以及政策制度的管制與引導促進珠三角地區的產業升級,同時企業本身也遵循客觀的產業關聯規律來集聚布局,以實現企業和所屬產業集群的穩定發展。經過上述發展歷程,珠三角呈現廣-深雙核極化,廣佛深莞連綿化、發展重心東移與次核心城市產業顯著增長的總體產業演化格局。
在珠三角產業演化的空間特征方面:1)珠三角企業進入熱點區分布在廣州、深圳等經濟發達城市的核心區,以及惠州、珠海等城市的重要產業園區。以上地區集聚分布金融保險、機械零件、網絡科技、商務與法務服務、企業管理與咨詢等高附加值的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呈現“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信息服務業”的多元產業組合結構。2)珠三角企業退出熱點區分布在珠三角的傳統專業鎮、工業園地帶,如東莞、佛山、中山部分區域,以及江門的欠發達地區。以上地區集聚分布服裝紡印、食品飲品、玩具禮品、電子儀器、化工冶煉等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污染型產業,呈現單一的制造業專業化產業組合結構。3)珠三角企業演替熱點區分布在廣州、佛山、肇慶等城市發展成熟的舊城區。該區域的傳統產業更新為承租能力更強、效益更高的產業。
產業升級路徑作用下,珠三角產業演化呈現從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污染型產業向高附加值的技術或知識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的規律。因此珠三角經濟發達城市的中心城區因適于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而吸引大量企業進入,珠三角專業鎮地區和后發地區集聚的低附加值企業因被升級而退出,廣州、佛山的老城區因適于高附加值產業發展但缺少產業用地增量而成為企業演替升級熱點區。
產業關聯路徑作用下,珠三角產業演化中“制造業+服務業”集群具有穩定、強化的產業關聯性,發揮協作效應更具發展前景;缺乏生產性服務業的制造業集群產業關聯不緊密、不穩定,缺乏支撐而難以在競爭中維持先進。廣州、深圳、佛山等經濟發達城市的中心城區提供“制造業+服務業”集群發展的優質土壤而成為企業進入的熱點地區,東莞、佛山、中山的專業鎮地帶以及江門的外圍地區的制造業集群因缺乏生產性服務業支撐,集群發展落后導致企業退出。
4.2 討論
本文基于微觀企業動態視角研究整體區域產業空間中的宏觀演化效應問題,在企業動態的運用上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集群或行業的范圍,并在產業關聯分析中引入新的算法將主流文獻中產業兩兩關聯拓展到3個及以上,也拓展了關聯的時間維度,總體上結合產業升級路徑和企業間的空間關聯揭示了珠三角產業空間演化的機理,對已有產業演化研究做了有益補充。一方面,本文所探測出的產業進入、退出、演替熱點區所體現的珠三角空間結構與已有研究有所不同,如王少劍等(2019)結合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數據分析表明,佛山、東莞在珠三角城市網絡中屬于第一、第二層級的重要城市。但本文卻揭示佛山、東莞兩地在產業演化方面存在較為明顯的階段性企業退出現象,兩地目前進行的專業鎮轉型升級可能是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本文總結出的產業升級與產業關聯路徑與李珊等(2021)的研究基本相符,其通過行業空間網絡視角的分析也得到珠三角產業正在從初級加工制造向高端制造等方向轉型升級的結論;本文總結出的產業關聯規律也進一步驗證了產業關聯性對企業進入、退出的影響(Neffke et al.,2011),并在此基礎上擴展了關聯性的時間維度,考慮了關聯的穩定性。總體上,產業空間演化遵循一定的規律,珠三角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其發展模式和規律有一定的代表性意義。通過促進和引導產業升級,挖掘和培育有利于企業進入和演替的產業關聯集聚區,對促進地區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所使用的Apriori算法盡管可以挖掘出產業之間關聯性,但關聯產生的具體原因,是技術或資源使用上的相似性,還是業務上的互補性,亦或是產業鏈的上下游聯系,還無法詳細說明。未來將結合技能關聯性分析、深度調研訪談等進一步探究產業空間關聯的具體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