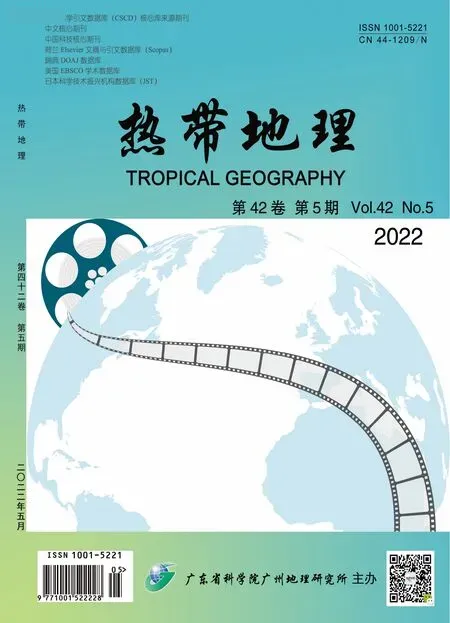大城市都市區制造業空間演變特征及其影響因素——以長沙市為例
駱 晨,鄭伯紅,劉琳琳
(中南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長沙 410075)
制造業是城市發展過程中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其空間是人們通過知識技術創造財富的特殊空間,帶動了城市經濟增長和空間轉型(Yang et al.,2017)。改革開放以來,大城市都市區逐漸成為制造業發展的主要空間載體,因其經濟基礎雄厚,自然資源豐富,交通網絡便利,可以在短時間內以較低的成本重新分配勞動力和資本(Florida et al.,2008)。隨著城市中心區土地、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漲,以及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制造業逐步由中心區向外圍郊區遷移(王俊松,2014)。在城市制造業空間演變的過程中,企業的區位選擇和布局是影響制造業空間演變的主要動力,其空間布局的合理性也會進一步影響企業后續的發展規模(張可云等,2021)。當前國家實施制造強國和推動高質量發展對原有制造業的產業選擇和區位布局等提出新的要求。
制造業空間演變一直是國內外學者們關注的熱點。20世紀中期,伴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深入發展,西方城市的制造業空間呈郊區化遷移趨勢(Wheaton et al.,2002)。針對該現象,早期研究重在關注制造業發展及其空間布局(Hise,2001)、工業企業區位動態選擇(Arauzo-Carod et al., 2009)和制造業空間演變過程的主要影響因素(Lewis,2001;Muller,2001)等方面。國外學者基于工業區位論、新經濟地理學、演化經濟地理學、政治經濟學和行為學派理論等,探討了規模經濟、生產成本、區位條件、制度環境、市場潛力等外在因素,以及企業行為、路徑依賴等內在因素對城市制造業空間演變的影響作用(Weber, 1960; Krugman,1993; Brouwer et al., 2004; Kichko, 2019)。同時,企業異質性產生的區位選擇和分類效應也會導致不同類型產業空間分布和演變特征(Baldwin et al.,2006)。隨后研究方向逐漸由僅關注企業經濟關聯的單一視角,向政策、社會、經濟、創新等多重視角轉變,主要探討產業的空間分布(Yeung et al.,2015; Kaygalak et al., 2016;Aritenang, 2021)。盡管已有研究從城市角度分析制造業空間分布,但主要針對制造業企業員工的數量變化(Kaygalak et al.,2016),或制造業的整體空間布局(Arauzo-Carod et al.,2009;Aritenang,2021),而對于城市內不同類型制造業企業空間演變的綜合性探討較少。
在經濟全球化和快速工業化的背景下,城市空間轉型發展已成為中國大城市都市區發展的重要特征,而制造業空間演變是其主要動力(劉漢初等,2020)。國內學者基于不同的空間尺度(國家、區域、省市),從空間格局、產業特性、動力機制等方面對制造業空間演變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主要聚焦于制造業高度集聚的城市群(徐維祥等,2019;劉漢初 等,2020;周偉 等,2020)或沿海發達地區大城市(張曉平等,2012;蔣麗,2014;高金龍等,2017;Yang et al.,2017)。基于空間格局視角,大城市制造業呈現由中心區向郊區遷移的趨勢,且制造業地理集聚區存在空間差異。從產業特性看,不同類型制造業在空間分布上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受市場影響,空間布局分散(張可云等,2021);而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空間集聚度較高(高辰等,2018)。在動力機制方面,學者們基于不同的視角進行了探討,普遍認為規模經濟(林柄全等,2020)、生產成本(梁育填等,2013)、區位條件(張杰等,2018)和政策制度(駱晨等,2021)等是影響制造業空間演變的主要因素。此外,不同類型制造業企業布局的核心影響因素不同(高辰等,2018;蔣海兵等,2021):市場潛力對勞動密集型企業影響顯著,政策制度對資本密集型企業的空間影響較大,土地成本、產業聯系促使技術密集型企業集聚(周銳波等,2017)。近年來,隨著數據挖掘技術的迅速發展,增強了精細化企業數據的可獲取性,各種計量方法模型的日趨成熟,為研究提供強力支撐(巫細波,2019;崔喆等,2020)。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產業集聚度指標進行測度,忽視了企業數據信息,無法如實反映產業的空間格局變化(崔喆等,2020)。而GIS 空間分析方法能彌補其空間信息的不足,被廣泛應用于產業空間的相關研究。
關于制造業空間演變已取得豐富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多數研究對中部地區大城市的關注度不夠,采用長時段企業數據的研究還不多見。其次,總體上側重于制造業整體空間研究,而從行業特性入手對不同類型制造業空間異質性的研究較少,且在指標選取上對于政策制度、創新能力等方面的重視程度不夠。與此同時,中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新時代,需要重新審視制造業空間布局,探究新時代下制造業空間呈現的新特點。
長沙市經濟發展水平和工業化進程位于全國的前列,但制造業發展存在空間異質性、土地利用效率低等問題。目前,關于長沙市產業空間演變主要探討了工業用地擴展對城市空間演變的影響,產業空間演變以及產業空間優化等方面(劉路云等,2015;葉強等,2019;駱晨等,2021)。受數據獲取限制,已有研究缺乏長時序企業數據的支撐,忽視了不同因素對不同類型制造業空間演變的不同作用。探討長沙都市區制造業空間演變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對實現長沙市產業空間調整,優化資源配置,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本文以長沙都市區1978-2020年制造業企業數據為對象,綜合運用ArcGIS空間分析方法與Sta‐ta計量經濟學模型,從點、面角度深入探討不同類型制造業空間格局的演變特征,選取社會經濟、生產成本、建成環境、政府行為和創新能力進行影響因素綜合分析。以期深入了解大城市制造業空間演變的影響機制,準確判斷城市產業發展規律,為長沙市制造業空間優化布局、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依據。
1 研究區概況、數據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長沙位于湖南省東北部,市域面積11 819 km2,是湖南省省會,長江中游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全國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核心城市。長沙市作為中國重要制造業基地,擁有深厚的工業發展基礎,是中部地區工業化快速推進的典型地區。改革開放以來,長沙產業發展迅速,工業附加值從1978年的6.37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3 420億元,占全省的比例達28%,在全省各市州中領先優勢明顯,對全市GDP的貢獻率達39%。其中,制造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90%以上,在全市的經濟格局中占比達1/3(長沙市統計局,2018)。很顯然,制造業是拉動長沙市和湖南省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此外,長沙市通過充分發揮制造業比較優勢,圍繞工程機械、食品、汽車及零部件、新材料、電子信息等五大千億級產業,其中工程機械產業規模突破2 000 億元,已經成為世界級產業集群。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術、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新型戰略性產業,培育世界級產業集群,打造中部地區崛起核心增長極。
選取長沙都市區作為研究區域,該區域是長沙市的核心區域,也是長沙改革開放以來城市擴張的主要區域。依據《長沙城市總體規劃(2003—2020)(2014年修訂)》劃定的范圍,包含芙蓉區、天心區、開福區、雨花區全部區域,岳麓區、望城區、長沙縣部分區域,總面積為1 930 km2(圖1)。

圖1 研究區域Fig.1 Research area
1.2 數據來源與處理
利用“天眼查”平臺①https://www.tianyancha.com/收集長沙都市區制造業企業數據,該平臺涵蓋中國近3億個社會實體信息。使用的企業屬性信息主要包括:企業名稱、登記行業、注冊時間和注冊地址等,并結合國家企業信用公示系統②http://www.gsxt.gov.cn/,對原始數據進行剔除、過濾、校正等清洗工作。根據這些企業的名稱和地址,借助高德開發平臺③https://lbs.amap.com/的Web服務API中的地理編碼,借用Py‐thon檢索獲取各個企業的經緯度坐標,再利用Arc‐GIS10.3 軟件將企業坐標轉換為空間點數據文件,由此構建制造業企業數據庫。該數據庫囊括了2020-12-31之前在長沙都市區內注冊的所有制造業企業,合計24 923家。為進一步分析不同類型制造業的空間異質性,在參考已有研究(Yang et al.,2018;巫細波,2019)的基礎上,以《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17)(國家統計局,2017)的大類為依據(制造業門類包括C13~43大類),根據制造業各行業對勞動、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依賴程度,將其劃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3 類。其中,C13~15、C17~24 為勞動密集型,C16、C25~26、C28~33、C42為資本密集型,C27、C34~41、C43為技術密集型。
長沙社會經濟數據來源于1978—2021年《長沙統計年鑒》④http://tjj.changsha.gov.cn/tjxx/tjsj/tjnj/《湖南統計年鑒》④和2000—2020 年《長沙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⑤http://www.changsha.gov.cn/szf/ztzl/sjfb/tjgb/。由于2000年前部分年份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的缺失,以及統計口徑的不一致,導致相關數據存在大量缺失,因此,在運用Stata計量模型進行因素分析時,采用的樣本范圍限定在2000—2020年,個別缺失數據用近5 a的年均增長率進行遞推處理。
1.3 研究方法
1.3.1 標準差橢圓 運用標準差橢圓(SDE)研究長沙都市區制造業空間格局和演變趨勢。橢圓表述空間要素分布的主要區域,平均中心表述企業分布的均衡點,橢圓的長軸和短軸分別反映空間要素的分布方向和分布范圍,X與Y的比率表示其延一個方向分布的極化情況,具體數學表達式為(Wacho‐wicz et al.,2016):

式中:Xw和Yw為長沙都市區的加權平均中心;xi和yi為空間要素的質心坐標;wi為企業數量的屬性權重。
采用ArcGIS10.3 軟件的空間統計模塊計算1978—2020年的標準差橢圓,將不同年份的標準差橢圓進行疊加,以得到不同類型制造業空間的分布特征和變化規律。
1.3.2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Kernel Density)常用于計算空間要素在其周圍領域中的密度,能直觀表現某類社會經濟活動空間的集聚程度。核密度值越高,表明要素越集聚(蔣海兵等,2021)。運用核密度分析對不同類型制造業空間分布進行可視化處理,直觀反映不同類型制造業的空間集聚程度。其計算公式為(孫威等,2020):

式中:λ?h(p)為點p處的核密度值;h是以p為圓心的半徑;pi是以p點為圓心、h為半徑內的第i個制造業企業,;p-p i為估算點p到樣本pi處的距離。采用ArcGIS10.3軟件開展相關計算和制圖工作。
1.3.3 空間計量模型 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會趨向獲利最大的位置,其空間布局存在明顯的離散特征,且因變量為企業數量(計數數據)。在處理離散型計數變量通常采用泊松回歸。假設Yi=yi的概率由參數為λi的泊松分布決定(陳強,2010):

式中:λi>0為“泊松達到率”,由解釋變量xi所決定,泊松分布的期望值與方差等于泊松達到率,則Yi的條件期望函數為:

泊松回歸的局限性在于要求因變量的期望值與方差相等,即當λi= 0,為“均等分散”;當因變量方差與期望值相差過大,當λi>0,出現“過度分散”時,泊松回歸不再適用,則需要使用負二項回歸模型。引入過度分散參數α,條件方差為:

條件方差是α的增函數,當α= 0 時,采用泊松回歸;當α>0時,則采用負二項回歸,且α值越大,表示數據的離散程度越強。
2 長沙都市區制造業空間格局及其演變特征
2.1 制造業發展時序格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實現了快速發展,其空間也在經濟轉型中得到重構。因經濟水平、政治環境的不同,制造業空間呈現不同的階段性特征。結合已有研究和長沙市實際,將長沙制造業發展分為1949—1978、1979—1990、1991—2003、2004—2011、2012—2014 和2015—2020 年6個發展階段(圖2)。
新企業區位選擇是驅動制造業空間演變的主要動力。圖2為1978—2020年各類制造業企業增量和數量變化趨勢。從企業的增量變化看,長沙都市區各類制造業企業數量增量基本呈增長趨勢,勞動、技術、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交織發展,資本密集型制造業與全門類制造業發展趨勢基本一致。從企業數量變化看,各類制造業呈逐漸增長的態勢,且隨著時間推移,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逐漸向技術密集型轉型升級。具體而言,1979—1990年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活力被激活,3 類產業呈同步增長趨勢,且增速緩慢;1991—2003年,伴隨改革開放和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要素,成為長沙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力,技術密集型制造業開始高于其他類型制造業,企業數量進入快速增長階段;2004—2011年,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呈現領跑趨勢,且資本密集型制造業開始與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拉開差距;2012—2014年,長沙全面實施“興工強市”戰略,制造業經歷了一個黃金發展期,形成了多點支撐的產業格局,勞動、資本、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增長同步,但從數量上看,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仍處于領先地位;2015—2020 年,3類產業增量波動較大。2015年國家全面推行制造強國戰略,推動長沙制造業企業數量快速增長,而智能制造作為主攻方向,是長沙市制造業發展的重點,促使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得到了快速發展。

圖2 長沙都市區各年份各類型制造業企業總數及其增數變化趨勢(1978—2020年)Fig.2 Changes of variou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angsha metropolitan area from 1978 to 2020
2.2 制造業空間演變特征
1978—2020年,長沙都市區制造業企業的數量從53家增長至24 923家。其中,勞動密集型企業共有7 297家,資本密集型企業共有8 049家,技術密集型企業共有9 577家。圖3和表1展示了全門類制造業及其子行業SDE的結果及變化。
2.2.1 全門類制造業企業標準差橢圓分析 如圖3-a 和表1 所示,1978—2020 年長沙都市區內的全門類制造業企業整體呈“西北—東南”分布,早期長沙制造業發展受湘江的自然限制,企業分布以河東老城區為主,沿湘江兩岸東西向發展。1972年湘江大橋建成,使得城市制造業突破湘江的限制向西發展。隨時間推移,標準差橢圓越來越大,表明企業分布呈擴散趨勢,其方位角在102.41°—116.96°之間變化。其中2004 年變化最為明顯,這與長沙市2003 年積極實施“退二進三”、疏散不適應城市功能定位的制造業企業等政策密切相關。1978-2020年橢圓平均中心主要在芙蓉區內跳動,主要因為芙蓉區是長沙市服務業高度集聚區,能為制造業提供便捷的服務,對企業規模較小的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企業產生較大吸引力。自1978年以來,X軸的標準差值呈增加趨勢,橢圓扁率逐漸增大,表明制造業的發展方向性逐漸明顯。源于布局在西北部的長沙高新區和望城經開區,以及東南部的長沙經開區與隆平高科技園吸引了大量企業入駐,逐漸形成集群效應。從Y 軸的標準差值變化看,1978—2003年,標準差值呈減小趨勢,此時制造業企業向心力越來越明顯。2003—2014年,標準差呈增長趨勢,制造業企業呈擴散發展。2014年之后,標準差又開始不斷減小,說明制造業企業由擴散向集聚發展。由此可見,長沙都市區制造業空間基本遵循“集聚—擴散—集聚”的演變規律。

表1 長沙都市區制造業SDE結果分析Table 1 Result of SDE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angsha metropolitan area
2.2.2 不同行業制造業企業標準差橢圓分析 不同行業的標準差橢圓變化趨勢不同。如圖3-b所示,1978—2020年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平均中心基本位于芙蓉區內,生成的橢圓總體呈“西北—東南”分布,方位角大致在99.56°—123.06°之間變化。1978年后,由于都市區東南方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數量顯著增加,促使方位角發生顯著變化。這與長沙政府于1979年8月編制的《長沙市城市總體規劃》中要求“控制大城市規模,發展小城鎮”的政策導向密切相關,城市建設用地以東南方向拓展為主。1990—2020年X軸的標準差距離不斷增加,體現勞動密集型企業沿長軸“西北-東南”方向存在擴散趨勢;從Y軸標準差看,1978—1990年,短軸標準差較小,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向心力明顯,1990年后Y軸標準差保持穩定的增長趨勢,勞動密集型企業不斷向外圍擴散分布。由于長沙市政府在1989年開始明確規定土地綜合開發轉讓費的價格,推動勞動密集型企業外遷重組。

圖3 長沙大都市區制造業空間演變的標準差橢圓變化(1978—2020年)Fig.3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 Changsha metropolitan area from 1978 to 2020
如圖3-c,資本密集型企業與全門類制造業企業空間格局相似。以工程機械為代表的資本密集型制造業是長沙市的支柱性產業,且該類產業普遍規模較大,因此對長沙整體制造業空間產生較大影響。1978—2020年資本密集型企業的平均中心發生較大變化,方位角大致在43.77°—122.58°之間變化。1978年平均中心位于雨花區內;1990年平均中心開始向西北部轉移,落于芙蓉區邊界處;1990—2014年,平均中心在芙蓉區內變化;2014年之后,平均中心向東北方位移,落于開福區境內。從橢圓的分布方向看,資本密集型企業總體呈“西北—東南”分布,其中1990年后,橢圓的分布方向由“東北—西南”轉變為“西北—東南”方向。歸因于1991年長沙科技開發試驗區升級為長沙高新技術開發區,成為國家首批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步入高速發展。長沙高新區憑借優惠的政策,吸引大量企業入駐,導致西北部的資本密集型企業激增。X軸標準差基本呈增加趨勢,沿“西北—東南”方向存在極化現象,Y 軸標準差變化呈“先集聚后擴散”的發展態勢。
如圖3-d,1978—2020 年技術密集型企業的平均中心主要位于芙蓉區與開福區、天心區和雨花區的交界處。該區域金融中心密集,人口密度高,市場需求量大,吸引部分規模較小的技術密集型企業布局于此。生成的橢圓呈“西北—東南”方向分布,方位角在106.13°~109.0°之間變化。1978 年,生成的橢圓近“南—北”向分布,該階段技術密集型企業受湘江的自然限制較大,沿湘江兩岸分布。1978年后,橢圓逐漸向“東—西”方向轉變。原因在于區域西部的岳麓大學城能為企業輸送人才、提供技術創新,區域東西兩邊的長沙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能為該類型企業提供優惠政策,從而產生較強的吸引力。X軸的標準差值不斷增加,企業方向性逐漸明顯。而Y軸的標準差值以2003年為時間節點,先減少后增加,技術密集型企業經歷了先集聚后擴散的發展態勢。在產業發展初期,出于對創新和新技術的需求,技術密集型企業首選在產業集聚度高的城市中心區發展,但隨著中心區地價的上漲以及生產技術的成熟,企業會逐漸向城市郊區轉移,以尋求空間擴大規模。
總體來看,不同產業特性的制造空間格局演變存在異質性特征:勞動密集型企業整體存在大規模的產業轉移,以接觸擴散和等級擴散為主;資本密集型企業依托工程機械產業在長沙高新區和長沙經開區形成集群效應,而部分污染性資本密集型企業受政府干預,逐步向外圍郊區轉移;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空間呈先集聚后擴散趨勢,集中在長沙高新區和經開區,并進一步向望城經開區、隆平高科技園和岳麓高新區擴散。
2.3 不同類型制造業空間集聚特征
借助ArcGIS,通過核密度分析對2020 年長沙都市區新增制造業企業分布進行可視化,得到各類制造業空間的集散特征(圖4)。長沙都市區制造業空間分布相對分散,各類制造業集聚中心各異,在各工業園區和重大交通設施附近形成多個較為明顯的集聚中心。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大部分為都市型工業,企業規模以輕、微型為主,用地布局靈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間特征。雖然中心區能為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提供便捷的服務,促使部分規模較小的企業仍選擇集聚于此。但隨著土地和勞動力價格的逐年攀升,長沙勞動密集型企業逐步向外圍郊區疏散;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以大型企業為主,其用地規模大,呈“大范圍擴散、小范圍集聚”的空間特征,主要表現為沿鐵路、高速、國道、省道等主要交通干線由中心區向土地價格更低的郊區遷移;技術密集型企業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導,其區位指向性強,傾向于布局在科教集中、政策優惠和環境優越的地區,受國家級開發區吸引較大,集聚中心基本布局在“岳麓大道—三一大道”的工業發展軸上,該工業軸密集布局于長沙高新區、長沙經開區、隆平高科技園等園區,先進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集群效應明顯。

圖4 2020年長沙都市區新增制造業企業核密度分析Fig.4 Kernel density of new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the Changsha metropolitan area in 2020
3 長沙都市區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影響因素
3.1 指標選取
影響制造業空間演變的因素復雜多樣,根據已有文獻(Sun et al.,2016;高金龍等,2017;周銳波 等,2017;張杰 等,2018;徐維祥 等,2019;劉漢初等,2020;周偉等,2020),長沙實際情況以及數據的可獲取性,選取全門類制造業企業以及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等不同類型制造業企業作為因變量,從社會經濟、生產成本、建成環境、政府行為、創新能力5個方面,選取11個指標作為自變量(表2),研究其對長沙都市區不同類型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

表2 長沙都市區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影響因素的各指標變量選擇及描述Table 2 Each index variable description of influenc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location choices
社會經濟發展條件是城市建設的重要物資基礎,其中經濟基礎、人口數量和工業水平與制造業發展息息相關。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代表一個地區的宏觀經濟發展情況,人均生產總值較高的地區通常經濟發展水平也越高,伴隨著更多的財政收入和市場需求,并依托其完善的基礎設施、人才儲備以及政策紅利等對制造業企業產生強有力的吸引(徐維祥等,2019;林柄全等,2020)。城市年末總人口代表城市的人口基礎反映勞動力的可用性、可及性以及市場潛能。地處人口資源豐富地區的制造業企業更便于獲取適宜的勞動資源(徐維祥等,2019)。工業總產值代表城市工業發展總體規模和水平,其水平的提升能帶動制造業集聚的形成。
生產成本是影響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的決定性因素,主要包括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周銳波等,2017;周偉等,2020),其中,區域職工平均工資常用于衡量城市勞動力成本對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地區工業用地出讓平均價格能直接反映制造業活動的土地成本。
建成環境是城市中滿足居民日常生活、工作和娛樂需求的人造空間(Sun et al.,2016)。交通基礎設施會影響企業的生產運輸、員工的通勤效率,從而影響制造業企業空間分布(周偉等,2020)。環境質量好的地區能吸引高端人才和制造業企業(Sun et al.,2016)。故選取公路里程數和城市綠地率2個變量衡量。
政府通過制定各類戰略政策引導和調控制造業的發展方向和空間布局(周偉等,2020)。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能有效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徐維祥等,2019)。政府通過設立工業園區、提供優惠政策和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吸引制造業企業入駐,從而引導制造業空間集聚發展(Kang et al., 2020)。因此選取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和省級以上工業園區數量3 個變量衡量政府行為。
新經理地理學認為技術創新是影響產業空間的重要因素(Ozawa,2003),專利申請是衡量城市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故選取專利申請數量作為衡量地區創新能力的指標。
3.2 結果分析
首先,選取模型A研究全門類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受到的主要影響因素。其次,為進一步研究不同類型制造業企業在區位選擇上的差異性,分別選取勞動密集型企業數量(模型B)、技術密集型企業數量(模型C)和資本密集型企業數量(模型D)進行分析。
通過計算因變量的統計特征,發現樣本方差遠高于期望值。以勞動密集型為例,因變量方差為1 970 040遠大于其期望值4 594.95,樣本的所有模型通過負二項回歸計算得到的α系數均在95%的置信區間上>0,故使用負二項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詳見表3。

表3 負二項回歸結果(2000—2020年)Table 3 Results of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analysis from 2000 to 2020
3.2.1 全門類制造業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在全門類制造業模型A中,社會經濟、生產成本和政府行為對長沙都市區制造業空間演變具有重要影響。Pop‐ulation 和Park 通過1%的顯著水平檢驗,且回歸系數都顯示為正,表明人口資源越豐富,勞動力的可用性、可及性越高,工業園區建設越快,越有利于制造業空間發展。人口的持續增長為企業提供豐富的勞動力,對勞動力需求較高的制造業企業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同時,長沙加快開發園區產業發展,對園區內的企業提供優惠政策,通過引導產業轉移,吸引關聯企業于此布局。PGDP、Wage、Mile‐age 和Open 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經濟基礎、勞動力成本、交通基礎設施和對外開放程度對企業布局產生一定吸引力。其中,PGDP和Mile‐age 的回歸系數為正,說明長沙市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交通基礎設施越便利,對制造業企業的吸引力越強。Wage和Open的回歸系數為負,這是由于勞動力成本的攀升會導致企業生產成本過高而失去競爭力,逐漸向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遷移,而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更側重于搶占市場份額,不利于本土制造業的發展。此外,Green、Investment和Patent對全門類制造業企業布局影響不顯著,可能是模型A無法體現行業異質性。
3.2.2 各行業制造業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勞動密集型模型B 的結果表明,PGDP、Population、Wage、Open 和Park 影響顯著,均通過1%的顯著水平檢驗。其中,PGDP、Population和Park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由于長沙市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市場需求量越大,人口增長越快則為企業提供的勞動力也越豐富,從而為企業提供更多的市場機會以及用人選擇。同時,廣泛布局在郊區的開發園區能為勞動密集型企業提供大量的政策優惠,如用工補貼、稅收優惠等以吸引該類型企業入駐。而Wage和Open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由于勞動密集型企業主要靠大量使用勞動力,企業出于節約生產成本的考慮,更傾向于布局在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而Open 對該類型企業演變產生負面影響,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外國跨國公司以占領國內市場份額為目標,吸納大量本地的勞動力,不利于本地企業的發展。Land在5%的顯著水平下為負,表明土地價格低的地區更能吸引勞動密集型企業布局。因此,長沙中心區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密集的人口資源吸引部分規模較小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布局;此外,更低的勞動力成本與土地價格和更多的工業園區數量將會引導該類制造業空間不斷向城市郊區遷移。
技術密集型模型C 顯示,PGDP、Population、Wage、Open和Park均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其中PGDP、Population、Park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技術密集型企業的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經濟基礎、豐富的人口資源以及工業園區的政策支撐。PGDP 在模型C 中的系數(0.032 6)遠高于其他模型,表明經濟基礎是該類型企業增長的重要動力,經濟發展繁榮地區具有創新、包容的發展環境對于技術密集型企業的發展不可或缺。而豐富的人口資源能為技術密集型企業提供技術人員儲備,有利于產業發展。同時,長沙開發園區政策能有效推動企業各項經濟指標的顯著提升,從而吸引企業入駐并不斷集聚。Wage和Open顯著為負,表明用工成本的攀升,會成為企業入駐和根植的阻礙;而跨國公司和全球資本的涌入,可能會導致行業技術壟斷,不利于技術密集型企業發展。Industry、Mileage 和Patent 的系數較為顯著且為正,反映該類型產業發展依賴于城市工業基礎的總體水平、高水平的通達性和技術創新的能力。其中,Patent 的系數在模型C中為0.044 1,相較于其他模型而言絕對值最高顯著性最強,說明創新能力是技術密集型企業獲得成功的重要驅動力。因此,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企業具有經濟基礎指向性、投資環境指向性和創新效應指向性特征,上述因素使得該類企業在長沙高新區和經開區形成集聚。
資本密集型模型D 的結果顯示,Population、Mileage 和Park 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豐富的人口資源、便捷的交通基礎設施和工業園區的政策支撐,對企業規模發展具有促進作用。相較其他模型,Mileage 的系數最高為0.042 2,說明資本密集型企業對地區交通可達性依賴度高,通過提升城市交通可達性水平,降低生產要素在該企業間的錯配程度,促進其再配置及生產效率的提高。而資本密集型企業的發展規模和效率離不開大規模的投資與政策的大力支持,長沙市開發園區為鼓勵企業充分利用多層次資本市場,對企業給予資金支持、稅收及租金優惠等各種利好政策,從而吸引企業入駐園區并形成集聚效應。Wage 和Open 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勞動力成本和利用外資水平是影響資本密集型企業的重要因素。勞動力成本上升會造成企業利潤空間縮小以及同行間競爭加劇。跨國公司資本的大量流入,容易形成行業壟斷,不利于本地資本密集型企業發展。此外Land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系數為-0.012 7,其絕對值遠高于其他2類行業,由于資本密集型企業普遍用地需求量大,土地價格的上漲將會導致企業發展用地成本的升高,對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產生擠出效應。
4 結論與啟示
4.1 結論
基于長沙都市區制造業的企業數據,分析了不同類型制造業空間演變過程,探討了社會經濟、生產成本、建成環境、政府行為和創新能力等因素對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得到的主要結論有:
1)1978—2020 年,長沙都市區制造業企業數量和增量總體呈現增長趨勢,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逐步向技術密集型升級。所有類型制造業在空間分布上均呈現明顯的郊區化趨勢,表現為由城市中心區集聚擴充向郊區化擴散發展,再到郊區集聚重組。在改革開放初期,長沙都市區制造業受湘江的自然限制,主要集聚在河東老城區并沿湘江兩岸展布,隨后伴隨湘江大橋的建成使得制造業空間突破湘江限制逐步向河西發展。隨著近20年來長沙市基礎設施及開發區建設的不斷完善,開發區逐漸成為制造業重組集聚的重要空間載體,制造業主要沿“西北—東南”方向擴展,呈現“點軸式”發展格局。在空間演變過程中,長沙制造業空間經歷了由集聚到分散再到集聚的周期變化特點,演變模式由鑲嵌式填充變為外向式擴散,但也面臨空間功能置換、空間利用率不夠、集聚程度不高等問題。
2)受產業特性的影響,不同類型的制造業在空間分布上呈現明顯的差異。勞動密集型企業以輕型、微型為主,用地布局靈活;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產業關聯度更為緊密,集聚效應明顯,因此,更需要通過集聚集群發展以減小生產成本、提高協作效率和抗風險能力;而資本密集型企業以大型企業為主,大規模的用地需求和員工需求,限制了其在城市中心區集聚,與此同時,外圍郊區的開發園區“政策租”等優惠政策吸引企業入駐,促使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呈現“大范圍擴散、小范圍集聚”的空間特征,其中高能耗、污染性的重化工制造業擴散趨勢尤為顯著。此外,資本密集型制造業與全門類制造業空間演變趨勢基本一致,反映該產業是長沙市制造業空間格局的基礎。
3)不同類型制造業企業區位布局的關鍵影響因素不同。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受到社會經濟、生產成本和政府行為的影響;技術密集型企業更加注重區域的經濟效益、創新環境以及政策支持,社會經濟、生產成本、建成環境、政府行為和創新能力均對其產生重要影響;資本密集型企業受人口基礎、交通可達性、土地成本和工業園區政策作用突出。3 類制造業空間演變均受到政府行為的顯著影響,其中,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和工業園區數體現了長沙市政府對制造業發展的規劃指引與政策導向,表明產業發展戰略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驅動著區域產業集聚與擴散。此外,對外開放程度對3類制造業企業布局都產生負面影響,表明大量外資的涌入容易形成行業壟斷,不利于本地制造業發展。
4.2 啟示
基于上述結論,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啟示:
第一,因地制宜、分區制定。逐步引導長沙中心區不符合城市定位的制造業企業向外疏散,對于污染性、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企業實施“退二進三”,引導公共設施、交通設施、綠地、服務業、居住用地等性質轉變;在近郊區實施“退二進二”限制高污染、強干擾制造業發展,重點發展高附加值的制造業,逐步引導用地功能置換。同時,應加快對現有開發園區的整合和完善建設,通過精細化、合理化設置主導產業,降低園區產業結構趨同度,進一步加強制造業向園區集群化、集約化發展。
第二,因產而異、精準施策。針對長沙不同類型的制造業發展現狀,政府應統籌考慮制定適宜的產業發展政策。為實現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合理擴散,可通過完善產業上下游配套條件,逐步引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由中心區向外疏散;引導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于開發區集聚,以長沙高新區和望城經開區為核心,依托周邊高校云集優勢,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和創新資源導入;對于資本密集型制造業而言,應加快疏散長沙中心區現有高能耗、污染性資本密集型企業,并督促其加大技術改造力度。同時,應通過優勢互補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引導生產要素向開發園區集聚,吸引非污染性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入駐園區。
第三,合理引導、優化配置。長沙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應充分考慮不同類型制造業空間演變的關鍵驅動要素,制定合理的招商引資及產業發展政策。通過優化營商環境,加快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配置效率,促進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優化升級;積極推動科學技術創新的成果轉化,加大人才引進力度,全面提高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發展水平;加快補齊郊區交通基礎設施,帶動資本密集型制造業沿交通軸線向郊區分散;進一步推進開發園區集約化、特色化發展,引導各園區合理分工、助力產業結構調整;鼓勵本地制造業積極參與全球產業網絡,強化與外部產業的聯系來提高自身的風險抵御力。
此外,本研究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數據獲取難度的限制,只選取2000—202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負二項回歸分析,未涉及更長的時間序列,未來將結合新的面板數據,分時段展開對長沙制造業空間演變的影響因素的動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