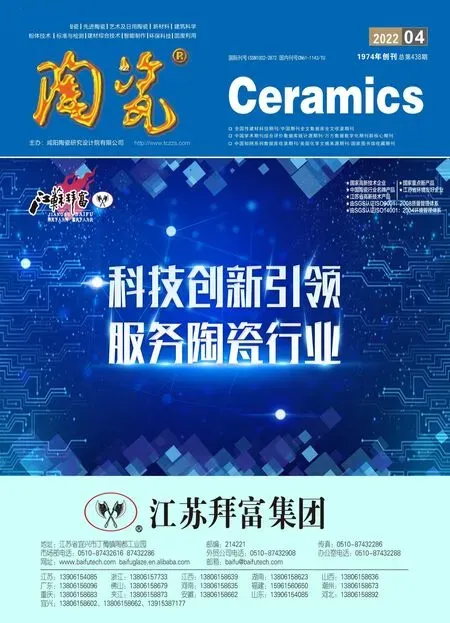淺談明代景德鎮民窯青花寫意之美*
徐可欣
(景德鎮陶瓷大學 江西 景德鎮 333000)
1 明代景德鎮民窯青花寫意
明代景德鎮民窯青花瓷繪畫掙脫了元代的異域風情,民窯的工匠不受各方約束,所描繪的內容貼切生活且簡單豪放,畫風也趨于自由寫意的繪畫性裝飾。寫意是中國傳統繪畫的一種形式,青花繪畫是陶瓷藝術中釉下彩繪表現形式之一,其繪畫內容與藝術創作均展示了人們對自然萬物和社會萬物的認知。青花寫意將我國傳統的山水、花鳥、人物等題材,運用青花料和瓷繪毛筆繪制于白色瓷坯繪畫之中,創作出一副“青墨”寫意畫,一墨一水、一料一茶遙相呼應,近似一致,青花寫意是中國傳統寫意繪畫在陶瓷介質上的創新與延申,是古人智慧結晶和時代進步的證明。
2 明代景德鎮民窯青花寫意之美
2.1 氣韻靈動的留白之美
在陶瓷青花寫意繪畫中構圖是第一要義,這與中國傳統水墨畫的發展有著必然的聯系,謝赫在六法論中將構圖稱之為“經營位置”,并強調構圖在繪畫中的重要性,好構圖能表現出繪畫內容的“氣韻生動”,創作出“超邁絕倫”的繪畫作品。明代景德鎮民窯青花寫意的構圖沿用了中國傳統寫意繪畫的基本構圖形式,在中國傳統寫意繪畫中,留白是一項重要的構圖手法,陶瓷工匠巧思地利用景德鎮瓷器“白如玉”的特性構造留白畫面,“計白當青”設計對比以表現以虛襯實、虛實相生的美感,從而營造氣韻靈動的留白之美。
留白在青花寫意的構圖中頗為普遍,如明代宣德年間景德鎮民窯出土的青花人物紋高足碗(見圖1)。碗部外壁描繪了仕女賞月的場景,足柄部繪制松竹梅紋飾。在仕女賞月的圖畫中,仕女立于樹石之下眺望遠方,旁側侍一童子,高處繪有云氣紋,遠處繪以群山起伏。用近景與遠景之間的大片空白表現畫面中近景與遠山的距離關系,同時襯托近景中的登高賞月,不是畫出所有的山嶺或山的全貌,而是使用大片留白的構圖。通過近處飄動的云氣紋、遠處山邊的虛化來表現薄薄的云霧彌漫著山峰的動態,讓人自然而然地感覺出留白處即群山間云霧繚繞,宛如仙境一般的畫面,以此烘托整體的環境氣氛,給人留以無盡的遐想。

圖1 青花人物紋高足碗
2.2 虛實相生的青白之美
明代景德鎮民窯青花寫意畫面的色彩表達,與中國傳統水墨寫意畫近似。中國傳統水墨寫意畫中,以不同深淺的墨色表達畫面色彩的層次,并有“墨分五色”一稱,陶瓷青花寫意繪畫中也有“料分五色”,分別為頭濃、正濃、二濃、正淡、影淡。“青花也者,系以深淺數種之青色,交繪成文,而不雜以他采,亦猶畫山水之專用墨色也”。青花的色彩以單色表萬色,依托毛筆為媒介,通過料與茶葉水將畫面表現在白色瓷坯之上,營造一副虛實相生、意境深遠的青白色瓷畫。
陶瓷青花寫意繪畫色彩的應用注重虛實相生、虛實結合的手法,“虛”與“實”的表達是中國傳統繪畫中一對重要的美學思想,也是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青花寫意瓷畫看似單調無色,但畫面中的青色多變,且層次豐富,青花料與白色瓷坯之間形成對比又相互調和,所謂“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既辨證又統一。清代《山靜居畫論》中道:“古人用筆,妙有虛實。所謂畫法,即在虛實之間。虛實使筆生動有機。機趣所之,生發不窮”。如清溪論道圖中(見圖2),人物端坐于山谷之間談學論道,垂柳下、溪水畔盤坐一童子聆聽學習,遠處繪以蒼山、草石、樹木的景色,陶瓷匠人運用毛筆在瓷坯上作畫,通過色彩的濃淡對比表現場景中的虛實關系,展示畫面豐富的層次感和深遠的意境。如畫面中“實”的山石與“虛”的水草相互呼應、“實”的魚群配以“虛”的溪水、“實”的蒼山相對應“虛”的云霧進行靜與動的對比,青色與白色之間的虛實,互相協調,相得益彰,勾勒出青花寫意畫虛實相生的青白之美。

圖2 清溪論道圖
2.3 質樸生動的題材之美
明代民窯的青花寫意題材廣泛,類別多樣,尤其是山水、花鳥以及文人墨戲畫中的梅、蘭、竹、菊題材等極為盛行。民窯工匠所繪的青花寫意作品風格神采飛逸、簡單豪放,具有生活性與開放性。雖然題材受當時文人畫和版畫的影響與啟迪,但并不完全等同,而是逐漸成熟為獨立的繪畫系統,既保有傳統文人畫的高雅格調,又不失民間藝術中的質樸生動。
如明代晚期景德鎮民窯的青花鹿紋盤(見圖3),中心位置繪以活潑靈動的兩只小鹿在樹下乘涼,腳下草地上盛開著一朵朵花兒,小鹿之間相互對視又好像在追逐打鬧,盤壁周圍采用開光的構圖形式,繪以仙草花果圖案,結合主題紋飾仿佛聞到花草芳香,置身于叢林之間。鹿是中國傳統繪畫中常見的題材,有著健康長壽、幸福和諧、繁榮昌盛的美好寓意,又同“祿”同音象征著福氣,工匠將鹿和花果仙草的造型裝飾得夸張生動,用簡單的線條強調鹿的動態,這種生動的表達更符合民間大眾質樸的藝術審美,題材內容更具生活趣味,體現著人文畫的精神意志。

圖3 青花鹿紋盤
2.4 詩意盎然的意境之美
陶瓷青花寫意中的意境是一種詩意盎然的視覺感受,將畫面中的情與景相互融合,形成一種景中有情,情中有景的意象,給予觀者無盡的遐想。它客觀存在且反應于人的思維。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中寫到:“藝術家以心靈映射萬物,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現的是主觀的生命情調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成就一個鳶飛魚躍,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靈境;這靈境就是構成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意境。”物化移情的意境源于自然萬物,民窯工匠在萬物中注入了思想感情,將形式美上升到意境美,將自然之美升華為藝術之美。意境是青花寫意繪畫的精髓,意境的表達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特質所在。
明代景德鎮民窯青花寫意繪畫中,工匠用青與白的色彩和巧妙的構圖表達情景相匯的詩意新境,如青花瓷罐,羲之愛鵝圖中(見圖4),人物倚靠在亭邊,目光望向水面之上,兩只鵝在水中游泳,岸邊垂柳下侍一書童。畫面中并非直白畫出水面的波紋,而是以簡單的長線條描繪出鵝在水面游走時留下的軌跡,長度不一的短線條和露出水面的水草表示水淺處。場景中虛實相生、動靜對比、情景相融,描繪出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趣。

圖4 羲之愛鵝圖青花罐
陶瓷匠人以自己豐富的想象和高超的藝術技法,賦予陶瓷藝術作品“悠然自得”的詩境,營造了詩意盎然的意境之美,這是中國陶瓷繪畫藝術的獨特魅力。
2.5 形神兼備的氣韻之美
明代景德鎮民窯工匠們,在創作中注重畫面的氣韻和個人的表情達意,強調繪畫對象的精氣神韻,以突出畫面形神兼備的意韻,作品中滲透著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獨有的意境美與氣韻美。“其實氣韻即是畫面上所產生的生動藝術效果,離開生動性就沒有氣韻,它是優美的運動,和諧的節奏所表現出來的活躍生命力”。明代景德鎮民窯青花寫意藝術作品中,工匠們通過畫面傳遞著內省的情感表達,刻畫形神兼備的氣韻之美,尤其在人物畫題材的塑造上有著獨特的造詣。如高士垂釣圖中(見圖5),人物服飾褶皺的刻畫,看似隨意勾勒的幾筆線條,卻靈動地將人物靜坐垂釣的形態表現得酣暢淋漓。兩只蜻蜓在水面上飛舞,彎曲的線條表現蜻蜓的翅膀煽動。看似簡單的人物表情,濃淡不一的寥寥數筆,不苛求形式上的細節,傳神地塑造了一個高士垂釣的場景,將“脫然世外身,不理世俗事”的氣質形象刻畫得惟妙惟肖,高超地描繪出一副神形兼備、氣韻靈動的藝術畫面。

圖5 高士垂釣圖
3 結語
中國古代陶瓷繪畫藝術在不斷地演變和發展中,逐漸形成特有的美感,這種美與時代的進步、藝術的發展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審美意識密不可分。明代景德鎮民窯青花寫意作為民間藝術的絢麗明珠,所體現出的美學思想和中國傳統寫意畫的文人精神,至今仍可作為陶瓷繪畫藝術創作的參考依據。傳統的藝術審美理念值得當代陶瓷設計者們深思和研究,探索中國傳統青花寫意之美,學習和思考,將之注入當代陶瓷藝術創作中,傳承和發揚中國傳統美學思想,帶給觀賞者美的視覺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