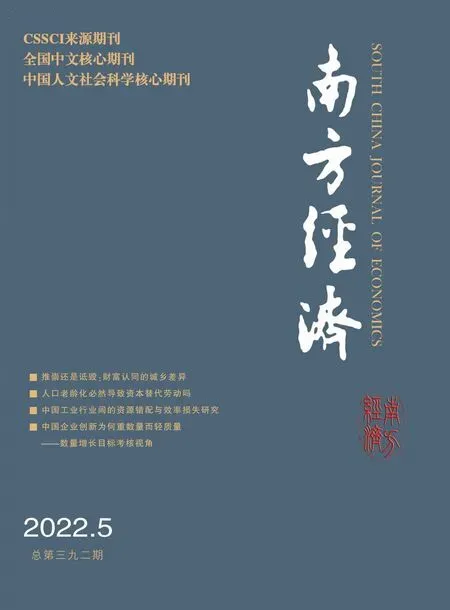國際援助再分類及其對受援國經濟增長的異質性影響
萬一方 陳云賢
一、引言
新自由主義思潮主張自由市場,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然而,傳統國際援助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援助國的財政收入,相當于是跨國的轉移支付,是一種跨國的政府干預(周弘等,2007)。因此,國際援助對受援國的經濟影響,是被學術界長期關注的一個命題。然而該命題尚未產生共識,無論用古典增長模型還是新增長模型都可以從各種不同的方向來進行討論(Hansen and Tarp,2000;Easterley,2003;Dalgaard et al.,2004)。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國際援助對受援國經濟發展有積極影響(Burnside and Dollar,2000;Rajan and Subramanian,2008;Galiani et al.,2017),一些學者認為國際援助對受援國是負面影響(Gupta and Islam,1983;Mosley et al.,1987),還有一些學者的實證結果發現國際援助對受援國的影響不顯著(Boone,1996;Dreher and Langlotz,2020)。本文從不同類型國際援助的影響具有異質性的角度,再次探討這一問題。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經合組織)定義的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簡稱ODA)是最為廣泛使用的國際援助分類方法。該定義對援助的優惠性提出了要求,規定贈與比重須在25%以上,并將不符合ODA標準的其他政府間援助歸類為其他官方援助(Other Official Flows,簡稱OOF)。2000-2014年間,超過80%的傳統援助國的援助被劃分為ODA,而接近80%的中國對外援助被劃分為OOF(李嘉楠等,2021)。之所以大部分中國對外援助不符合ODA的定義,是因為21世紀以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采用了創新性的一攬子援助方式,對國際援助的理解具有自己的特色。ODA的概念和統計方法是OECD發展援助委員會根據上世紀傳統援助國的主要援助方式制定的,沒有考慮新興援助國的援助方式,而聯合國、世界銀行等主要國際組織也同樣沒有相關定義。新型的國際援助在資金使用方面同ODA有著明顯區別,ODA分類體系無法有效估算新興援助國在國際援助中的份額,也較難激發傳統援助國采取新型援助手段的積極性。為此,傳統援助國和新興援助國都在嘗試重新審視和界定國際援助。
一些中國學者就新型國際援助方式的定義做出了嘗試。張海冰(2012)將中國對非洲的援助模式界定為“發展引導型援助”,援助國通過“援助+合作”的方式幫助引導受援國實現自主發展。林毅夫、王燕(2016)則提出了“超越國際援助”的概念,提出以ODA為主要方式、綜合利用多種資金渠道。鄭宇(2017)提出在定義上用更包容的“發展合作融資”概念代替ODA概念。現有研究大多是圍繞新興國援助與ODA的聯系與區別來進行分類,其本質落腳點都是基于國際援助是否具有互惠性,分類基準是根據國際援助是無償性質、優惠性質還是商業性質、投資性質。這樣的分類方式忽略了國際援助的根本目的,即促進受援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近年來,部分學者也提出應更加明確援助目標,如鄭宇(2017)提出應根據各國的實際情況來平衡投向保障型援助和發展型援助的資源。然而,現有研究并沒有從受援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動因角度對國際援助進行定義和分析。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如下兩點創新性工作:第一,從資源生成的角度出發,提出資源配對援助法,宏觀性地將國際援助分為商業性國際援助、開發性國際援助和公益性商業援助三類。資源生成理論是中觀經濟學開創性的理論創新。資源生成理論提出,資源并不簡單分為可經營性資源(可交易商品)和非經營性資源(公共品)兩類,其中還有一種模糊的資源類型——準經營性資源。準經營性資源具有動態性、經濟性、生產性三大特性,既不同于非經營性資源、不能由政府完全承擔,也不同于可經營性資源、不能完全交由市場配置(陳云賢,2019;陳云賢,2020)。本文認為,受援國落后的本質原因是資源稀缺,國際援助通過向受援國注入資源推動其社會經濟發展,不同類型的資源注入將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對應資源生成理論中的非經營性資源、準經營性資源和可經營性資源,本文將國際援助分為公益性援助、開發性援助和商業性援助三類。第二,根據上述三類國際援助,本文實證驗證了開發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對受援國的正向影響。通過對2003-2014年中國對外援助數據的分析,發現總的援助規模對受援國的經濟正向影響顯著,且開發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分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開發性援助對受援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要強于公益性援助,而公益性援助對受援國經濟發展促進作用的持續期要長于開發性援助。
傳統援助國在過去幾十年里主要關注社會性基礎設施和人道主義救援等公益性援助,對經濟性基礎設施和生產部門等開發性援助相對忽視。中國的對外援助以開發性援助為主,能夠整合無償援助、商業貸款和權益投資等多種融資渠道,積極推廣自身在經濟發展中的經驗,推動受援國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規模效應、實現開放式的工業化發展,從而促進受援國的經濟發展。截至2017年底,僅國家開發銀行和絲路基金對不發達國家所提供的對外援助已經超過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規模的總和(吳雨珊,2018)。因此,有必要對以開發性援助為主的中國對外援助在國際援助中的角色進行定義。本文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援助定義和理念,講好中國援助故事,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
本文以下部分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顧了資源生成理論、提出新的國際援助界定方法,并給出該方法與現有國際援助報告系統的銜接,第三部分分析不同類型中國對外援助對受援國的影響,第四部分是結論性評述。
二、資源生成理論和資源配對援助法
(一)資源生成理論
中觀經濟學的資源生成理論將資源分為可經營性資源、準經營性資源和非經營性資源三類。可經營性資源與產業發展相對應,非經營性資源與民生保障相對應,準經營性資源與市政軟硬件基礎設施相對應。
1.可經營性資源
可經營性資源xj的總量等于每一個個人或企業i對這種可經營性資源的擁有數量之和,可經營性資源在個人或企業之間是可分的。可經營性資源可以用如下公式表達:
可經營性資源對應產業資源,主要反映的是私人部門資本的投資和積累,與人口、科技水平等生產要素一起,對社會的經濟產出起主要推動作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資本存量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是包括固定資產存量在內的所有過去和現在投入到生產過程中物品的價值總和。對于進出口保持均衡的市場經濟體,增量的可經營性資源主要來自于當期國民經濟產出扣除當期私人部門消費支出和當期政府購買支出:
2.準經營性資源
準經營性資源具有有限的非競爭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以城市資源為主,主要包括保證國家或區域的社會經濟活動正常進行的公共服務系統和為社會生產、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軟硬件基礎設施,如交通、郵電、供電供水、園林綠化、環境保護、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事業等城市公共工程設施和公共生活服務設施等。完善的軟硬件基礎設施促進各國、各區域的社會、經濟等各項事業發展,推動城市空間分布形態和結構的優化。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既可由企業來承擔,也可由政府來完成。因此,準經營性資源兼備公共物品與私人產品的特征(1)隨著時間的推移,準經營性資源可能轉化為可經營性資源或非經營性資源。限于現有數據庫,本文主要分析援助國提供開發性援助時注入資源的性質,無法從實證方面追蹤準經營性資源的時序變化。。
(1)增量的準經營性資源
在經濟體的發展初期,各項基礎設施比較落后,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進行建設,這個階段政府投資在準經營性資源所占比重較大。隨著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在經濟體發展建設的中期,各方面建設逐漸發展成熟,居民可支配收入逐漸增加,政府投資逐漸下降,私人投資開始上升,此時私人部門有能力和意愿投資準經營性資源,當期的準經營性資源轉換為可經營性資源的比例逐漸提升。當期新增的準經營性資源可以從一開始就遵循采用獨資、合資、合作或股份制等形式組建項目公司,直接轉化為可經營性資源。增量的準經營性資源對可經營性資源的轉化可以用如下公式表達:
xq=(1-λ)xj
變量λ(0≤λ≤1)表示增量準經營性資源在公共部門當中的配置比例。理論上的極端情況下,如果λ為0,則準經營性資源完全屬于私人部門,即被轉換為純粹的可經營性資源;如果λ為1,則準經營性資源完全由公共部門所有。增量準經營性資源是轉變為可經營性資源,還是非經營性資源,由當地市場經濟發展程度、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和社會民眾的認知程度決定。
(2)存量的準經營性資源
在經濟體發展建設的中后期,居民可支配收入較高、社會財富積累,同時社會經濟發展速度減緩,私人部門投資風險提升、投資回報率降低,居民對準經營性資源投資的投資意愿較高。通過對區域原有的存量資產進行股權改造優化,當期的準經營性資源全部轉換為可經營性資源,存量的準經營性資源逐漸轉換為可經營性資源。存量準經營性資源對可經營性資源的轉化可以用如下公式表達:
變量ε(0≤ε≤1)表示存量準經營性資源在當期對可經營性資源的轉化比例。理論上的極端情況下,如果ε為0,則當期無存量準經營性資源轉化為可經營性資源;如果ε為1,則所有存量準經營性資源都轉化為可經營性資源。存量準經營性資源對可經營性資源的轉化程度,由當地市場經濟發展程度、市場真實利率水平和投資回報率等因素決定。
3.非經營性資源
任何一個消費者i都可以支配非經營性資源,其總量是xm,非經營性資源在個人或企業之間是不可分的。非經營性資源可以用如下公式表達:
非經營性資源反映了一個經濟體全體組成成員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是一種現實存在的購買力,由政府作為實施主體,以政府財政收入和政府負債作為支付來源,對應的是政府消費性支出。社會成員對非經營性資源的占有不因個體的地位和收入有所區別,每個社會成員對非經營性資源的消費機會均等。存量的非經營性資源對整個社會福利的影響主要由其微觀效用函數進行作用。
(二)資源配對援助法
對應資源生成理論對資源種類的劃分方式,本文提出資源配對援助法,將國際援助劃分為商業性援助、開發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三類。
1.商業性援助
商業性援助是向受援國提供可經營性資源的一種國際援助,主要包括對被援助國家產業資源部門的援助,是帶有援助性質的商業行為。如表1第2行所示,援助國政府對商業性援助的管理主要基于對可經營性資源的調配,與之相匹配的管理原則是“規劃、引導,扶持、調節,監督、管理”。

表1 三類國際援助類型
商業性援助的主要涉及部門是私人部門。項目實施主體包括公司、企業、商業銀行和私人投資者等。援助提供方式包括公司企業對受援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企業社會責任投入,商業銀行對受援國的商業貸款、出口信貸、融資擔保,以及私人投資者對受援國的直接股權投資及投資組合等。
2.開發性援助
開發性援助是向受援國提供準經營性資源的一種國際援助,主要包括對受援國社會經濟活動正常進行的公共服務系統和為被援助國家社會生產、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軟硬件基礎設施的支持,包括城市硬件基礎設施建設、城市軟件基礎設施開發、智能城市項目建設等,如交通、郵電、供電供水、園林綠化、環境保護、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事業等城市公共工程設施和公共生活服務設施。如表1第3行所示,援助國政府對開發性援助的管理主要基于對受援國準經營性資源的生成,可以視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的合作和分工狀況來確定,利用政府部門的信用和資金優勢、配合私營部門的經營與技術優勢,采取“政府推動,企業參與,市場運作”的原則進行。
開發性援助的主要涉及部門包括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項目實施主體主要是援助國雙邊機構以及國際和區域性多邊機構,包括德國復興信貸銀行等傳統援助國開發銀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新興援助國的發展銀行和發展基金,也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等國際性發展組織,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區域性發展銀行和歐盟等區域性發展機構。開發性援助的援助提供方式包括對外貿易貸款、對外投資貸款、專項合作基金和投資基金等。
3.公益性援助
公益性援助是向受援國提供非經營性資源的一種國際援助,即對受援國社會公益產品和公共物品的支持,包括經濟保障、歷史、地理、形象、精神、理念、應急、安全、救助,以及區域的其他社會需求等。如表1第4行所示,援助國政府和公益機構對公益性援助的管理主要基于對受援國非經營性資源的補充,與之相匹配的管理原則是“社會保障,基本托底,公平公正,有效提升”。
公益性援助的主要涉及部門包括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項目實施主體包括政府部門中的雙邊機構、多邊機構、全球性公益計劃等,以及私人部門中的非政府組織、慈善機構等。援助提供方式包括世界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雙邊及多邊機構提供的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和優惠貸款等援助方式,多邊機構及全球性公益組織提供的聯合國專家志愿者、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全球環境基金、全民教育快車道倡議等全球性公益援助項目,也包括了全球性非政府組織、援助國和受援國非政府組織所提供的公益性支持,以及私人慈善機構、慈善基金發起的公益性項目和慈善個人的捐贈匯款等。
(三)資源配對援助法與現有援助定義的區別及聯系
現有的ODA概念無法吸納新興援助國的援助和私人部門創新性的發展援助資金,需要修正和改革。在國際層面,世界銀行在2001年提出“全球發展融資”(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的概念,指代所有投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流(世界銀行,2001)。聯合國首腦會議千年發展目標提出“創新發展融資”(Innovative Development Finance),指代所有為發展籌集資金以補充ODA的非常規籌資方式(聯合國,2012)。OECD在2014年提出“官方對可持續發展總支持”(Total Official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簡稱TOSSD)的概念,包括了官方直接提供和官方撬動的、用以促進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所有優惠及非優惠資金。在國內層面,我國2021版《對外援助管理辦法》將對外援助定義為“使用政府對外援助資金向受援方提供經濟、技術、物資、人才、管理等支持的活動”,強調援助的官方性并按援助提供方式進行分類,“援助資金主要包括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和優惠貸款三種類型”,同時“通過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方式創新對外援助形式”。
以上對國際援助的定義方式主要有兩點分歧:第一,廣義還是狹義,是否應該將所有用于發展的資金,無論是政府資金還是私人資金、無論通過何種援助方式、無論受援國是否是最不發達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都劃分為國際援助,還是取其中的部分;第二,改良還是創新,是圍繞著現有的ODA的定義來進行補充和擴大,還是另起爐灶重新界定新的國際援助定義和統計規則。本文提出的資源配對援助法為解決這兩點分歧提供了參考。
對于第一點,資源配對援助法的分類方法可以吸納所有促進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援助資金。資源配對援助法將國際援助按對受援國的資源注入類型來分類,意味著援助的優惠程度、資金來源、提供方式和附加條件等方面的區別被淡化。無論是官方行為還是市場行為,國際援助只是一種對受援國的資源注入,與援助國和受援國的國內制度和政治環境無關。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都可以直接提供和間接撬動公益性援助、開發性援助和商業性援助。只要能夠發展生產力的資源注入,都可以在國際援助的實踐中使用。
對于第二點,資源配對援助法是一種基于資源注入和配對的分類方法,在統計上與ODA的定義并行不悖。在下一節里,我們根據經合組織債權人申報系統(Creditor Reporting System,簡稱CRS)將ODA解構,并與資源配對援助法進行銜接。TOSSD尚處于討論階段,具體的統計規則和準入標準尚未確定,但預計也會使用CRS作為申報準則。因此,資源配對援助法也可以與TOSSD相互對接,便于贏得更為廣泛的國際認同與支持。
(四)資源配對援助法與經合組織債權人申報系統的銜接
現有的全球援助匯總和分類系統中,以經合組織債權人申報系統(CRS)使用最為廣泛,國際援助透明度倡議(IATI)和援助數據(AidData)等援助數據庫均普遍使用CRS的行業分類和代碼。CRS的主要申報人包括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簡稱DAC)成員國、非DAC成員自愿申報國和多邊機構等,申報的內容是ODA,涉及的援助類型主要是公益性援助和開發性援助。
CRS一級子目錄共八項。根據CRS二級子目錄和三級子目錄的解釋說明,我們將其與援助國向受援國注入的資源類別,以及援助類別相匹配,如表2(2)IV.多部門/跨部門援助和IX.未分配/未指定根據三級子目錄內容進行分類。限于篇幅,本文將上述分類置于附件,備索。。

表2 CRS對應援助類別表

圖1 CRS一級子目錄的分類
三、不同類型對外援助對受援國的影響
(一)模型設定
國際援助是對受援國公共支出的直接補充,開發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補充了受援國的公共投資和公共服務,從而影響受援國的經濟增長。過往研究表明,公共支出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決定因素,公共服務和公共投資兩者都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影響(Barro,1990;Ghosh and Roy,2004)。開發性援助作為一種額外的公共資本投入,直接進入生產函數從而影響經濟產出。公益性援助不僅作為額外的公共服務進入生產函數,而且在預算緊張的前提下改變了受援國的需求結構、增加了受援國公共產品的消費。然而,此前對國際援助、公共支出以及經濟增長的聯系相關的研究較少(Agénor et al.,2008;Chatterjee et al.,2012)。聯合國千年大會以來,國際援助的主要目標逐漸由消除貧困轉向推動經濟發展,主要援助國和新興援助國紛紛采取了各種新型的援助手段。因此,有必要重新檢驗國際援助構成與受援國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這一命題。基于資源配對援助法的定義和分類,本文提出以下兩點假說:
假說1:公益性援助和開發性援助都對受援國經濟發展有正向影響。
以往文獻研究普遍證實了各類基礎設施投資(3)以往文獻提到的基礎設施普遍包含了準經營性資源和非經營性資源。對經濟的正向影響,例如,Barro(1990)為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內生影響提供了理論基礎,Aschauer(1989)、Jumbe(2004)等學者都從實證的角度驗證了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雖然部分學者的研究發現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有反向影響,但是,反向影響普遍發生在基礎設施投資累積到一定程度的情況(廖茂林等,2018)。受援國往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非經營性資源和準經營性資源都十分匱乏。因此,公益性援助和開發性援助都對受援國經濟發展具有正向影響。
假說2:開發性援助對受援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更直接并且強烈,公益性援助對受援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更間接并且持久。
直觀而言,公益性援助通過人們對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社會公共產品的消費行為影響其效用,從而對社會生產和經濟發展產生作用,過程較為間接,發揮作用的時間更漫長;開發性援助通過對城市軟硬件基礎設施的投資拉動經濟,直接進入生產函數對經濟發展產生作用,過程較為直接,由于直接影響產出,因此產生作用的時滯更短,作用更加明顯。因此,開發性援助對受援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更直接并且強烈,公益性援助對受援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更間接并且持久。
基于以上理論假說,本文借鑒張原(2018)的模型設定,以受援國經濟增長為被解釋變量,以各個受援國得到中國援助的規模與結構及其滯后項為核心解釋變量,考察中國對外援助對受援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具體的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lnGDPmit=α1lnAidit+α2lnAidi,t-1+φXit+λi+χt+μit
(1)
lnGDPmit=β1lnGAit+γ1lnWAit+β2lnGAi,t-1+γ2lnWAi,t-1+φXit+λi+χt+μit
(2)
公式(1)和(2)分別用于評估總援助規模與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其中,Xit表示i國第t年的經濟增長情況,參照Dalgaard et al.(2004)、Rajan and Subramanian(2008)的做法,本文利用受援國的實際人均GDP反映受援國經濟增長情況;Aid表示受援國得到的中國援助規模,GA和WA分別表示開發性援助規模和公益性援助規模;lnAidi,t-1表示i國在第t-1期得到的總援助規模,lnGAi,t-1和lnWAi,t-1分別表示i國在第t-1期得到的開發性援助和公益性總援助規模;Xit為控制變量,參照朱丹丹、黃梅波(2018)、嚴兵等(2021)、盧晨、張樹濤(2021)等文獻,本文的控制變量包含DAC成員國的對外援助規模、政府支出規模、制度質量、外國直接投資(FDI)、對外貿易、城市化水平、人口規模和衛生健康狀況;α、β、γ和φ為待估參數;λi和χt分別表示個體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μit為殘差項。
(二)變量選擇與變量描述
被解釋變量為受援國的經濟增長情況,本文采用受援國的實際人均GDP進行反映,此變量以2014年為基期進行度量與換算,并取對數,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的WDI數據庫。
核心解釋變量為總援助規模、開發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規模,數據來源于AidData數據庫。上述三個核心解釋變量同樣以2014年為基期進行度量與換算,并利用GDP平減指數對總援助規模與結構的名義值進行處理。本文刪除了總援助規模觀測值缺失連續兩年及以上的國家樣本,最終得到2003-2014年期間中國對58個國家的援助數據,共696個樣本(4)在AidData的原始數據庫中,中國對外援助的國家有106個,其中,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的受援助國分別有50、23、28和5個。。
除此之外,參照朱丹丹、黃梅波(2018)等文獻,本文控制了一系列相關變量,包括政府、商業、人口和衛生等多方面以及DAC成員國的對外援助規模。(1)在政治制度方面,本文選取政府支出規模與政府效能作為政府層面的控制變量。其中,政府效能數據來源于全球治理指數(WGI)數據庫,用于反映受援國的制度質量。政府效能數據的取值范圍為-2.5至2.5,并且數值越大代表政府效能越高。(2)在營商環境方面,本文選取外國直接投資(FDI)和對外貿易來反映,FDI和對外貿易越高意味著該國的營商環境越好,對外資的吸引力越強。(3)在人口方面,本文選取人口規模和城市化水平來衡量,前者用于衡量受援國的勞動資源豐裕程度,后者用于衡量受援國的城市經濟發展狀況。(4)在衛生健康方面,出于數據的可得性考慮,本文根據WDI數據庫的指標,選取受援國得了瘧疾的人數來衡量,受援國的衛生環境較好,得瘧疾的人數會相對較少(5)限于現有數據,本文在實證分析中只考慮了公益性援助和開發性援助,沒有考慮商業性援助,但加入了外國直接投資作為控制變量。。(5)參照李嘉楠等(2021),本文還控制了OECD國家對外援助規模。
上述變量的具體定義及描述性統計見表3。

表3 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分析
1.總援助規模與經濟增長
表4報告了總援助規模對受援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根據第(1)列的回歸結果,總援助規模對受援國實際人均GDP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與朱丹丹、黃梅波(2018)等文獻的研究結果一致。在控制變量中,受援國的政府支出、政府效能、對外貿易、城市化水平、人口規模都與該國的實際人均GDP水平呈顯著正相關;而得了瘧疾的人數越多(衛生條件較差)對GDP水平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FDI和DAC成員國對外援助規模雖然產生正向影響但不顯著。根據第(2)列的回歸結果,總援助規模平方項對受援國實際人均GDP產生正向影響但不顯著,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與第(1)列相似。根據第(3)列的回歸結果,滯后一期的總援助規模對受援國實際人均GDP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意味著對外援助的經濟效應具有滯后性,與張原(2018)的研究結果一致。

表4 總援助規模與受援國經濟增長
2.援助結構與經濟增長
進一步地,本文分析了援助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估計結果見表5。其中,援助結構包括開發性援助(lnGA)和公益性援助(lnWA)。由表5第(1)列可知,在引入控制變量、時間和個體固定效應的基礎上,開發性援助對受援國的實際人均GDP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公益性援助產生的正向影響不顯著。此外,開發性援助的邊際影響大于公益性援助的邊際影響。在此基礎上,本文引入開發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的平方項,發現開發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都對受援國實際人均GDP產生先降后升的“U型”作用。可能的原因是開發性援助存在門檻效應,只有超過該門檻才能對經濟增長產生促進作用,與朱丹丹、黃梅波(2018)的研究一致。此外,本文依次引入滯后一期的開發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考察對外援助對受援國經濟增長的滯后效應。可以看出,滯后一期的開發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都對受援國實際人均GDP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且開發性援助的邊際影響仍舊大于公益性援助的邊際影響。因此,開發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對受援國經濟增長存在門檻效應,而且開發性援助產生的影響更大。

表5 援助結構與受援國經濟增長
3.援助作用的異質性分析
為考察援助作用的異質性,本文分別以聯合國標準和樣本國家實際人均GDP均值來判斷受援國是否為低收入國家(或貧困國家),估計結果見表6。其中,2014年聯合國界定貧困國家(即最不發達國家)的標準是人口低于7500萬且人均GDP低于900美元/年。

表6 異質性分析:是否為低收入國家
由表6可知,如果按照聯合國標準劃分,對于收入水平相對較高的國家,只有開發性援助對受援國實際人均GDP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對于收入水平相對較低的貧困國家,對外援助規模對受援國實際人均GDP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且這種正向影響主要來源于開發性援助的促進作用。如果按照樣本國家實際人均GDP的均值水平劃分,無論是收入相對較高還是相對較低的國家,援助總規模都對受援國實際人均GDP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且對收入相對較低國家的邊際影響更強。
4.援助的內生性問題分析
進一步地,對外援助與受援國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互為因果的內生性問題,表現為:一方面對外援助規模與結構都會影響受援國的經濟增長情況,另一方面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也會影響中國政府的對外總援助規模與結構。本文參照Nunn and Qian(2014)、Dreher et al.(2017)、李嘉楠等(2021)的做法,使用t-1期的中國鋼材產量(CHN_Steel)與受援國在樣本期間接受中國援助的頻率的交互項作為國際援助的工具變量。具體地,本文構造三個工具變量,包括:CHN_Steel×Aid_times、CHN_Steel×DA_times、CHN_Steel×PA_times,分別解決lnAid、lnGA和lnWA的內生性問題。因為鋼鐵生產是中國的優勢產能,而產能過剩程度主要取決于國內的產業布局和經濟周期,會影響中國的對外總援助規模與結構,但不會受受援國經濟發展的影響(Dreher et al.,2017)。因此,本文的工具變量外生于受援國經濟增長,能較好地解決內生性問題。
表7報告了利用工具變量法來解決國際援助內生性問題的估計結果。根據第(1)列和第(2)列的估計結果,總援助規模對受援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都高度顯著,且第一階段F值都超過了弱工具變量的經驗值10。不過,引入控制變量之后總援助規模的邊際效應具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根據第(3)和第(4)列的估計結果,工具變量(CHN_Steel×DA_times)的第一階段F值都大于10,并且開發性援助對受援國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根據第(5)列和第(6)列的估計結果,雖然工具變量(CHN_Steel×PA_times)的第一階段F值略小于10,但是公益性援助對受援國經濟增長仍舊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此外,相較于表5和表6的估計結果,解決內生性問題之后,lnAid、lnGA和lnWA對受援國實際人均GDP的促進作用更大。

表7 總援助規模與結構的內生性問題分析:工具變量法
四、結論性評述
本文從中觀經濟學的視角,回答了國際援助研究中的一個經典問題——不同類型國際援助對受援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首先,本文是中觀經濟學理論的實際應用。資源生成是中觀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基礎性理論,對應資源生成理論中的非經營性資源、準經營性資源和可經營性資源,本文提出資源配對援助法,將國際援助分為公益性國際援助、開發性國際援助和商業性國際援助等三類。
其次,本文提供了國際援助統計口徑的新思路。ODA強調政府部門的主導性及援助內容的優惠性,而本文提出的分類方法能夠廣泛吸納各種非政府部門的援助手段和創新發展的融資工具,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前瞻性,同時也能夠與現有的經合組織CRS系統有效銜接。中國高度重視對外援助的透明性,先后發布三本對外援助和國際發展合作的白皮書,卻仍因沒有加入OECD發展援助委員會并按CRS準則申報對外援助數據,而受到海外輿論的抨擊非議。OECD嘗試通過建立TOSSD,吸納新興援助國家接受DAC既有規則的制約,但這一概念目前仍處于討論階段。本文的分類方法為國際社會理解中國對外援助和國際合作行為,提供了新的切入點。
最后,本文發展了國際援助研究的文獻。文章指出國際援助的著眼點是資源生成,國際援助通過注入資源推動受援國社會經濟發展。傳統援助國偏重于提供公益性援助,偏重于減少貧困和制度建設,對開發性援助關注較少。因為融資方式和資金投向的不同,中國以開發性援助為主的對外援助受到了很多國外輿論的質疑。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開發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存在門檻效應和滯后性,兩者都對受援國經濟發展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且開發性援助對受援國經濟發展促進作用要強于公益性援助。因此,傳統援助國和新興援助國都應該設定多樣性的援助目標,并采取差異化的援助手段,讓國際援助更富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