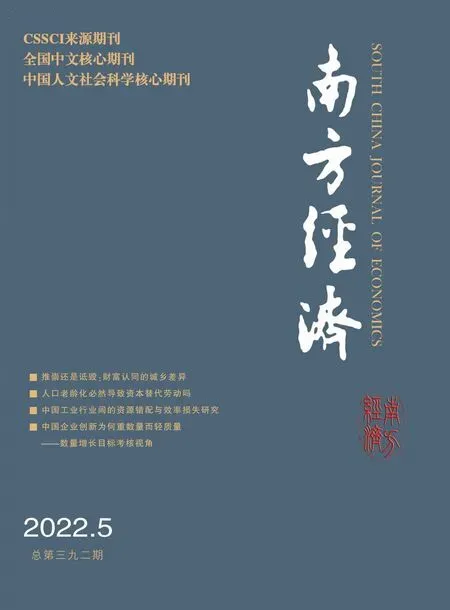合作研發中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的影響:技術差異和管理差異的調節作用
王晨風 韋詩豪
一、引言
合作研發被認為是彌補我國企業創新中的薄弱環節的重要途徑,被企業廣泛使用(白讓讓、譚詩羽,2016)。然而,大量合作研發并沒能達成預期目標,取得的績效水平明顯低于預期(Lhuillery et al.,2009;Okamuro,2007)。因此,識別影響合作績效的前因變量,進而發現導致合作研發沒能達成預期目標的原因就有重要意義。現有研究指出:合作研發的治理機制、合作各方的投入、合作各方的知識交流與共享、合作項目的特點等對合作績效都有重要的影響作用(蘇中鋒,2018;李玲,2011;孫永磊等,2014;蘇中鋒等,2016)。其中合作各方投入的專有投資被看作是合作研發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向麗、胡瓏瑛,2019;于茂薦,2018;余海晴等,2020;Dyer and Singh,1998)。在合作研發過程中,雙方都會進行專有投資,尤其是投入所擁有的獨特資產來實現優勢互補,進而實現合作研發目標(Wu,2016;Oxley,1997;Sampson,2004)。那么,專有投資能提高合作績效嗎?針對該問題,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 theory)和關系交換理論(Relational exchange theory)存在截然不同的觀點。其中,交易成本理論認為專有投資會提高交易成本,進而妨礙合作研發活動的開展,因此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有負面影響(Wu,2016;Williamson,1981;Yu et al.,2006);而關系交換理論認為專有投資體現了合作方對合作關系的承諾,可以增進合作各方的理解與信任,對合作績效有正面作用(Zhao et al.,2014;Lui et al.,2009;Dyer and Singh,1998)。那么,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到底有什么樣的影響呢?現有理論卻無法提供明確答案,使其成為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Wu,2016;Okamuro et al.,2011)。
本文認為上述對立觀點主要由兩方面原因所導致。第一,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的影響不僅取決于合作各方投入的總數量(專有投資總量),還取決于各方投入數量的差異(專有投資差異)(Wu et al.,2017;Aparicio,2001;Ojala and Hallikas,2006)。例如,有兩個合作研發項目,專有投資總量都是100單位,其中一個是合作雙方各投入50單位專有投資,而另一個合作研發項目中雙方分別投入99單位和1單位,兩個合作研發的績效非常可能存在巨大差異。因此,分析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的影響,不僅要關注專有投資總量,更要關注專有投資差異。遺憾的是,現有研究未能將專有投資進行細化(Vitta et al.,2011;王節祥等,2015;Vitta et al.,2010),僅僅關注了專有投資總量的作用,忽略了專有投資的差異(Aparicio,2001),成為現有研究的一個不足。
第二,專有投資所發揮的作用會受到合作各方差異的影響。一方面,合作各方存在差異才能保證各方專有投資存在互補關系,實現優勢互補;但該差異也可能導致各方專有投資難以融合,進而影響專有投資作用的發揮。另一方面,合作各方的差異可能使得各方更容易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使得專有投資導致的交易成本增大(Trada and Goyal,2017;Wang et al.,2013);但是,差異使各方更強調通過專有投資來對合作關系進行承諾,使專有投資產生更大的價值(Su and Bao,2018;余海晴等,2020)。也就是,合作各方的差異不僅影響專有投資發揮的作用,而且影響交易成本理論和關系交換理論對專有投資作用的解釋力度。因此,對專有投資和合作績效關系的研究必須關注合作各方差異的調節作用。然而,現有研究對合作各方差異少有涉及,成為另一個研究不足。
為了深入認識合作研發中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的影響,針對上述研究不足,本文重點關注合作研發中專有投資總量和差異與合作績效的關系,以及合作雙方在技術和管理方面差異對上述關系的調節作用。通過對140個合作研發問卷調研所獲取數據開展實證檢驗,本文發現:專有投資總量對合作績效有促進作用,而專有投資差異對合作績效有負面影響。同時,合作伙伴間的技術差異和管理差異是影響專有投資與合作績效關系的重要情境因素。本文研究系統分析了合作研發中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的影響,不僅有助于豐富對影響合作績效前因變量的認識,而且有助于深入認識合作研發中專有投資的價值,尤其是解釋交易成本理論和關系交換理論對專有投資價值認識方面的不一致問題。在實踐方面,本文研究可以指導企業更加有效的對合作研發開展專有投資,并更好的利用專有投資來提高合作研發的績效,實現合作研發的目標。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合作研發
合作研發是指企業、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組織機構,以規避創新風險、分擔研發投入、縮短研發周期、實現優勢互補等為目的而形成的合作關系,它以合作成員的共同利益為基礎,以合作創新為目的,以優勢資源互補為前提(王龍偉等,2011)。學者們從不同的領域和角度研究了合作研發對合作績效的影響,并普遍認為合作研發可以有效提高合作績效(Shin et al.,2016;Tomlinson,2010;Dahlander and Gann,2010;王龍偉等,2011)。原因是:第一, 合作研發能夠將知識溢出內部化,同時促進合作伙伴間自愿的知識分享和創新投資(初大智等,2011),有助于企業之間的知識交流和轉移(王龍偉等,2011)。具體來說,在企業間合作研發過程中,雙方可以通過契約等明確規定來實現轉移生產工藝技術、技術專利等顯性知識交流,同時企業間通過合作研發關系的建立,雙方相互派駐技術人員參與到對方的生產、新產品開發等活動之中,并共同解決各種技術性問題,這些都會促進合作各方知識的轉移和學習(Benn Lawson et al.,2009)。第二,合作研發可以彌補單個企業創新資源不足的限制,確保企業創新活動的順利開展(王龍偉等,2011)。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技術創新難度增大,重大科技項目的組織和實施日趨復雜,單個企業在創新過程中更容易受限于技術、資金、知識等資源的不足。合作研發則通過與不同的外部組織進行知識資源共用等方式打破這一桎梏。例如,Ragatz(2005)發現,企業與其合作供應商之間的密切合作有利于企業獲取與應用技術,從而縮短項目開發周期,降低項目開發成本。第三,合作研發有助于提高創新水平。初大智等(2011)通過對廣東省五大類制造產業421家企業的調研,發現合作研發對創新水平具有重要的正向影響,有助于加快新產品的市場化進程,提高企業新產品商業化速度和成功率(Yuan Li et al.,2008)。因此,合作研發被大量企業采用,在“2014年全國企業創新調查資料開發”課題組調查的企業中,開展了創新合作的制造業企業約9.3萬家,占制造業企業的比重為26.4%。
然而從實踐結果來看,大量合作研發并沒能達成預期目標,取得的績效水平明顯低于計劃值(Okamuro,2007;Lhuillery et al.,2009)。因此,大量學者開始識別影響合作績效的前因變量,以求發現導致合作研發沒能達成預期目標的原因。現有研究已經發現:合作研發的治理機制、合作各方的投入、合作各方的知識交流與共享、合作項目的特點等對合作績效都有重要的影響作用(蘇中鋒,2018;李玲,2011;孫永磊等,2014;蘇中鋒等,2016)。其中合作各方投入的專有投資被看作是合作研發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向麗、胡瓏瑛,2019;于茂薦,2018;余海晴等,2020;Dyer and Singh,1998)。在合作研發過程中,雙方都會進行專有投資,尤其是投入所擁有的獨特資產來實現優勢互補,實現合作研發的目標(Wu,2016;Dyer and Singh,1998)。那么,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的影響究竟如何呢?
(二)專有投資
專有投資是由資產專用性演化而來,指的是主體的投資行為具有特定性,它是一種專門用于協作的不可重新部署的投資(Vita et al.,2010):假如投資的手段和目的發生改變,勢必會造成其價值的損失。專有投資是企業間合作的關鍵要素,合作伙伴根據任務需要建立合作關系,在合作中合作雙方均需要投入特定的專有資產,結成一種固定的戰略關系,并且合作雙方在長期的合作中共享生產資源和市場信息(孫超,2018)。那么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會產生什么影響呢?現有理論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解釋:交易成本理論認為專有投資是交易成本的來源,并且認為專有投資帶來的這種負面效應隨著資產專用性的增加而增加(Williamson,1981),不利于提升合作的績效(Wu,2016;Yu et al.,2006),但關系交換理論認為專有投資作為將各方聯系在一起的工具(Dyer and Singh,1998;Saxton,1997),體現了對合作研發伙伴的承諾并促進了各方之間的合作,從而有利于提高合作研發的績效(Lui et al.,2009;Dyer,1997)。這一爭論導致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的影響變得不明確。本文認為這種互相矛盾的解釋主要是目前的研究局限造成的:現有文獻強調合作研發各方的總專有投資,而忽視了合作伙伴間專有投資差異所起的作用(Aparicio,2001;Ojala and Hallikas,2006)。專有投資差異導致各方對合作的承諾不同,加劇了機會主義的危害,從而影響了合作績效(Dyer,1997;Pemartín and Rodríguez,2017)。同時,學者們認為協作很少是對稱的,他們研究了權力和能力等幾個方面的不對稱性,并且認為不對稱在合作中具有重要意義(Yang et al.,2015;Bretherton and Carswell,2002;Hingley,2005)。然而,卻很少有研究調查過專有投資差異在合作研發環境中對合作績效的重要影響(Pemartín and Rodríguez,2017)。由于總專有投資和專有投資差異所起的作用區別很大(Aparicio,2001),在這方面研究的缺失導致我們對專有投資與合作績效的關系的認知不夠充分(Dyer,1997)。為了更深入地探討二者之間的關系,本文從專有投資的兩個方面:專有投資差異和總專有投資入手,研究它們對合作績效的不同影響。
1.專有投資差異
本文認為專有投資差異對合作績效有負向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專有投資差異會妨礙合作研發伙伴間的協作。關系交換理論認為專有投資代表對合作的承諾,是一種聯系合作伙伴關系的工具(Dyer and Singh,1998;Saxton,1997)。當專有投資差異處于較高水平時,各方投入的專有投資數量存在較大的差距,表示各方對合作有不同程度承諾,這會妨礙合作各方的協作(Dyer,1997)。第二、交易成本理論認為專有投資是交易成本的一項來源。在專有投資存在較大差異的情況下,會導致較高的交易成本。具體來說,專有投資是一種專門用于協作的不可重新部署的投資,當雙方專有投資存在不對稱時,投入少的合作伙伴利用討價還價、終止合作等威脅的手段,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從這些專有投資中攫取回報(Klein et al.,1978),導致較高的交易成本。因此專有投資差異降低了合作中的有效協調,增加了機會主義的危害,阻礙了合作伙伴間獲得激勵的一致性,不利于合作研發目標的實現和績效的提升。由此可得:
假設1:合作研發伙伴間專有投資差異對合作績效有負向關系。
2.總專有投資
本文認為總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的影響是正面的,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專有投資有助于滿足研發活動的資源需求(Wu et al.,2017)。合作研發的一個突出優勢是各方可以從合作伙伴處獲取補充資源并且共享研發成本(Yu et al.,2006;Bretherton and Carswell,2002),當合作各方共同將大量的專有投資用于合作研發時,研發活動不僅可以利用更多的資源,而且更有可能享受整合各合作伙伴提供的補充資源所產生的協同效應(Aparicio,2001;Rokkan et al.,2003),從而更有利于研發目標的實現和合作績效的提升。
第二,總專有投資促進了合作各方之間的協調:根據關系交換理論,專有投資體現了合作各方的承諾,并且可作為將各方聯系在一起的工具(Lui et al.,2009;Dyer and Singh,1998;Saxton,1997)。當合作各方投入的總專有投資處于較高水平時,表示對合作研發的承諾也就越大,這種承諾可以降低合作中的機會主義行為,使得合作伙伴間更容易建立信任關系,協調變得更加容易(Wu,2016;Lui et al.,2009;黃嘉欣等,2015),進而有利于合作目標的實現。
第三,由于合作研發比其他類型的合作具有更高的風險和更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各方在選擇合作伙伴時會更加謹慎(Diestre and Rajagopalan,2012)。專有投資作為交易成本的來源所起的作用在高承諾水平的合作研發中可能不像在其他類型的合作中那么重要(Lui et al.,2009)。因為,總專有投資高時所代表的是雙方對于合作高程度的承諾,這種承諾可以有力地抑制“敲竹杠”等機會主義的發生,很難產生較高的交易成本,使得專有投資不利于合作績效的影響處于弱勢水平。
因此,總專有投資越高,研發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壽志鋼,2012)。由此可得:
假設2:合作研發伙伴間的總專有投資與合作績效有正向關系。
(三)技術差異和管理差異的調節作用
總專有投資和專有投資差異對合作績效有著不同的影響,同時,其所發揮的效果和面臨的情境緊密相關(Fryxell et al.,2002)。例如,利用高水平的總專有投資來促進合作研發目標的實現必須保證識別合作伙伴的技術知識技術實力等優勢,進而才能通過總專有投資更好地實現資源互補和共享,提升合作績效。因此,為了深入認識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的作用,還需要考慮情境因素的影響。本文認為合作研發伙伴間的差異是一個重要的情境要素。一方面,合作各方存在差異才能保證各方的專有投資之間存在互補關系,實現各方的優勢互補;但是,該差異也可能導致各方的專有投資難以進行融合,進而影響專有投資作用的發揮。另一方面,合作各方存在的差異可能使得各方更容易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使得專有投資導致的交易成本增大(Trada and Goyal,2017;Wang et al.,2013);但是,各方的差異使得各方更強調通過專有投資來對合作關系進行承諾,使得專有投資產生更大的作用和價值(余海晴等,2020;Su and Bao,2018)。
因此,為了深入認識專有投資與合作績效的關系,本文將進一步分析合作研發伙伴間差異對該關系的調節作用。本文重點關注合作研發伙伴在技術和管理兩個方面的差異。其中,技術差異主要體現在合作伙伴在技術知識和技術實力方面的差異,管理差異主要涉及合作伙伴在管理風格和企業文化方面的差異(Kelly et al.,2002)。選擇管理差異與技術差異做自變量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考慮到在創新管理研究領域,學者們將創新分為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而合作研發的目標也是開展管理創新與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和合作研發伙伴的技術密切相關,管理創新與合作伙伴的管理方式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考慮到,在合作研發中要取得良好的績效,不僅需要合作雙方在管理活動上的相互協調配合,也很大程度上依賴合作雙方達成技術上的互補(Okamuro,2007),可見合作伙伴間的技術和管理差異對合作研發都有重要影響。因此本文重點關注合作研發伙伴在技術和管理兩個方面的差異,分析其對專有投資與合作績效的關系的調節作用。
1.技術差異對專有投資差異與合作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
在實踐中,合作各方因發展方向以及知識積累過程的不同等使得各自的技術知識儲備有所差異,并且企業以往積累的技術知識往往會對其以后的技術活動選擇和開發產生影響(羅芳,2010),企業的技術發展因此會呈現出很強的歷史路徑依賴,這一特性使得不同企業的技術特色和技術適應群體等都有所不同,長此以往造成了不同的技術主體擁有的技術知識在質和量上產生很大的差別,從而形成技術差異。
關系交換理論認為,專有投資差異阻礙了合作伙伴之間的有效協調。而在研發過程中,如果合作雙方之間存在較大的技術差異,會加劇合作雙方的溝通障礙,導致雙方無法進行有效的知識共享,降低互動的有效性和知識轉移的效果(高孟立,2017),進而加劇了專有投資差異帶來的協調障礙,不利于資源和知識的整合,從而影響合作研發企業的價值創造活動。另外,交易成本理論認為專有投資差異會增加合作的交易成本。而在合作研發過程中合作伙伴的技術差異會導致合作各方無法準確預測和把握對方在合作研發過程中,特別是對技術知識的共享與交流過程中,是否履行了所做出的承諾、是否有對技術知識的濫用、是否有傷害合作伙伴利益的情況等,更加劇了機會主義等行為在這種環境中滋生的可能性(Sirmon and Lane,2004),從而增加了專有投資差異帶來的交易成本。由此可得:
假設3:技術差異負向調節專有投資差異與合作績效的關系,即技術差異增強了專有投資差異與合作績效的負向關系。
2.管理差異對專有投資差異與合作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
在實踐中,合作雙方因發展規模、經營環境以及文化制度與機制等的不同而使得各自的管理風格和企業文化存在差異,并且企業決策層構成、市場信息掌握情況以及設備與工藝等的不同會對其以后管理活動的實施產生影響,從而形成管理差異(才悅,2018)。
關系交換理論認為,專有投資差異損害合作雙方的有效協調以及阻礙研發活動的進展,導致對合作績效產生負面的影響。而合作研發伙伴間存在較大的管理風格差異以及企業文化差異時,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雙方的溝通、交流障礙,不利于知識的有效轉移和共享,降低了合作研發的協同效應,阻礙了合作研發活動的進展,加劇專有投資差異對合作績效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交易成本理論認為專有投資差異所帶來的較高的交易成本,也會因為合作雙方的管理差異而增加。具體來說,合作伙伴間較大的管理差異,使得雙方難以具備良好的配適度,也就難以建立積極穩健的合作關系,不利于合作各方準確評估和評價對方是否有故意夸大需求及改變事實描述等的行為(Aparicio,2001),這些問題同樣也增大了協調管理的難度,并且增大因沖突付出的成本和防范機會主義的成本,從而使得專有投資差異對合作績效的負面影響更加顯著。由此可得:
假設4:管理差異負向調節專有投資差異和合作績效的關系,即管理差異增強了專有投資差異與合作績效的負向關系。
3.技術差異對總專有投資與合作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
合作研發過程中雙方技術差異較大時,合作各方難以通過完備的契約以約束合作伙伴的行為,難以建立懲罰機制避免和預防機會主義行為(Lavie et al.,2012),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實現合作研發目標,合作各方之間會做出更高水平的承諾,從而建立良好的合作信任關系,促進和鼓勵合作伙伴實現更多的互惠行動,從而加大對合作研發的過程控制,減少機會主義行為的產生(Lui et al.,2009)。同時,高水平的承諾也會減少技術差異帶來的雙方員工交流溝通的障礙,確保合作雙方實現有效的知識分享,增強知識轉移的效果,更有利于資源的整合和協同效應的實現。因此在雙方技術差異較大的情況下,合作各方對合作的承諾變得尤為重要。根據關系交換理論,專有投資的投入量體現了這種承諾,因此雙方的技術差異較大時,總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的正向影響變得越強,越有利于研發目標的實現。相反,當合作研發雙方之間的技術差異較小時,合作雙方可以通過采取其他的手段來約束對方,例如建立完善的契約等,在這種情況下,總專有投資所體現的承諾對于合作績效雖然擁有正向的影響,但是其發揮的作用弱于合作伙伴間存在較大技術差異的情境。由此可得:
假設5:技術差異正向調節總專有投資和合作績效的關系。
4.管理差異對總專有投資與合作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
同理,當合作研發雙方管理差異較大時,合作伙伴在溝通、交流方面難免存在障礙,導致合作雙方簽訂的契約和規范不能有效地約束合作伙伴的行為,同時也難以有效利用懲戒機制預防和規避機會主義等不當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障雙方的協調溝通以及資源互補和共享,實現良好的合作績效,合作雙方更需要建立積極穩健的信任關系,通過對合作伙伴做出更高的承諾來減少合作中的機會主義行為等不良影響。此時,合作各方對合作的承諾就變得更加重要。根據關系交換理論,專有投資的投入量體現了這種承諾,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總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的正向促進作用變得更加顯著。因此在管理差異比較大的情況下,總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的正向關系會處于較強水平,正向影響作用變得更強。相反,Sirmon(2004)指出,當合作雙方之間的管理差異較少時,合作雙方可以通過其他一些手段如簽訂完善契約規范、建立懲戒機制等等來規避不合理行為。在這種情境下,總專有投資發揮的作用弱于合作雙方之間存在較大的管理差異的情境。由此可得:
假設6:管理差異正向調節總專有投資和合作績效的關系。
三、實證檢驗
(一)數據收集
本文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數據來驗證所提出的假設。在樣本選擇上,調查團隊從獲取的企業名錄中隨機抽取1200家企業作為調查對象。這些企業分布在安徽、廣東、河南、江蘇、陜西、上海等省市,可以避免單一地區抽樣可能造成的偏差。在問卷設計上,調查團隊參考現有文獻開發出問卷初稿,通過對多家企業進行預調研及與多位企業管理者討論來修訂問卷。在調查方法上,調查團隊采用面對面調查方式收集數據,并嚴格執行現場解決問卷填寫者疑問,以此保證回收的問卷填寫完整且有效。調查團隊成員在開展正式調查前接受了關于背景知識、問卷問題確切含義及訪談技巧的培訓。同時,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問題,調差問卷被設計成兩部分,并分別由同一單位兩名管理者獨立完成。調查團隊于2014年開展數據收集工作,共獲得249家企業數據。其中,140家企業開展了合作研發,因此本文最終樣本數為140家。為檢驗可能存在的未回答偏差問題,我們比較了參與和未參與調查企業的基本特征,沒有發現顯著差異。同時,我們根據企業同意參與調查的時間將樣本分兩組進行比較,沒有發現顯著差異(Armstrong and Overton,1977)。另外,140家開展合作研發的企業和109家沒有開展合作研發企業在基本特征方面也沒有顯著差異。因此,本文不存在未回答偏差問題。
(二)變量的度量
本文各變量的測量題項主要以國外現有的理論研究為基礎,同時根據部分專家學者和業內人士的探討意見進一步完善優化。除非特殊說明,所有變量均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法測量,“1”表示“很低”或“非常不同意”,“5”表示“很高”或“非常同意”,同意程度由1到5逐級遞增。
根據Okamuro et al.(2011)及Diestre and Rajagopalan(2012)的研究,本文采用四個題項的主觀量表對合作績效進行測量,具體包括:“合作研發取得了預期成果”,“合作研發實現了合作目標”,“合作研發取得了積極影響”,“合作雙方對合作結果滿意”。
基于Suh and Kwon(2006)的研究,并根據具體情況進行了修改,從而對專有投資進行測量,具體來說測量我方投入包括三個題項:“在合作過程中,我方投入了大量的專用型資產”,“在合作過程中,我方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如果中止合作,我方將面臨巨大的損失”;測量伙伴投入包括三個題項:“合作項目中伙伴方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合作項目中伙伴投入大量專用型資產”,“如果中止合作伙伴方將面臨巨大損失”。
本文主要借鑒Kelly et al.(2002)的研究,對技術差異進行測量,具體包括:“技術知識存在差異”,“技術實力存在差異”。對管理差異進行測量具體包括:“管理風格存在差異”,“企業文化存在差異”。
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企業年齡、企業規模、伙伴年齡、伙伴規模、技術不確定、市場不確定及競爭強度。以員工人數為依據量度企業規模,采用6點計分量表測量(1=少于50人,6=多于1000人)。技術不確定、市場不確定和競爭強度的指標參照Jaworski and Kohli(1993)的研究。具體測量指標見表1。

表1 變量的信度和效度
(三)信度與效度檢驗
信度指的是采用同樣的指標或測量工具重復地測量某相同事物時,得出相同結果的可能性。研究中某個指標或者測量工具的信度高,表明它得出的測量結果不會因為測量工具或者測量設計本身的特性產生變化。信度的分析檢驗通常采用Alpha系數鑒定評判,Alpha值的取值區間為[0,1],值越大,量表信度越好,說明相對誤差值越小,問卷的內部一致性就越好。其度量標準:當Alpha≥0.6 時,達到可接受水平;當Alpha≥0.8 時,量表信度很好;當Alpha≤0.6 時,達不到接受水平。此外,總量表的Alpha取值往往大于0.8,如果在0.7和0.8間,也達到了可接受水平。
效度則指的是某種測量工具能夠測量出其所要測量特性的正確性程度。效度越高,則表示測量結果越能展示所要測量的特征。對于度量指標的信度,本文采用了Alpha系數來衡量。由表1可得,所有變量的Alpha系數全都大于0.70,表明變量度量指標通過了效度檢驗(Fornell and Larcker,1981)。對于度量指標的聚斂效度,本文采用各變量測量指標的因子載荷進行衡量。由表1可得全部指標的因子載荷都大于0.70,具有良好的效度(Fornell and Larcker, 1981)。
四、分析結果
本文所有涉及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表2 描述性統計
本文采用多元回歸的方法檢驗所提出的假設。具體數據分析分為三步:首先,將企業規模、年齡、伙伴規模、年齡、技術不確定、市場不確定及競爭強度這7個控制變量加入到模型1中,分析控制變量的作用。然后將專有投資差異、總專有投資、技術差異和管理差異加入到模型2中,檢驗專有投資差異和總專有投資與合作績效的關系。最后,將專有投資差異和總專有投資與技術差異和管理差異的交互項加入到模型3中,檢驗技術差異和管理差異的調節作用。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問題,根據Aiken et al.(1991)的研究,本文對變量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回歸分析結果
模型2發現:專有投資差異和合作績效有負向關系(β=-0.181, p<0.01),支持了假設1;總專有投資和合作績效有正向關系(β=0.306, p<0.001),支持了假設2。模型3表明:專有投資差異和技術差異交互項對合作績效有負向的影響(β=-0.223, p< 0.05),專有投資差異和管理差異的交互項也有負向的影響(β=-0.328, p<0.001),說明技術差異和管理差異都負向調節專有投資差異與合作績效的關系,支持了假設3和4。同時,模型3發現:總專有投資和技術差異的交互項對合作績效沒有顯著的影響(β=-0.072,p>0.10),說明技術差異沒有調節總專有投資和合作績效的關系,假設5沒有得到支持。模型還發現:總專有投資和管理差異的交互項對合作績效有正向的影響(β=0.188, p<0.05),說明管理差異正向調節總專有投資和合作績效的關系,支持了假設6。
為更直觀地說明技術差異和管理差異的調節作用,本文對調節作用進行了畫圖。如圖1所示,在技術差異大時,專有投資差異與合作績效的負向關系更顯著,說明技術差異的調節作用為負,支持了假設3。圖2表明,專有投資差異和合作績效的負向關系在管理差異大時更加明顯,支持了假設4管理差異負向調節專有投資差異和合作績效的關系。如圖3所示,總專有投資與合作績效的正向關系在技術差異大和小兩種情境下沒有顯著的區別,說明技術差異對該關系沒有顯著的調節作用。圖4表明,總專有投資差異和合作績效的正向關系在管理差異大時更加明顯,說明管理差異正向調節總專有投資和合作績效的關系,支持了假設6。

圖1 技術差異對專有投資差異與合作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 圖2 管理差異對專有投資差異與合作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

圖3 技術差異對總專有投資與合作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 圖4 管理差異對總專有投資與合作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
五、討論與結論
(一)理論貢獻
本文對現有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貢獻。第一,系統分析了合作研發中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的影響。現有研究認為專有投資是影響合作績效的關鍵因素,然而交易成本理論和關系交換理論對二者關系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解釋。本文通過關注專有投資的兩個不同特征(總專有投資和專有投資差異)來探索其對合作績效的影響。研究表明,專有投資是否有利于合作績效取決于專有投資的不同特征,有助于解釋交易成本理論和關系交換理論得出不同結論的原因。因此,本文更全面地描述了專有投資與合作績效的關系,豐富了對專有投資與合作績效關系的認知。
第二,本文發現專有投資在合作研發中的作用取決于總專有投資和專有投資差異兩項特征,有助于推動對專有投資的研究。除了現有研究已廣泛關注的總專有投資之外,專有投資差異是專有投資的另一個關鍵特征。研究發現,總專有投資和專有投資差異對合作績效有截然相反的作用。該發現體現了專有投資的復雜性,并表明專有投資的作用是多維的而非單一的。因此,對專有投資作用的探索必須考慮專有投資差異,否則只是提供了片面的知識。
第三,本文將技術差異和管理差異作為重要的情境要素,發現專有投資的有效性和具體情境相關。研究發現合作各方差異對專有投資的有效性有重要影響,該結果表明,合作各方的差異加劇了專有投資差異的危害性,但強化了總專有投資的有效性。因此,后續對專有投資的研究需要將合作伙伴間差異這一重要情境考慮進來。
(二)實踐價值
本文也有很好的實踐價值。首先,本文發現總專有投資對合作績效有積極影響,而專有投資差異對合作績效有負面影響。因此,為了獲得更好的合作績效,合作各方不僅應該投入更多的專有投資,還應該減少和均衡專有投資差異。其次,本文發現專有投資的有效性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因此在合作過程中,企業不僅需要注重選擇存在技術和管理差異合伙來實現雙方的優勢互補,更要注意技術和管理的差異會導致專有投資差異對合作績效產生更負面的影響作用。綜上所述,本研究闡述了通過合作研發促進企業創新過程中面臨的問題,指導企業對合作研發活動進行有效的設計,幫助企業針對所面臨的合作伙伴狀況以及自身條件對合作研發活動進行相應的調整和優化,最終促進合作績效的提升。
(三)局限性與未來研究方向
盡管在研究的各個環節都有細致的考慮,但由于時間和客觀資源的限制,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并且為未來的研究指出了方向。首先,本文使用的是橫截面數據,以橫向數據驗證所提出的假設,但是合作伙伴間專有投資的投入與企業合作績效的演化關系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進行的動態過程。因此,如果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夠采用縱向數據來對各變量的演化關系進一步分析是更為準確的。其次,本文中的數據提供都來源于合作的一方,包括專有投資和合作績效等,雖然該方法的有效性得到了普遍的認可并得到廣泛地使用,但是鑒于一方提供的合作研發的主觀數據可能存在自我報告偏差,如果收集的數據來自于合作雙方的話,所獲取的衡量數據將更加全面。
對于未來的研究方向,本文提出了如下建議:第一,除了技術差異和管理差異,其他要素、機制和過程也會調節專有投資與合作績效之間的關系,鼓勵學者在未來研究中關注其他調節變量。第二,總專有投資和專有投資差異都涉及專有投資的關鍵方面。然而,以往的研究大多只強調了總專有投資,而忽略了專有投資差異。在研究專有投資的內涵時,未來的研究應做全方位的考慮。第三,專有投資影響合作績效的中介機制尚不完善,以后的研究可以關注其他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