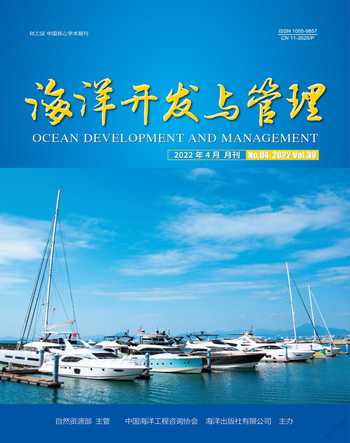藍色海灣修復社會資本參與的 PPCC 洞頭模式
李昌達 顧詩靈 馬靜武 喬觀民 李加林 鄭衡

摘要:為有力保障海洋生態修復項目建設以及實現高效片區治理,文章以洞頭藍色海灣修復項目為例,詳細分析政府和社會資本價值創造和價值捕捉(PPCC)模式的運行方式,并總結其經驗啟示。研究結果表明:藍色海灣修復總體表現為片區開發,且具有很強的公共物品屬性和外溢效應,應用 PPCC模式是對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的重要創新;通過參與主體的動機凝聚和資源互補創造多元價值,根據不同參與主體的價值捕捉機制實現合作共贏,從而形成政府、企業和公眾共建和共治以及經濟、生態和社會價值共享的 PPCC 洞頭模式,藍色海灣修復項目取得明顯成效,進一步實現成功的多元片區治理。
關鍵詞:藍色海灣;生態修復;價值創造;價值捕捉;片區治理
中圖分類號: F205;P748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1005-9857(2022)04-0011-08
The PPCC Dongtou Model for Social Capital Participationin Blue Bay Restoration
LI Changda',GU Shiling,MA Jingwu3,QIAO Guanmin,LI Jialin,ZHENG Heng'
(1.Dongtou Marine and Fishery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Wenzhou 325700,China;
2.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iques,Center for Land and Marine SpatialUtilization and Governance Research,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China;
3.Center of Land Remediation in Wenzhou,Wenzhou 3250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ffectively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and achieve efficient area governance, this paper took the Dongtou Blue Bay Restoration Project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in detail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value creation and value capture (PPCC) model, and summarized its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toration of the Blue Bay was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by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precinct, and had a strong public goods attribute and spillover effec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PCC model was an important innovation of the government-private partnership (PPP) model. Through the motivational cohesion of the participating entities and the complemen- tarity of resources to create diversified value, according to the value capture mechanism of differ- ent participants to achieve win-win cooperation, so as to form the PPCC Dongtou Model of gov- ernment, enterprise and public co-construction and co-governance, as well as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value sharing. The Blue Bay Restoration Project had achieved remarkable re- sults, would further achieve successful multi-area governance.
Keywords:Blue bay,Ecological restoration,Value creation,Value capture,Area governance
0引言
開展藍色海灣整治行動,改善近海水質,修復受損岸線和海灣,增加濱海濕地面積,有效控制圍填海規模,實現“水清、岸綠、灘凈、灣美、島麗”的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目標,是海洋強國建設的內在要求。
藍色海灣(以下簡稱藍灣)修復總體表現為片區開發,具有多行業、多領域、多主體和多元價值的特性。基于此,洞頭積極引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推動藍灣修復項目建設。PPP模式在全球新興經濟體中被廣泛應用,其初衷是解決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中政府資金不足的問題,并逐漸演化為解決“利維坦”效率低下以及“私有化”與公共性之間內在沖突的問題[1-3],強調多元治理,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統一[4-6]。由于藍灣修復項目的市場化盈利能力較弱,洞頭創新 PPP模式為政府和社會資本價值創造和價值捕捉(PPCC)模式,推動相關項目的良性發展,并成為“國家級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區”。
公共項目建設通常具有很強的空間溢出效應,因此捕捉公共價值、彌補公共投資不足以及推動公共投資有效運行成為政府和學術界共同關注的熱點,如政府和社會資本價值捕捉[7-8]和價值分配[9-10]。溢價捕捉策略能夠實現外部性的內部化,維護市場的公平性和公正性[11]。當前主要關注公共項目建設溢價效應的價值捕捉,主要方式為土地增值回收[12-14],而對公共項目建設綜合價值創造與價值捕捉的關系關注不足。價值創造與價值捕捉的關系主要存在于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研究[15-16],可提供很好的借鑒。
基于過程視角,以多元價值為紐帶拓展 PPP模式,形成 PPCC模式分析框架,解譯洞頭藍灣修復的片區開發成功經驗,可為公共項目建設實現政府、企業和公眾共贏的高層次治理提供新注腳,為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轉換新通道以及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新框架。
1文獻綜述和理論框架
PPP模式應用于政府、企業和公眾合作解決公共問題具有強大優勢[17],尤其是在政策制定、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建設和經濟發展方面被廣泛和深入研究。藍灣修復屬于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和能力建設項目,因此應用 PPP模式具有很強的適應性。
1.1PPP模式
PPP模式強調動態價值循環過程并衍生許多模式,如建設-運營-轉讓(BOT)模式和轉讓-運營-轉讓(TOT)模式。其中,BOT 模式的私營企業建設和運營一體化以及成本節約內在化可能導致效率和服務質量降低[18];BOT 模式適用于擬融資建設項目,而 TOT模式適用于曾由政府投資建設而現由國有企業運營的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項目[19-20]。BOT模式和 TOT模式都屬于用戶付費捕捉,其中企業運營是關鍵特征,影響政府財政行為。為保障經濟利益與公共項目之間的公平性,企業往往定價較低,而由政府根據績效進行補貼[21]。
由于政府對企業運營公共項目的影響有限,不利于在公共部門和企業之間形成良好交流,從而影響項目績效以及增加政府財政壓力[22]。從利益相關者角度看,政府和企業通過公共項目分別達到提供服務和獲得利益的目標,公眾則可享受高效和高質的公共服務,從而實現多方共贏。
公共項目因具有公共物品屬性而定價較低,單一的票務收入并不能覆蓋企業建設和運營成本,須由政府財政補貼作為保障。作為收費還貸的典型模式,BOT 模式和 TOT 模式具有回收周期長、回收風險大和回收難度高等特點,會增加政府財政負擔。
1.2PPC模式轉變
公共項目的正外部性會對周邊地區產生溢價效應,當項目的動態回收率難以覆蓋其建設和運營成本時,通過適當回收外部溢價以彌補虧空可推動公共項目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將溢價回收納入 PPP模式形成新模式,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價值捕捉(PPC)模式。
根據“誰受益、誰負擔”的價值捕捉原則,對受益者或使用者的價值捕捉主要有3種方式。①對直接使用者采用票價回收溢價的方式;②對公眾采用稅收回收溢價的方式;③特定的非使用者最易“搭便車”,因此是價值捕捉的重點對象,采用征收土地增值稅回收溢價[14,23]的方式,而采用土地一次性出讓回收溢價的方式難以保障運營的可持續性[13]。根據不同類型的對象采用不同的價值捕捉方式能夠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效率,而隨著傳統 PPC模式稅收捕捉方式的細化,捕捉難度逐漸加大。
作為 PPC模式的新形式,聯合開發可實現正外部性的內部化,用以覆蓋建設和運營成本,而依靠地區壟斷實現價值回收不具有可持續發展性[24]。對政府而言,項目由企業投入資金和技術開發建設,財務風險也由企業承擔,而最終成果互惠互利,因此政府承擔的風險和責任較小;但項目周期較長,在后續建設過程中易產生糾紛,影響價值捕捉效果。
采用 PPC模式的項目具有公共物品特性,價值形式具有共有性、共享性和不可分性,導致價值捕捉較為困難。此外,價值捕捉須考慮主體之間的關系[16],且通過協商才能有效實現綜合價值的有效回收。目前學術界逐漸認識到價值創造的重要性,如技術創新的價值創造和價值捕捉具有不可分性[25-26],但對將價值創造和價值捕捉納入同一框架的公共物品鮮有研究,主要是由于 PPC模式優先考慮價值回收補償,而不是像技術創新那樣考慮價值源泉。
1.3PPCC模式創新
從系統性思維視角看,創造是價值的源泉,因此公共事務管理和公共項目建設的價值捕捉須與價值創造相連接。實際上,當前對公共物品的認識已從項目本身發展到項目提供的服務,而藍灣修復正是特殊的公共物品實踐。Leite等[27]認為公私合作存在動機凝聚以及資源互補和共享過程,且強調價值分配;對其公私合作框架進行改進,結合藍灣修復項目的特性,即形成 PPCC模式框架,以過程視角分析價值創造與價值捕捉的關系。
價值是技術、經濟、服務和利益的貨幣表示形式[28],是項目實施過程中所有行動者的感知結果,包括經濟內在價值、社會價值、經濟外在價值和非經濟外在價值等方面[16]。因此,價值創造不僅創造經濟利益,而且創造生態和社會相協調等綜合價值。
增加價值創造是 PPCC 模式的主要驅動力。①價值創造強調資源整合。價值創造是主體之間資金、資產和資源相互整合的過程,包括政府的資源調度、企業的知識技術模塊化架構[15]以及公眾和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②價值創造須明確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邊界。政府須明確生態修復導向,以市場手段調配資源、鼓勵公眾參與以及實現多元主體協同治理[29-30],使項目具有公共目標導向性、經濟利益追求性和公眾多目標性。
價值分散溢出增加價值捕捉的難度。藍灣修復屬于片區開發,其溢出效應更多地表現為景觀、生態和社會等非經濟價值,即“綠水青山”范疇,因此價值捕捉媒介和通道的選擇具有一定的困難性。藍灣修復是政府主導下的項目建設,經濟利益非優先考慮范疇,這給以追求利益為主的合作企業帶來很大的疑慮,使其感覺風險很大,尤其是企業在PPP股權協議下很難“搭便車”,因此項目選擇是企業合作的重要前提。此外,由于片區開發中的公眾具有很強的“搭便車”優勢,可將公眾納入公共項目建設范疇,促進共建共享。
藍灣修復項目應強調價值創造與價值捕捉的協同,充分考慮不同主體擁有的資金、資產和資源及其對經濟、環境和社會價值的追求,通過“做大蛋糕”降低價值捕捉風險,在價值捕捉困難的情況下實現共贏,從而實現多元主體參與公共項目建設的有效治理。
2洞頭藍灣修復 PPCC模式的運行方式
2.1研究區域
洞頭位于甌江出海口,陸地面積約為173km2,海域面積約為2862km2,海岸線約為351km;擁有海島302個,包括有居民海島14個和無居民海島288個,素稱“百島之縣”。
洞頭擁有優美的生態環境、豐富的海洋資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洞頭作為全國首批8個藍灣整治試點之一,2016—2020年通過藍灣修復項目實現清淤疏浚157萬 m3、修復沙灘15萬 m2和修復砂質岸線1.5km,整治修復國家級海洋公園核心區海洋生態廊道岸線23.73 km,擴展南塘灣濕地公園22hm2,第一類和第二類海水水質標準的海域面積占比提高10.4%,基本實現“水清、岸綠、灘凈、灣美、物豐、人和”。
2.2過程視角的藍灣修復 PPCC模式
2.2.1PPCC模式的形成
資金是藍灣修復最大的“短板”。藍灣修復項目總投資9.27億元,其中中央補貼5.26億元,其他則由地方政府解決。2015—2017年洞頭年均財政收入為11.11億元,財政壓力很大。為有效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洞頭政府積極引進社會資本參與藍灣修復項目建設。2015—2017年溫州年均居民儲蓄額為73.07億元且私營經濟發達,因此社會資本參與藍灣修復項目建設具有很大的可行性。此外,藍灣修復是國家級項目,項目載體是4A 級海島景區,具有發展旅游經濟的可能性,因此藍灣修復項目具有強大的號召力。
洞頭政府希望借藍灣修復之力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企業關注藍灣修復后優質資源的價值實現,且參與國家級項目建設有利于擴大聲譽并與政府建立良好合作關系;公眾渴望改善生態環境和優化“三生”空間,對藍灣修復具有強烈的認同感。政府有項目、企業有資金且公眾有需求,三者達成一致即形成動機凝聚,有利于主體之間的交流合作和資源互補。考慮到片區開發中價值捕捉難的問題,洞頭政府以沙灘修復和海洋生態廊道建設為主體項目,具有一定的行動邊界和權利場域,增強企業和公眾的參與信心,從而提高合作的可能性。
動機凝聚和資源互補是 PPCC模式形成的驅動力。洞頭政府、企業和公眾達成藍灣修復的共識并實現各自資源的重組和配置,有利于更好地實現價值創造和價值捕捉。
2.2.2價值創造
政府出讓優質資源和資產進行合作是價值創造和價值捕捉的基礎。藍灣修復項目重點關注沙灘修復和海洋生態廊道建設:海島地區的沙灘具有“臨界空間”意象,屬于優質資源[31];海洋生態廊道是海島景觀的凝視空間且具有領域性邊界,屬于優質資產。
2.2.2.1沙灘修復的價值創造
(1)提升生態價值。以生態為導向,政府委托專業機構科學分析和規劃東岙沙灘修復的平面布置、剖面設計和鋪設沙粒選擇,并沿沙灘岸線清淤疏浚。通過提高海水水質和保護濱海岸線,為沙灘景觀開發提供環境基礎。通過構建藍灣指數評估體系開展修復評估,反映生態治理成效,推動后續修復工作的有序實施。
(2)提升景觀價值。沙灘具有較好的景觀特性,可通過景觀設計提高景觀價值,企業聘請專業人員高標準設計韭菜岙沙灘景觀。在生態設計的原則下,政府通過招標遴選資質較好的企業實施沙灘修復項目。沙灘修復使沙灘面貌煥然一新,原來礫石遍地的沙灘成為風景秀麗的景點,實現“黃沙變黃金”的轉變。沙灘修復與花園村莊建設同步開展,村莊生活和生態環境日益向好,70%的東岙村村民從傳統捕撈和養殖業轉行從事旅游業和相關產業,積極發展“農家樂”和民宿旅游,沙灘邊的舊民房經改造變為“聚寶盆”。
(3)提升社會價值。沙灘修復后可有效抵御臺風等自然災害,并經受住超強臺風“瑪莉亞”和“利奇馬”的考驗,有力保障村民生命和財產安全。村民通過旅游業的發展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環境,從而提高幸福感和片區治理意識。政府加大宣傳力度,積極舉辦國際會議和賽事,打造美麗沙灘的“金名片”。
2.2.2.2海洋生態廊道建設的價值創造
(1)提升生態價值。政府與企業協商建設成本較高的高架木質廊道,與采用成本低廉的水泥建材相比更能保護生態環境,且盡量避免破壞海島山體。在海洋生態廊道沿線建設生態海堤和破堤通海工程,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實現廊道和海島岸線生態價值的同步提升。
(2)提升景觀價值。開發具有生態特色的景觀線路,提高與區域環境的融合度和連通性,使生態修復與景觀美化相結合。改造并建設總長11.4km 的“東海第一臨海懸崖棧道”和總長15.5km 的濱海綠色生態走廊,將零散景觀“串珠成鏈”,打造親水空間,為村民和游客提供觀賞新視角,發揮滯客效應并實現旅游增值。
(3)提升社會價值。海洋生態廊道建設結合海島岸線修復和沿線村莊改造,打造凸壟底、東岙和金岙等一批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海洋生態村莊,在改善村莊環境的同時使其與沿線景觀互動串聯,形成“海上花園”意象,推動旅游業的發展,創造沿線村莊的綜合價值。
綜上所述,沙灘修復和海洋生態廊道建設通過拓展景觀廣度和提高景觀深度,實現對海島資源的持續性價值創造,并以地區特色提升知名度。政府堅持將發掘、傳承和弘揚海洋文化作為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載體,注重傳統與創新的有機統一,促進旅游業和相關產業的發展,帶動村民共同富裕。沙灘修復和海洋生態廊道建設一期項目的成功推動二期項目的建設,實現“滾動開發”,既激發市場活力又緩解財政壓力;政府實現職能轉變,由公共物品提供者變成監管者;公眾從項目中獲益,從而提高參與公共項目建設的積極性,進一步促進片區治理。
2.2.3價值捕捉
以往的生態修復項目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建設,投資周期長且成本高,產生的外部性易引發“搭便車”行為,導致效率低下。在 PPCC模式中,多元主體參與價值創造和價值捕捉,有利于實現合作共贏。
由于藍灣修復項目具有公共物品屬性,項目回收存在風險,加之旅游產品價值捕捉分散且大部分存在外溢效應,進一步提高項目回收風險。面對這種風險,根據領域性原則,須精準捕捉邊界明確的項目價值,而將邊界模糊的項目價值直接讓利于民,從而減少價值捕捉的阻礙,促進項目快速實施。因此,須分析不同主體的價值捕捉機制。
2.2.3.1生態價值捕捉
游客通過旅游和觀賞活動實現沙灘修復和海洋生態廊道建設的生態價值捕捉。這種價值捕捉是無形的,即不能表現為直接經濟價值而僅能表現為體驗價值。生態旅游的景觀價值越高,游客的旅游意愿越強,越有可能帶來更多的消費,對旅游業的發展產生潛在價值。
2.2.3.2經濟價值捕捉
政府和企業對有明確邊界的沙灘酒店和海洋生態廊道共同進行精準的經濟價值捕捉。旅游景觀的分散性和外溢性導致價值捕捉困難,為實現更加精準的價值捕捉,應打造“眾星捧月”的旅游凝視效應。港口清淤疏浚、破堤通海和村莊環境改善等工程不僅改善水質、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美化環境,而且提高沙灘和海洋生態廊道等景觀的觀賞性,旅游景觀進一步升值,提高價值捕捉空間。按照股權協議,企業與政府通過共同獲取門票和酒店收入等方式進行價值捕捉,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愈發改善,生態和經濟價值產生“1+1>2”的效應,符合公共項目建設的宗旨。
東岙村沙灘修復完成后,由于其邊界較為模糊,政府和企業難以進行精準的價值捕捉,因此讓利于民,提高村民自我管理的意識和能力。相關資源由當地街道辦事處負責運營和管理,以村民“搭便車”共享價值的方式進行價值捕捉。2016—2020年東岙村集體經濟收入提高10倍,戶均收入提高10萬元;村莊環境整體改善,村民通過經營“農家樂”和民宿以及獲得房地產溢價實現經濟價值捕捉。
2.2.3.3片區綜合溢出價值捕捉
沙灘修復、海洋生態廊道建設和沿線村莊集中整治促進洞頭生態環境整體改善和旅游景觀提質,促進片區整體價值的提升和經濟的發展,產生溢出效應。政府通過房地產溢價和稅收等方式進行價值捕捉。
2.3共建、共治和共享
公私合作須獲取和整合各方的資金、資產和資源,以創造新的產品和實現綜合目標,依靠單一主體無法輕易完成。參與主體之間通過博弈和協商達成共識,分別貢獻各自的知識、技術和能力,便會產生大于單獨效果之和的綜合效果,實現資源互補。資源互補被認為是合作成功的關鍵,因為其允許參與主體依靠協同效應創造新的價值[32]。
在藍灣修復項目中,政府發揮強大的綜合資源調度作用,公眾和非政府組織(NGO)發揮提出建議和輿論監督作用,企業在其中利用知識和技術進行合作創新,不僅為公眾創造價值,而且提供創新服務。對企業而言,資源互補能夠更好地建設和運營項目,有利于降低成本、獲得社會效益和提高知名度。2018年以來,洞頭已接洽客商60余批共計500余人次,成功簽約7個項目,總投資達300億元。價值創造和價值捕捉相互促進,企業從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獲得的利益越大,參與合作的意愿就越強烈,價值創造形成良性的閉路循環。村民是藍灣修復項目的最大受益者,可從旅游經營和房地產外溢效應中捕捉價值。藍灣修復項目大幅提高村民生活水平,被稱為“富民工程”,一期工程的良好示范效應為二期工程的順利建設奠定基礎,同時促進村民積極主動參與,實現片區治理。
3啟示
3.1藍灣修復的 PPCC洞頭模式
藍灣修復是公共項目,具有很強的公共物品屬性。洞頭藍灣修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實現政府、企業和公眾的共建和共治以及經濟、生態和社會價值的共享,從而建立藍灣修復的 PPCC洞頭模式(圖1)。
3.1.1藍灣修復具有強大的動機凝聚力
藍灣修復作為國家級項目具有強大的號召力,政府和企業在經濟、生態和社會價值的吸引力下積極參與,推動 PPCC模式的形成。
不同參與主體擁有不同的資源和價值目標,可通過交流合作實現資源互補,而缺乏統一動機是公共治理的難點。其中,政府擁有資金、信息和公共資源,并致力于生態價值的提升;企業擁有資金和技術,并追求經濟價值的最大化;公眾擁有土地和公共資源,并傾向于生活環境的改善。在藍灣修復和資源互補的雙重促進作用下,各參與主體達成一致目標即高質量建設藍灣修復項目,并形成創造綜合價值的共識即動機凝聚,推動 PPCC模式的形成。參與主體的資源互補意愿和動機凝聚力隨著共識的增強而增強,有利于藍灣修復項目建設。政府、企業和公眾凝聚在一起并形成良好的交流合作關系,為價值創造提供基礎。
3.1.2參與主體共創多元價值
生態岸線改造與沿線美麗村莊建設相結合,加快藍灣修復區民宿經濟的發展,推動村莊內生發展。積極引進社會資本,推動區域生態建設。以藍灣修復綜合價值聯結政府、企業和公眾,形成政府主導、企業承建和公眾參與的網絡關系和共建模式。通過“做大蛋糕”創造景觀經濟、環境生態和社會治理價值,降低價值捕捉風險。
3.1.3精準捕捉和富民共贏
價值捕捉是藍灣修復項目建設的關鍵所在,而藍灣修復項目的公共物品屬性和外溢效應提高價值捕捉的難度和風險。為應對這種風險,在價值捕捉的過程中須充分考慮價值類型和不同主體的價值捕捉機制,并開展價值捕捉協商。
根據景觀的邊界實現政府和企業的精準價值捕捉以及公眾的價值捕捉,實現價值共享;公眾作為最大受益者,通過“搭便車”獲得多樣化收入,而富民程度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公眾的片區治理意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自身并不參與價值捕捉,NGO 在價值捕捉協商中發揮重要作用,可公平和公正地協調各參與主體的價值分配。
3.2成功的片區治理:從行政管理走向多元治理由政府主導的 PPP模式強調行政管理,由于片區開發的價值分散且外溢性強,以往主要通過房地產開發獲取溢價。藍灣修復項目的片區開發范圍更廣且價值更分散,導致價值捕捉更困難。因此,藍灣修復項目的特殊性導致單純依靠政府或企業都不能實現整體治理,而是要求多元主體協同參與,即各參與主體通過協商創造價值和捕捉價值,實現生態、經濟和社會價值的協調發展。
政府在政企合作中強調頂層設計。企業以生態修復項目為媒介進行價值捕捉,并增強社會責任感。推動公眾主動參與公共項目建設,實現公共服務由行政管理向多元治理轉變;尤其是富民工程促進公眾生態意識的覺醒,使公眾積極參與日常生態保護工作。政府、企業和公眾共同構成協同治理網絡,實現價值創造和價值捕捉的良性循環以及片區治理的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1]王春福.公共產品多元治理模式的制度創新[J].管理世界,2007(3):160-161.
[2]丁日佳,丁文均.基于制度分析與發展框架的環境保護稅多元協同治理研究[J].稅務研究,2020(7):116-120.
[3]廉超. PPP模式助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J].貴州社會科學,2017(1):152-157.
[4]顏紅艷,賀正楚,李晶晶,等.城市軌道交通 PPP項目主體行為風險評價[J].科學決策,2019,261(4):1-22.
[5] TANG Y, LIU M,ZHANG B. Ca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PPs) improvetheenvironmentalperformanceofurban sew- age treatment?[J]. Journal 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 2021,291:112660.
[6] HUANG Y,JIANG C,WANG K,etal.Public-privatepartner-shipinhigh-speedrailfinancing: caseofuncertainregionaleco- nomic spillovers in China[J]. Transport Policy, 2021, 106:64-75.
[7]張芳,張安錄.軌道交通對住宅價格空間增值效應與價值捕獲機制的構建:武漢地鐵四號線的實證分析[J].價格月刊,2021(6):11-19.
[8] SALON D,徐逸菁.利用區位價值捕獲為城市公共交通設施投融資[J].城市規劃學刊,2017(5):121-122.
[9]戚安邦,鄭麗霞.建設項目價值最大化和分配合理化模型與方法:基于全體利益相關者視角的分析[J].工業工程與管理,2015,20(6):28-33.
[10]王秀芹,劉旸,張少波. PPP項目再融資收益分配的關鍵影響因素研究[J].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23(5):414-422.
[11]馬祖琦.公共投資的溢價回收模式及其分配機制[J].城市問題,2011(3):2-9.
[12]李艷飛,劉俊業,翟磊.溢價回收視角下的城市生態治理項目建設資金來源研究:從滇池生態保護費談開去[J].城市發展研究,2013,20(1):140-143.
[13]鄭思齊,胡曉珂,張博,等.城市軌道交通的溢價回收:從理論到現實[J].城市發展研究,2014,21(2):35-41.
[14] WU JY, HU YJ,WANG Q X,etal.Exploring valuecapturemechanisms for heritage protection under public leasehold systems: acasestudyofWestLakeculturallandscape[J]. Cit-ies,2019,86:198-209.
[15]王宏起,王卓,李玥.創新生態系統價值創造與獲取演化路徑研究[J].科學學研究,2021,39(10):1-15.
[16] CHESBROUGH H,LETTL C, RITTER T. Value creationand value capture in open innovation[J]. JournalofProductInnovation Management,2018,35(6):930-938.
[17] BRINKERHOFF D W,BRINKERHOFF J M.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 perspectives on purposes, publicness, and good governance[J]. Public AdministrationandDevelopment, 2011,31(1):2-14.
[18] MASKIN E,TIROLE J.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nd gov-ernmentspendinglimits[J]. InternationalJournalofIndustrialOrganization,2008,26(2):412-420.
[19] CUIC,LIU Y, HOPE A, etal.Review ofstudieson the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 (PPP) forinfrastructure projects[J]. In- ternational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8, 36(5):773-794.
[20] MENG X, ZHAO Q, SHEN Q.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fortransfer-operate-transferurbanwatersupplyprojectsinChina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ring, 2011, 27(4):243-251.
[21] SHARMA R,NEWMAN P. Can land valuecapturemakePPP'scompetitiveinfares? A mumbaicasestudy[J]. TransportPolicy,2018,64:123-131.
[22] LIX, LOVE P E D. Employing land value capture in urbanrailtransit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Delhi' sairportmetroexpress [ J].Researchin Transportation Business & Management,2019,32:100431.
[23] KIM M. Upzoning and value capture: how U. S. localgovern-ments use land use regulation power to create and capture valuefrom real estate developments[J]. Land Use Policy,2020,95:104624.
[24]林雄斌,楊家文,李貴才,等.跨市軌道交通溢價回收策略與多層級管治:以珠三角為例[J].地理科學,2016, 36(2):222-230.
[25]董廣茂,徐靖偉,張冬敏.創新在基于價值捕捉的產業升級中的作用[J].西安工業大學學報,2020,40(2):221-226.
[26]張華,顧新,王濤.基于過程管理視角的開放式創新關系治理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20,37(11):1-8.
[27] LEITE E,BENGTSON A. A businessnetwork view on valuecreationandcaptureinpublic-privatecooperation [ J].IndustrialMarketing Management,2018,73:181-192.
[28] ANDERSON J C, NARUSJ A, VAN-ROSSUM W. Customervaluepropositionsin busines markets[M]. Cambridge: HarvardBusinesSchoolPres,2006.
[29]王喆,周凌一.京津冀生態環境協同治理研究:基于體制機制視角探討[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5,36(7):68-75.
[30]朱喜群.生態治理的多元協同:太湖流域個案[J].改革,2017(2):96-107.
[31]梅思雨,喬觀民,馬靜武,等.行動者網絡視角下的藍灣修復洞頭模式:以東岙沙灘修復為例[J].中國發展,2020, 20(3):12-19.
[32] HODGE G A, GREVE C.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n in-ternationalperformancereview[J]. PublicAdministration Re-view,2007,67(3):545-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