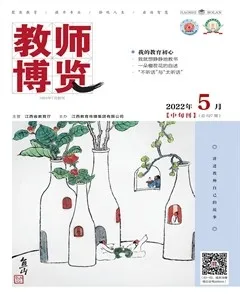教師權威角色的解構與重構
張鵬
韓愈有言:“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在這種認知下,教師都是傳、授、解的行為發出者,而行為接受者則是未直接明示的學生,這背后隱藏著教師權威觀念。這種教師權威觀念帶來的恰是道德訓誡、行為管理、知識占有等統治型教育實踐,也帶來了我國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但這種“尊”與“重”中是否含有屈從的成分和不平等?新時代教師權威觀念與角色是否還適應核心素養培育的關鍵任務?這都需要我們對教師角色進行重新認識。
在傳統社會中,文化資源占有和分配不均衡,代際劃分明顯,故而德高望重的老師因其飽讀詩書、修身進德,便可以對進入學堂的學生展示道德與學識,進而使學生崇拜、服從。但這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因為我們并不能保證所有老師都能登上道德與學術的絕對高地,而這種教師權威角色擴散開來,則可能會磨滅很多學生的天性,損傷學生生命機體自主自發的個性發展。
學生并非沒有獨立思想和自主行動力的機器或動物,一種內外協調的民主觀念和要求正在沖擊和解構教師權威角色,這在學校的德育實踐與課堂教學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現在的學生對自我道德觀念的認同感更高,似乎都有屬于自己的一套“理論”,很難接受教師自居道德高地的訓誡與教導,也對教師自我的道德自律和行為示范提出要求,這也就是學生內心常有的獨白:“你能做到嗎?你還說我。”學生更傾向于沉浸式的道德活動和行為體驗后的真實感觸,譬如親手扶起摔倒的老人而得到贊美與鼓勵后的幸福體驗。面對當前學生越來越強烈的道德自覺,教師道德權威角色很可能會力不從心,但教師不能因而退居自守,無所作為,而應該解構自身傳統權威角色,去重構新教師身份,即成為師生道德進階的協行者、互助者。在這種攜手互助的過程中,教師應主動作為,創造道德環境與教育契機,引領學生成長,使學生成為道德完善的自覺者和自修者。如學生自我領導力的培養、班級班干部體系的建設等,教師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而是解決問題的指導者,變班級管理為班級治理。
在信息時代,眾多學習資源和渠道遍布網絡,學生完全可以借助網絡進行學習。教師上網搜索的信息資源,學生也可以搜索到。那么,教師還是知識的絕對占有者嗎?當前,新課標強調學科核心素養培育,任務驅動、情境創設、項目教學、自主合作探究式課堂正是核心素養真正落實的捷徑。而傳統作為知識權威角色的教師所進行的課堂講解,在幫助學生提高學科核心素養方面已顯示出缺陷和短板。課堂本是一個多元的相互學習場,課堂預設與生成的任何一個方面都可能會影響到學生,因而學生在課堂上的生成契機、學習所得并不僅僅來自老師,也來自其他同學。故而日本佐藤學教授一直倡導相互傾聽的課堂生態。有了傾聽,深度對話與思考才成為可能,這種民主的課堂文化取向,挑戰的正是教師單向言說、學生單向傾聽的傳統課堂。
面對新時代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戰,教師更需解構權威角色,進而重構新角色。一方面,學生可以借助網絡獲得學習資源,但對于鋪天蓋地的學習資源,如何去粗取精,擇優學習,按照怎樣的順序與結構去加工學習內容,學生還存有很多問題。對此,教師作為過來人,便可指導學生搜集、組合、加工學習內容的方向與方式,鍛煉學生的媒介素養和自主學習能力。另一方面,面對課堂教學挑戰,教師應轉變教學理念,變知識的直接傳授為順應學習規律的探究習得,學生在課堂上就像人類尋覓科學一樣探尋奧秘,整合知識;教師變“一言堂”為平等對話中的首席,激發學生思考與言說的欲望,讓課堂生成在相互對話、傾聽、思辨中恣意迸發。由此,教師在學生與知識、學生與素養、學生與學生、學生與教師等多重關系中重構出科學編織者的新角色。
無論是民主呼聲的高漲,還是學生道德學習對傳統教師道德訓誡的挑戰;無論是學生學習方式的轉變,還是學生特長多樣化所帶來的對教師的更高要求,每一項都在消解教師的權威性。但是這種消解并不代表對教師人格意義的抹殺,相反,消解帶來的是教師新的“權威”身份的再造,當然,這種新的“權威”并非傳統倫理文化意義上的權威,而是為學生道德自律、學識增長、人格完善負責并適時指導,以身示范的引領性“權威”。實際上,這樣的教師在學生面前呈現的不再是“我是什么,你們應該是什么”的指令與要求,而呈現的是“我應該是什么,我們應該是什么,我們如何成為那個什么”的求思、展望與行動。用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理想愿景喚醒學生,用一種智慧思索與堅定行動啟迪學生,因教師價值觀里對師生人格平等的篤定,因教師職業自律里對以生為本的堅守,贏得了學生認可,賦予了教師權威角色新的內涵,這樣的老師才能合乎情理地成為葉瀾教授所說的“教師在學生面前展現的不只是‘專業,而是其全部的人格”。
人格平等、以生為本的價值堅守,道德完善的以身示范,學習媒介與方式的指導等教師職能所重構的“權威”角色,對教師提出了要求,那就是教師必須成為終身學習者。這種終身學習實際上是自始至終的自我解構與重建,以及時刻的反思與更新。這種終身學習可從三個層面展開:“哲學層面”的研究人(學生)、群體(班級)和社會關系(家校社),“技術層面”的研究課堂活動設計、班級活動設計與學生活動產品,“實踐層面”的對學科教學、班級治理等諸多微觀個案的剖析。當然,這也肯定是不完全的,因為教師面對的日常是復雜而充滿變化的,但關鍵是,每位教師在對自身的角色認知中都應有打破、重建的勇氣和持續學習的毅力,這也是在不斷為重構的新教師“權威”角色的合理性做詮釋。否則,沒有終身學習,教師“權威”豈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學校教育沒有終點,教師的角色行為所帶來的意義也沒有終點,教育是為學生的終身可持續發展奠基。每個學生在離開學校后的人生軌跡,都是我們教育故事的續寫,關鍵是在連續不斷的續寫中,教師回望自身角色,去發現“原來,我還做得不夠好,我離理想的教師‘權威還有很大距離”的遺憾和努力的方向。于是乎,教師在權威角色解構與重構的持續回環與升級中,必然指向教師的“專業性”所需要具備的終身學習和終身修煉的品質。
(作者單位:山東省威海市實驗高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