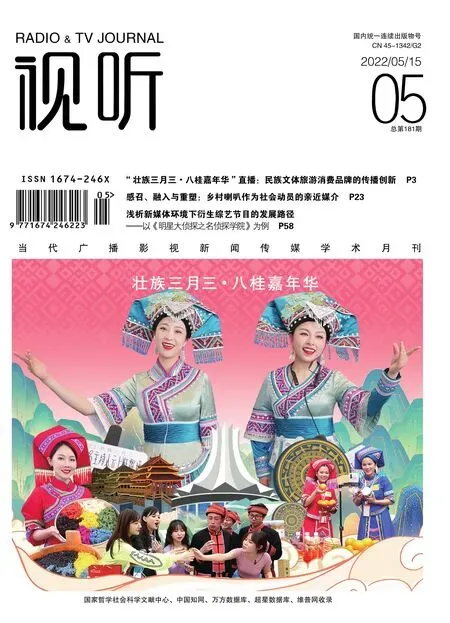動畫電影《西游記之再世妖王》的倫理性反思
楊 璟
《西游記》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超級IP。1906年,豐泰照相館記錄的京劇名伶俞菊笙表演的《金錢豹》片段被視為“西游”影像生產之開端。《孫行者大戰金錢豹》(1926)和《豬八戒招親》(1953)都曾掀起一陣熱潮,而電視劇《西游記》(1986)作為公認的無法超越的經典,重播次數超3000次,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可以說,“西游”文化在中國影視史上各個時期從未缺席,并且逐漸走向世界,成為海外影視生產的重要題材之一。作為熱衷于攝制“西游”電影的星浩影業有限公司主導出品的國產動畫電影,《西游記之再世妖王》(2021)傳承了中國動畫學派民族化造型風格,彰顯了中國國產動畫電影的工業化水平,然而也無法掩蓋其口碑不高、票房乏力的現實。究其原因,《西游記之再世妖王》在著力追求民族化形式時,沒有恰當地處理好電影的倫理精神“賦能”問題,其民族化特征沒有得到彰顯。
一、人倫敘事:傳統性的失效
人倫敘事是中國電影的傳統。所謂人倫敘事,是指在構建故事情節時,將人物的倫理道德追求作為推動敘事進展的關鍵性要素,將人與人之間的親情、友情和愛情表現作為吸引觀眾的最重要元素。早期中國電影在與外國電影的激烈競爭中逐漸摸索出一套能夠充分滿足中國觀眾心理需要的模式,中國電影史上一批極具市場影響力的電影正是這套模式的演繹。比如,中國化的家庭倫理片的開創之作《孤兒救祖記》(1923)“在反思孝道的基礎上,用倫理調和代際沖突”①。《姊妹花》(1934)、《一江春水向東流》(1947)及之后的《牧馬人》(1982)、《千里走單騎》(2005)、《地久天長》(2019)等一些有影響力的家庭倫理片都是人倫敘事的經典之作。又如,中國武俠片將俠義精神內涵放在重要的位置,豪俠們對情義的追求超越了個體生命。經過100多年的發展,人倫敘事在中國電影中產生了廣泛影響。
人倫敘事也是一種劇作技巧。首先,它要通過合乎邏輯的手段,營造人物之間的真實情感,而這種真實情感需與銀幕之外的社會心理同構。其次,電影敘事必須逼迫主要人物進行兩難抉擇,這是情節突轉的關鍵點。例如,在《西游記之大圣歸來》(2015)中,江流兒與齊天大圣之間的真摯情感不僅表現在江流兒對齊天大圣的偶像崇拜上,也表現在江流兒純真而執著的人道主義救贖精神對齊天大圣的感召上。這種情感吸引力是通過大量非敘述性的細節鋪墊來實現的。又如《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中,哪吒與其父母的親情、哪吒與太乙真人的師徒情、哪吒與敖丙的友情都是建立在強烈的當代社會倫理情感的基礎之上的。“這種世俗化、溫情化的改編,也許正是合家歡動畫一種必要的敘事策略,也符合大眾文化的商業訴求,在這個意義上,《哪吒之魔童降世》可謂是一次成功的嘗試。”②所以,當劇情將齊天大圣和哪吒推向兩難時,他們的情感選擇對觀眾而言極具震撼力。
《西游記之再世妖王》中的人倫敘事本應該緊抓兩個關鍵關系來實現,一是孫悟空與唐僧、豬八戒、沙和尚之間的同門師徒情義,二是孫悟空與果子之間的類“父子親情”。但是在電影中,創作者下的功夫還明顯不夠。一方面,影片開端部分展現了唐僧師徒四人“打打鬧鬧”,接著講述了師兄弟三人合伙“作惡”偷吃人參果,除此之外未有其他溫情化的設計,因此師兄弟三人同生共死的情感性鋪墊顯得極為薄弱。另一方面,果子的犧牲是孫悟空獲得超級力量的情感動力,但孫悟空和果子之間的情感關系的建立也缺乏內生性動機。在《西游記之大圣歸來》(2015)中,齊天大圣在江流兒身上看到年輕時的自己。盡管江流兒被塑造得并不可愛,甚至有些許“煩人”,但是由于這種“自戀”心態使齊天大圣對江流兒有強烈的認同感,因此,齊天大圣最終為江流兒而戰是遵循情感邏輯的。然而,在《西游記之再世妖王》中,孫悟空從果子身上看到的是唐僧。由于之前師徒情誼的表現力不足,孫悟空與果子除了有共同的目標之外,兩人的情感關系只能建立在果子的純粹可愛上。因此,影片以此來推動孫悟空為果子而爆發也就顯得力度不足了。
總的來說,《西游記之再世妖王》的人倫敘事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出,該片的創作團隊還沒有完全吃透中國電影傳統的人倫敘事技巧,也沒有很好地對接社會現實,未能實現傳統人倫敘事的現代改造,導致影片難以真正打動中國觀眾。
二、正義動機:集體倫理意識的弱化
《西游記之再世妖王》在建構主要戲劇沖突時,實際上還是選擇了西方戲劇傳統中的“二元對立”模式,即正義與邪惡的斗爭。圍繞著這一傳統的戲劇模式,其采用的是好萊塢式個人英雄敘事策略。在影片中,孫悟空最終靠個人的超能力打倒了妖祖元蒂,完成了正義終將戰勝強大邪惡力量的敘事套路。然而,值得我們思考的是該片中孫悟空執行正義行為的內在依據。
正義是一個極為復雜的概念。西方倫理學對正義的概念、內涵和外延長期存在爭議。相對于西方的正義一詞,中國的正義更偏向于“義”。“義”又常常與“俠”聯結,構成“俠義”。中國的俠“代表了勇敢、自我犧牲、慷慨、正直、為公義而戰的美德”③。“義”又可以分為“小義”和“大義”,君臣之義、師徒之義、朋友之義為“小義”,為國為民是“大義”。在《辭海》中,正義被闡述為“對政治、法律、道德等領域中的是非、善惡作出的肯定判斷。作為道德范疇,與‘公正’同義,主要指符合一定社會道德規范的行為。人們的行為是否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和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判斷人們行為是否符合正義的客觀標準”④。進入新時代,我們不僅要堅持傳統的“小義”,而且要強調現代集體、國家意識的“大義”。
“西游”文化代表著中國古典文化傳統,但是創作者在用影像來闡釋和重組“西游”故事時,常會將其與現代意識緊密聯系。例如,在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動畫長篇《鐵扇公主》(1941)中,創作者“把《西游記》中‘孫悟空三借芭蕉扇’的部分改編為動畫劇本《鐵扇公主》,用意并不僅僅是以鐵扇公主來對白雪公主,而是用曲筆寫劇本,古為今用,使劇本的思想內容含蓄,發人深思”⑤,其目的在于隱喻團結抗日的時代精神。又如,《西游記之大圣歸來》(2015)中的江流兒是沒有任何法力的小和尚,但他卻為拯救被混沌擄去煉丹的兒童們不惜鋌而走險。齊天大圣看似為江流兒而戰,實則是為兒童們的生存而戰。所以,《西游記之大圣歸來》(2015)也因其正義性而具有道德震撼力。
《西游記之再世妖王》試圖展現代表正義的唐僧師徒、果子與代表邪惡的妖祖元蒂之間的對抗。影片本來需要著力表現妖祖元蒂對鎮民生命、財產的毀滅性力量,然而卻僅僅用了一個場面來完成這一任務,即妖祖元蒂派眾妖怪到一個小鎮上來捉拿果子。眾妖怪弄得整個小鎮雞飛狗跳,妖祖元蒂還利用法術控制了部分鎮民,使他們加入到妖怪的隊伍中。最終,妖怪被孫悟空等趕走,妖祖元蒂法術失效,那些被控制的鎮民失去了生命,但果子使用靈力讓他們都復活了。這個場面一方面突出了妖祖元蒂的惡,另一方面也為后來果子因救孫悟空而犧牲埋下了伏筆。但是,正是因為果子讓死去的鎮民復活了,反而消解了妖祖元蒂惡的程度。因為只有對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才能把妖祖元蒂之惡推向極致,從而提升孫悟空、果子消滅妖祖元蒂行為的正義程度。基于此,影片最終難以避免地被導向了孫悟空、果子、唐僧之間的“小義”上。
所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是在此模式的電影中起關鍵作用的問題。而《西游記之再世妖王》在此問題上卻缺乏力度,導致其集體倫理意識被弱化,最終不能很好地調動觀眾的觀影情緒。
三、個人英雄主義:時代性的悖論
英雄主義是人類共同的文化傳統。從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到好萊塢超級英雄電影,從盤古開天辟地、后羿射日到武俠小說、革命英雄傳奇,英雄們開創偉業的故事在古今中外都深受人們的歡迎。一般認為,個人英雄主義“是指脫離人民群眾,迷信、倚重個人力量而去完成某種社會任務的英雄主義思想行為”⑥。個人英雄主義在人類文化中有較大的影響力。在中國歷史上,盡管集體主義在中國傳統精神中占據重要地位,但其也與個人英雄主義長期共存。
從某種意義上講,《西游記》原著小說就蘊含著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孫悟空大鬧天宮是個人英雄主義的集中表現,而他保護唐僧去西天取經途中經歷的多數劫難也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散在呈現。一些“西游”電影的創作者如萬氏兄弟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他們通過電影敘事,將個人英雄主義改造為強調團結斗爭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然而,受原著的影響,許多“西游”電影沒有完全擺脫個人英雄主義。在紹劇電影《孫悟空三打白骨精》(1961)中,只有孫悟空能夠辨明忠奸;在動畫電影《大鬧天宮》(1964)中,孫悟空完全依靠個人的力量戰勝了傲慢的天庭;動畫電影《金猴降妖》(1985)亦是三打白骨精的翻版,及至后來的《大話西游》(1995)、《悟空傳》(2017)等,都明顯地受到個人英雄主義的影響。
自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盛行的個人主義、虛無主義等頹廢消極思想也隨著西方文化進入中國。20世紀末,美國好萊塢電影被引入中國。大量好萊塢動作片在驚險的情節、勁爆的視覺效果的包裝下,也將西方個人英雄主義價值觀輸入到中國。錄像帶、光盤以及互聯網的普及,給中國人觀看更多好萊塢電影提供了機會。一方面,好萊塢電影以及好萊塢電影生產理論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電影生產者,如美國著名編劇理論家羅伯特·麥基極力宣揚個人英雄主義價值觀的電影編劇教材《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一度被奉為中國電影編劇行業從業者的必讀書目。另一方面,由于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較長階段里,集體主義成為宰制性的倫理規范,個人價值長期沒有得到足夠重視,集體和個人的關系失衡,導致部分人產生逆反心理。這樣的社會心態致使當時好萊塢動作片中的個人英雄主義讓中國觀眾感到耳目一新。近年來,國家著力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然而社會上一種不加批評地吸納中國古代文化的思想傾向有所抬頭。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個人英雄主義與好萊塢文化中的個人英雄主義相結合,影響了中國電影、電視劇的創作。
《西游記之再世妖王》的戲劇沖突的解決就是孫悟空依靠個人的超級能力戰勝了可能會毀天滅地的妖祖元蒂。與好萊塢電影類似,《西游記之再世妖王》“使用了大量的特寫展示、色彩暗示、特技渲染、音樂烘托等鏡像語言,讓觀眾不知不覺中融入電影,與英雄人物同呼吸,共命運”⑦。該片在塑造孫悟空形象時突出其冷酷、桀驁不馴的性格。作者希望以這種“人設”來反襯孫悟空與果子之間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用力過猛”,孫悟空顯得極為孤傲,不禁讓人聯想起好萊塢電影中的終結者、蝙蝠俠和鋼鐵俠等“美國英雄”形象。孫悟空之所以要挑戰妖祖元蒂,完全是為了彌補自己誤放妖祖元蒂的錯誤,是自尊心使然。孫悟空準備前往妖祖元蒂藏身處與其決一死戰前,要求豬八戒和沙和尚不要跟隨,認為這是自己的事,與兩位師弟無關。豬八戒和沙和尚決定與孫悟空同生共死,但是在戰場上卻沒有戲劇性作用。鎮元子知道孫悟空放出妖祖元蒂,如臨大敵,立刻讓清風、明月上天庭搬救兵,但是在后面的敘事中,無論是鎮元子還是天庭都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該片模仿好萊塢動畫電影而設計的廣目天王南天門口登記的噱頭“彩蛋”,不但沒有起到諷刺官僚主義的作用,反而和上述元素一起強化了孫悟空的個人英雄主義。
人類歷史的任何時代都需要英雄主義,新時代的中國更需要以英雄主義精神來引領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伴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和文化環境的改善以及影像的躍進,超級英雄的創造也可能是一種標志。”⑧我們承認,在具體歷史情境下,個人英雄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起到關鍵性的推動作用,但是在歷史大變局中,個人英雄往往顯得渺小無力,需要依靠團隊的力量、集體的力量乃至全人類的力量才能取得突出的成就。所以,我們不否認個人英雄主義,但是中國觀眾觀看好萊塢動作片和國產傳統IP大片的期待視野是不同的。觀看好萊塢電影自有好萊塢的語境與文化前提,而《西游記》是圍繞著一個取經團隊來展開的中國故事,“西游”電影可以表現孫悟空的個人英雄主義,但更應該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團結互助的時代精神注入其中。

四、結語
《西游記之再世妖王》的倫理問題反映出一個規律,那就是在改編《西游記》這樣極具影響力的中國傳統IP時,不僅要注重傳統優秀文化的傳承,而且要注重將現代意識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適時合理地植入。因為“影像語言在意識形態引領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在構建我國包括仁愛共濟、立己達人、厚德載物、和而不同、同舟共濟等主流意識形態上獨具優勢,具有中華民族倫理的典型特征”⑨,只有經現代改造后的優秀傳統文化,才可能真正具有時代精神引領作用。
注釋:
①陳犀禾.探索和創新的年代——論20世紀20年代中國電影的歷史意義和地位[J].當代電影,2020(03):61-68.
②劉起.《哪吒之魔童降世》:鏡像結構與文化重構[J].電影藝術,2019(05):46-49.
③龔鵬程.俠的精神文化史論[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23.
④陳至立 等.辭海[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2922.
⑤萬籟鳴,萬國魂.我與孫悟空[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86:90.
⑥朱貽庭.倫理學小辭典[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66.
⑦劉荔.好萊塢電影中的個人英雄主義[J].當代電視,2018(03):110-111.
⑧周星,雷雷.中國影像:超級英雄創造的思考[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02):77-82.
⑨袁智忠,田鵬.影像語言的倫理性[J].電影藝術,2021(01):9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