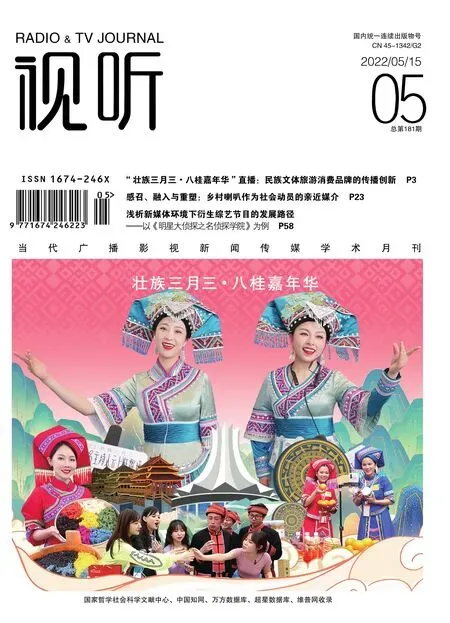中國神話典型形象影視改編的身體敘事
趙旻瑞
中國傳統神話為影視創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在語言和文字傳播時代,抽象的語言文字符號以表達意識為主要目的,身體隱含在其中。當中國傳統神話被搬上銀幕或熒屏時,勢必需要進行不同程度的改編,構建更加符合新時期歷史要求的世界觀、價值觀和藝術價值體系,以適應當代廣大受眾群體的觀影需求。伴隨著傳統神話中的人物由語言描繪的抽象符號轉為影像的具象符號,神話在表達方式上實現了“從文學化表達向視覺化表達的轉變”①,其人物的身體影像成為視覺需求的承載者。反觀影視作品中身體的傳播,其時空的自由建立在對于身體的克服之上。廣義上的身體敘事將身體作為敘事符號,以靜態或動態、在場或虛擬、再現或表現的身體,形成話語的敘事流程,從而達到表述、交流、溝通和傳播的目的。中國傳統神話中的人物在進行影視化改編后,原本只存在于文字中的能指符號會被構建出在場的、可感的動態身體形象,并將身體作為敘事符號取代原本抽象的文字符號。
一、想象的再現:身體影像的具象化創作
“神話”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釋義為“關于神仙或神化的古代英雄的故事,是古代人民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生活的一種天真的解釋和美麗的向往”②。神話中人物的身體在文本中被文字以抽象的形式表現出來。中國傳統神話的文本是其形式中為大眾接觸最頻繁的,其中的閱讀過程伴隨著對抽象的文字符號進行的想象活動,通過想象視覺畫面與聲音來實現對文字信息的理解和保存。而基于影像生產工具的發展,視覺在身體的整個感官系統中占據主導地位,以視覺符號為主導的文化超越了其他感性文化形式愈發占據當代文化的主導地位。在視覺性的表達中,若想完成意義的生產,首先就需要將具體的形象作為基本單元,其次才能在具體形象的意義建構下實現表意功能。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歇爾為視覺文化提出了三個關鍵詞,分別是符號、身體和世界。視覺表達中的身體可以傳遞種族、形象、性別、姿態語言、表演等訊息。影像的動態呈現賦予了影像不同于圖像二維平面的“三+一”維,即影像是三維立體空間和時間維度的存在方式。除此之外,影像從電影默片時代進入有聲片時代后,在表達上完成了視聽綜合符號的運用。通過仿真的創作內容,在日常生活里作為人類存在中負責感知世界、釋放激情和承擔表意功能載體的身體,在影像中得到比圖像更大的表現力。當代視覺文化轉向首先造就了身體性的文本③。身體作為符號的價值逐漸浮現出來。對神話中的人物進行影視化改編,就需要將神話文本中的人物由“一個能指符號,指向缺乏實體存在的虛擬幻想”④轉為具體可見的實在具象。
吳承恩在小說《西游記》中對孫悟空身體的描寫頗多。例如,在第四回中,孫悟空不滿玉皇大帝安排的弼馬溫一職,回到花果山水簾洞中要做齊天大圣時,吳承恩這樣描寫孫悟空:“身穿金甲亮堂堂,頭戴金冠光映映。手舉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稱。一雙怪眼似明星,兩耳過肩查又硬。挺挺身才變化多,聲音響亮如鐘磬。”再如,在第十四回中,孫悟空被壓在五指山下多年,初次見到唐三藏時,他的狀態是:“尖嘴縮腮,金睛火眼。頭上堆苔蘚,耳中生薜蘿。鬢邊少發多青草,頜下無須有綠莎。眉間土,鼻凹泥,十分狼狽;指頭粗,手掌厚,塵垢余多。”⑤文本中孫悟空的形象大抵就是一副雷公相,青面獠牙,尖嘴猴腮。但在影視化改編中,將孫悟空這一具有反叛精神和英雄氣概的人物進行了形象美化。無論是《大鬧天宮》中孫悟空的面部造型借鑒了戲劇臉譜的方式,還是動畫片版《西游記》中孫悟空的面部造型整體采用了圓滑的線條,都將孫悟空的形象柔和化,更適合兒童受眾群體觀看。1986年版的電視劇《西游記》中找來了戲曲表演的猴王世家里長相俊俏的六小齡童來飾演孫悟空的角色。盡管在造型設計上力求還原原著小說文本中描繪的形象,但就孫悟空本身的身體而言,是創作者基于故事文本的二度創作,基于真人肉身的造型加工以及當時的造型技藝水平,無法完全還原小說中描寫的孫悟空形象。動畫電影《西游記之大圣歸來》的孫悟空更是一次經典身體的重構:瘦削高挑卻有寬肩,一身紅毛和棱角分明的長方臉。這里的孫悟空不再是原著小說中無法無天、逍遙自在的美猴王,而是一個性格狂躁抑郁,看淡功與名,甚至帶有一絲中年危機的普通人。這里的孫悟空就打破了傳統故事文本中存在的猴王形象。
《封神演義》第十二回中描寫哪吒出世時的形象和環境是“……房里一團紅氣,滿屋異香。有一肉球,滴溜溜圓轉如輪……跳出一個小孩兒來,遍體紅光,面如傅粉,右手套一金鐲,肚腹上圍著一塊紅綾,金光射目”;第十四回中哪吒現蓮花化身時是“面如傅粉,唇似涂朱,眼運精光,身長一丈六尺”⑥。金光射目等外貌過于異于常人,在具象化的表達中可能會影響受眾的觀感和接受度。于是,在動畫片《哪吒傳奇》中,金光射目、眼運精光這樣的形象被消解,在具象化的創作中呈現的是一個可愛的孩童形象;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哪吒形象則有了較大的顛覆:哪吒作為肉球形體出生時帶有魔丸印記,厚重的煙熏妝、扁塌的鼻梁、一口小齙牙、走起路來吊兒郎當、痞氣十足。這樣的形象一改以往影視化改編中的神采奕奕,成為兼具“美”和“帥”的形象設計。
《封神演義》中沒有關于姜子牙的外貌描寫,而是對姜子牙進行了動作描寫。這就使得閱讀文本的讀者難以想象出姜子牙較為具體的身體形象,只能通過類似年齡的老者、智者的形象來對姜子牙進行形象補全。而在影視化改編過程中,創作者必須對姜子牙的形象予以設定,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應當是一個具體的、活靈活現的姜子牙。以《封神演義》為創作背景的大部分影視作品都盡力將姜子牙塑造為鶴發老者。而動畫電影《姜子牙》中的姜子牙不再是外貌看起來已到古稀之年、垂垂老矣的老者,而是一個長著胡子但外貌俊朗的中年大叔形象。
由上述案例不難看出,依托于神話故事文本的影視化改編作品始終貫穿著“創造性思維”,無論是孫悟空、哪吒還是姜子牙,都是影視化改編創作者對神話故事文本進行的極具個性化創作的藝術想象,并將這一想象再現出來,從而消解了抽象符號與具象符號的二元對立。羅蘭·巴特認為,圖像轉向時代的開始和視覺傳播的泛化就使得言語成了圖像的寄生物⑦。也就是說,隨著“讀圖時代”、視覺文化時代的到來,抽象的、線性的語言文字符號成為輔助圖像、影像表達的工具。圖像也可以對所傳達的信息進行編碼,并向其賦予內涵及象征意義,以此使作為符號的圖像實現語言符號中的能指和所指的層級劃分。觀眾可以通過視覺感官對神話故事文本中的抽象符號進行直接把握。影視化改編作品用以圖像為主的力量,為觀眾帶來了非線性的感性思維和具象思維。將過去蘊含前因后果、前后邏輯的思維方式一舉轉變為圖像的整體,并且通過熒屏或銀幕實現傳播。影像身體通過表演、表現以及后期剪輯等方式,可以實現電影符號學家麥茨所說的“想象的能指”。“想象的能指”意味著電影“能指”本身的特殊性以及由虛構故事(電影的想象界)所導致的能指閱讀(觀影)的“想象性”⑧。觀眾作為身體影像的接受者,也就實現了對既存知識回憶的“再現性想象”,而從無到有的“生產性想象”⑨則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想象空間的壓縮而被消解,同時被消解的還有對神話體系整體建構的能力。
二、景觀的重構:身體敘事的邏輯重塑
法國哲學家居伊·德波在《景觀社會》一書中指出,景觀已經成為一種物化了的世界觀,其本質是為人們搭建以影像為中介的社會關系。單獨的影像身體意象在敘事中組成了身體景觀。基于中國傳統神話的人物形象進行改編創作的影視化作品中的身體,從《西游記之大圣歸來》到《哪吒之魔童降世》再到《姜子牙》,尤其展現出“被現代觀念浸潤的身體意象”的“躍遷式身體景觀”⑩,在對世俗化身體進行架空處理的基礎上,又增添了全新的現代觀念,以適應和符合當前影視受眾市場的需求。多元身體景觀的重構使得中國傳統神話為身體影像敘事中的邏輯重塑提供了有力支撐。影像身體建立在現實身體基礎之上,通過藝術化的表現形式來完成身體影像的構建。如果說現實身體是從意識決定身體的陰影中走出的,已經顯現出自身的主體性,那么影像的身體則是肉身與意識同一性和矛盾性兩個層面的突出展現。其第一層面即在于影像記錄與身體形體的演出,通過后期制作完成影像敘事,這里體現的記錄既是肉身又是意識,即身體與意識的同一性。而第二層面則在于身體與意識之間產生矛盾,即身體不僅反映了肉身,也反映了區別于肉身的意識。
影視化改編創作基于原有的神話故事文本,但不能局限于舊文本之中。《封神演義》在自身結構、敘事邏輯等方面存在缺陷:價值觀陳腐、結構混亂、人物臉譜化等都為其改編增添了不小的難度。基于文本的姜子牙一直渴望并致力于為神權和王權效力;九尾本來是受女媧這一神權代表之命報復紂王不敬,并結束商朝的統治,被姜子牙冷靜無情斬殺,而后姜子牙代替元始天尊執行封神。這樣的姜子牙始終是權力的附庸,身體與意志高度屈從于權力。即使是帶有鮮明悲情色彩和反叛精神的哪吒,也被濃厚的宿命論包裹著。但動畫電影《姜子牙》對姜子牙進行了顛覆性的改寫,一方面賦予他質疑神權的精神,另一方面則是對宿命論的反叛。創作者在身體景觀的構建中,舍棄了冗雜且龐大的群像,取而代之的是聚焦于封神之后的全新紀元。當元始天尊提出“救一人還是救天下”的道德難題時,創作者為姜子牙和觀眾的艱難選擇提供了身體景觀支撐:女孩小九在強大的反派九尾的身體之中。在男性話語主導的社會背景中,女孩承擔了弱者的形象,當影片展開姜子牙與小九的公路片歷程時,一個“大叔+萌妹”的身體景觀呈現出來。而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那個更加反叛的哪吒與“絕美”的敖丙之間全新的友情線,則是為觀眾建構一個明顯對比的身體中,相似卻純潔的精神內核。創作者正是借助這樣的身體景觀構建起全新的身體影像敘事邏輯。
三、符號的消費:消費文化中的身體狂歡
身體景觀不僅僅是視覺奇觀的締造者,同時也承載了多元的價值符號和文化表征。當身體在影像中取代了文字之于文本的地位后,也就承載了符號的意指功能。消費社會的理論范式強調欲望的文化、享樂主義的意識形態和都市的生活方式。身體景觀的重構雖然看似將身體從靈魂和意識的制約中解放出來,并帶有狂歡特質,實現了對文字文本內的“官方規定”的突破,但實際上一整套新的身體美學標準誕生了,這種美學標準體現為“當代強制性的身體美的視覺標準”。神話故事中神仙和妖魔鬼怪的身體在影視創作中跳脫了現實,“以一種變形、夸張甚至異化的形態喚醒大眾對身體的獵奇欲,從而滿足了對于神話傳說中的身體想象。”?多元身體景觀的重構為身體提供了多向度的能指。當嚴肅的神權被拉下神壇,取而代之的是人權和獨立個體時,也為身體的能指符號增添了欲望化和全民性的特征,并引發了集體無意識的身體狂歡。
身體美學規范和視覺媒介意識形態在其中更隱蔽地建立身體標準,大眾視覺媒介也確立了一系列身體美學標準。同時,身體也被視覺文化符號傳播系統納入了消費主義之中,“看起來漂亮”的觀念在人群中不斷被反復強調。從此,“漂亮”成為身體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評判標準。這種身體美學標準的建立,扼殺了身體形態的多樣性,使得身體形象被固化。固化的身體形象束縛了身體表達意義的范圍,從而造成影像身體的隱喻功能被弱化。而人作為社會歷史發展的主體,其意識存在物、勞動存在物、社會存在物及歷史存在物維度都被消費文化抹平,變成了消費符號和產品符號。個人的獨特特征也就淹沒在大眾時尚塑造的所謂“個性”之中。基于神話故事文本產生的影像身體,由于自身對現實的超越性,也就使得身體樣態的多樣性有了實現的可能。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無論是哪吒、太乙真人、李靖還是李夫人等角色的塑造,都從原本的扁平化神權王權語境中解脫出來,被賦予了當代價值觀。但值得注意的是,敖丙的身體重塑仍然以消費為目的。在消費社會,人們首先要求的是視覺快感,對于視覺快感的需求優先于故事本身。

四、結語
中國傳統神話的豐富脈絡足以為中國商業類型電影提供龐大的神話宇宙。影像身體對敘事的完成和符號意義的被賦予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對身體影像、景觀進行合理化改編和創作是能否實現神話宇宙建構的重要基礎。神話身體超越現實的先天優勢,為神話身體影像和景觀塑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如何發掘中國傳統神話中的人物,如何打造富有人格魅力和號召力的影像身體,仍然是影視劇創作者需要不斷思考的問題。
注釋:
①湯天甜,應春茜.融合與抽離:影視化神話空間中受眾的生存路徑[J].電影藝術,2020(02):93-99.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212.
③梅瓊林,陳旭紅.視覺文化轉向與身體表達的困境[J].文藝研究,2007(05):93-101.
④湯天甜,應春茜.融合與抽離:影視化神話空間中受眾的生存路徑[J].電影藝術,2020(02):93-99.
⑤吳承恩.西游記[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9:15-51.
⑥許仲琳.封神演義[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107-128.
⑦[法]羅蘭·巴特.顯義與晦義——批評文集之三[M].懷宇 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13.
⑧趙斌.作為一般符號學的電影修辭理論——《精神分析與電影:想象的能指》思想遺產與價值重估[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1):24-33.
⑨[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鄧曉芒 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1.
⑩?胡琴,徐廣飛.意象·景觀·符號:國產網絡劇的身體“神話”[J].文化藝術研究,2020(04):12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