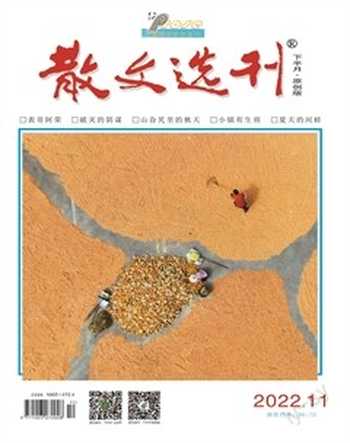六爺
鄭曼

清明節前夕,恰逢小雨,一早父親就打來電話說,今天兩個姑姑和妹妹約好一起回老家給爺爺奶奶上墳。
駛入鄉道,雨已經小多了,零星地飄散著。我跟愛人說:“今天我要多買一些,我六爺去年疫情期間走了,啥儀式也沒有給舉行,上次見我六婆,說埋我六爺就如同埋了一只貓,悄無聲息的,他的一生太可憐了。你城里娃不懂得。”
那是上世紀 80 年代初,整個農村文化貧瘠,村里面啥娛樂都沒有,那時候我們村上的小孩都喜歡六爺,都喜歡圍坐在他的周圍,聽他給我們講古今中外的故事,講仁義禮智信。每次講到關鍵時刻,他就會停下來,端起他心愛的紫砂壺,咕嚕嚕地喝上一大口,我那時曾偷偷喝了一口,苦得我瞬間就吐了,再也不敢偷喝了,也不知道他為啥愛喝苦茶,而且端著那個茶壺,快樂了一輩子。記憶里,他始終微笑著,他喜歡村上所有的小孩,所有的小孩都愛去他門前的石礅子聽故事,和他說說自己的心里話。六爺給所有上學的孩子講知識的重要性,說改變命運就必須要好好努力學習,每次有誰考了好成績,他都會獎勵他一個水果糖。
我那時還小,也不知道大人們都經歷了什么,只知道六爺肚子里咋能有那么多故事,他啥都知道似的,后來大一些追問父親才知道,六爺畢業于鳳翔師范學校,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人民教師……
六爺是我爺爺最小的一個弟弟,他們父親不在時,他才三歲,從小衣食寒酸,在艱難的求學后走上了育人的講臺,一站就是 16 年。在“文革”中,他被批斗了整整一個月,在他身上留下了致命的刀痕,他依然不卑不亢,不申不辯,收拾好行李毅然回鄉種田。此時愛人瞪大了眼睛:“一點也看不出來你六爺還有這樣坎坷的經歷,我每次和你回來見他,都是他坐在村口的大槐樹下,一邊聽收音機,一邊喝茶那微笑的樣子。每次見面都問:‘雨雨娃乖得很。聽你爸說,娃鋼琴彈得好,好好培養娃,你爸那時也是對音樂非常有天賦的,但是咱家成分不好,一生也沒走出去,我這侄子也命運坎坷,啥時把我雨雨娃的錄像拿回來,讓爺看看,聽到娃們都出息,我就高興。說著就端起茶壺,喝一口他那苦茶,笑著說:‘我娃心長的,每次見我都給我拿吃貨,爺小時候沒白愛我娃。完了就給我講起村上以前幾個小伙伴,說他們只要回村,都到他那去,給他匯報一下在城里的狀況。”想到這,我心里泛起一陣難過,哽咽著說,六爺可憐地死在疫情期間,多愛熱鬧的一個人,卻孤零零地走了。“好了,別難受了,一會兒去給六爺多燒點錢,讓他在那邊別受到委屈和排擠。”愛人小聲地對我說……
車一進村子,老遠就看見六婆在村口的槐樹下張望,我趕緊下車,叫了一聲,六婆,你認識我不?這瓜娃,六婆咋不認識呢,你是我曼曼嘛。然后拉起我的手,笑嘻嘻地說道,走進屋走,六婆給你做飯。“你等一下。”我快速從車上提下一箱牛奶,還有些水果,給愛人說讓他把車先開到家去,我一會兒就回來了。我跟隨六婆蹣跚的腳步,朝街道里面走,她不停地說,我啥都有,你還給婆買啥呢,可惜你六爺吃不上我娃的吃貨了。她眼睛瞇著,滿臉笑意地說道。你放心六婆,我一會兒去墳上給我六爺多燒點錢,他想吃啥就自己買。“哦,看我娃乖的,還記得她六爺的呢!”她苦笑著說,“哎,不知道讓誰把鎖子給拿跑了。”(其實她已經患上嚴重的癡呆癥了,經常把自己鎖在門外,孩子把鑰匙給收了起來)還是老舊的兩扇木門,打開后,門道上還放著六爺以前坐的躺椅,那舊得都快成古董的收音機灰塵布滿,放在門道的竹子床頭;院子里六爺親手栽種的杏樹花開得正艷,正如他一生樂觀的生活態度,只是院子里的青苔長滿了院墻的兩邊。土屋陋室里,還摞了厚厚的報紙和書刊。就這一介布衣,粗茶淡飯,想起他八十多歲高齡還在為村上的老年文化事業做著貢獻,心里就不由得一陣酸楚,看著六婆佝僂的后背,我急忙用手拭弄了一下眼角……
六婆現在孤零零一個人住在這兩間土房子里,院墻有好大一截已經坍塌。她說,她要守著這兩間土房子,哪里都不去,幾十年已經習慣了,幾個孩子要接她,她都不習慣,說不去給他們添麻煩,自己啥都能干,再說你六爺隨時回來,家里還有人的。六婆也已經 86 歲了,院子雖然全是土路土墻,但被她打掃得干干凈凈,廚房里還放滿了燒火的柴火,想起來就自己給自己做一頓飯,但是經常就忘記自己吃了沒有,清醒時啥都知道,糊涂起來只說以前老早的舊事。這時六婆家的小姑也來了,她對我說,你六婆死活不和我去,就要守著她這破家,我隔幾天來給洗洗衣服,收拾收拾。我笑著說,隨她吧,年齡已經大了,她咋高興就咋來。“關鍵是她現在啥也記不住了,錢都拿不住,一會兒就不知道了,時而清醒,時而糊涂,把人都能愁死。”小姑愁容滿面地說著,隨手抱起床上的床單被罩,裝進一個大袋子,綁在一輛自行車上,“這些我要拿回家洗,你婆這兒沒洗衣機。”隨后又開始要脫六婆身上的衣服,六婆說不臟,不讓脫,娘倆在屋里開始爭執了起來。
看著被擱置在窗臺上的茶壺和那些舊書舊報,我腦海中就浮現出六爺給我們講故事時的笑臉,不用說,他當年教書的樣子一定也很好看。我給小姑和六婆告了別,說要趕緊回去,今天大姑他們都回來了,一會兒一起去上墳。小姑說她來時順便去墳地了,叫我走慢點兒。
我從土房子里走了出來,看著對門和隔壁的紅磚大瓦房,還有更好看的一家二層小樓,和六爺的家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住了四五十年的土房子,是那么熟悉又那么的扎眼,六爺臨死也沒住過一天的磚瓦新房子,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