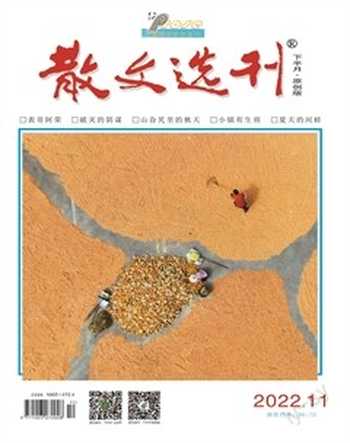小鎮有生煎
徐群

生煎饅頭俗稱生煎,是江南的一種地方小吃,類似于北方人的鍋貼和臺灣的“水煎包”。友相生煎的包子,面軟汁濃,肉鮮底脆,咬一口充滿了蔥香、肉香和芝麻香。友相兢兢業業,技藝越做越精到,日子久了,他的生煎滋味竟聲名遠播。
出鍋時,友相會用鍋鏟在生煎鍋沿上敲打出“當當當”的節奏,入耳又好聽。吃客們偱聲過去,圍在長方形的案板周圍,一個個報出自己需要的數量:我四個,我六個,給我八個,十個……因為大都是熟客,報完數,人們便將錢扔到案板上,然后自己找回零錢。友相拿出一疊干荷葉,攤在手掌上,一個個鏟好生煎遞給他們。那些人拿好生煎,倒點米醋,或站,或蹲,或在河邊的欄桿上坐著吃。有時忙上一陣,生煎還沒賣完,見來客少了,友相會“當當當”再敲一遍招攬顧客。
夏天的晚上,友相也擺夜攤,為的是那些街坊四鄰的老顧客們。午夜,木橋上乘涼的人,肚皮咕嚕咕嚕叫了,整條街都關門了,要想吃點宵夜,唯包子友相的生煎莫屬。那時候,絕大多數人吃不上大魚大肉,生煎的食材也很純正,沒有假冒偽劣的替身,肉鮮蔥香,面粉筋道,有人一口氣吞上八到十個也不算多。
當夜風中飄來生煎的香味,隨后聽到“當當當”鏟子敲擊鍋沿的聲音,食客們就知道包子友相的生煎出鍋了,眾人聚攏在生煎攤前,滿滿一鍋生煎,有時候五六分鐘就見了底。
生煎這種食物就常常在我的閑暇時光,“霍”地從我腦海里跳出來,活色生香。
每次去外婆家,一向儉省的外婆早上總要帶我去買生煎吃。走出外婆家的兩扇黑漆漆的大門,是一條窄窄的石板小弄,走出弄口,走過一座顫巍巍的木橋,橋堍對面就是供銷社的一爿飲食店。飲食店里除了供應大餅油條之外,還賣豆漿生煎。
現煎現賣的生煎才是最好吃的。隔著老遠就能看到排隊買生煎的人歪歪扭扭的隊伍。外婆便去排隊買生煎了。我坐在長條凳子上,仰著臉不時張望一下,貪婪地嗅著從生煎鍋里飄來的陣陣香味兒。見外婆端著生煎走來,我急吼吼地站起身來。外婆用筷子將生煎夾破,用嘴使勁地吹涼,我一口面皮一口肉餡地吃起來。待我將皮、餡統統吃完,外婆又把那金黃的底板送到我嘴邊。如此,一個美好的早晨便開始了。那時候,能吃到香脆帶有肉餡的生煎包,絕對是件奢侈的事情,外婆給我的待遇,也常常惹起比我才大幾歲的小舅舅的羨慕嫉妒恨。時至今日,說起此事,小舅舅還念念不忘。
后來,我獨自去河對岸的飲食店買生煎、吃生煎。我跟在慢慢蠕動的隊伍后面,眼盯著生煎師傅和他的生煎鍋。生煎在油鍋里膨脹,發出吱吱的聲音,排隊的人伸長脖子,我忍不住偷偷咽了幾下口水。當油膩膩的木蓋揭開,一股白霧和焦香味彌漫四周,眼看著生煎們被師傅從鍋里一個個鏟出,直接端到客人面前,我的心興奮得快要跳出來了。誰知快輪到我時,前面那個人把剩下的生煎都包圓了。我又氣又恨,急得快要哭出來了。
在時間的打磨下,當初那個陪我去吃生煎的人已經逝去,她的樣子也變得模糊不清,但她陪我一起吃生煎的場景,還深深地印在我心頭。
許多年后,我又坐到了這家無名小店的方桌前吃生煎了。夾起一個生煎,蘸一點醋,先吃面皮,然后是肉餡……餡鮮汁滿,皮薄底脆。哦,還是從前那個熟悉的味道。我有些滿足地笑了,看外面等著生煎出鍋的眾生相。店外面,那些大人手牽著背個老大書包的孩子,焦急地等在爐邊,十幾雙眼睛盯牢師傅的每個動作。
生煎師傅也是店老板,將一只只雪白的小饅頭在鍋底排列整齊,淋兩勺菜油,煎一面,翻個身,直至雙面金黃,然后潑半碗水。只聽到“吱啦”一聲,無數細小的油珠四處亂濺,一股香噴噴的蒸汽沖天而起,趕緊將木蓋蓋上,不時手墊抹布把住鍋沿轉幾圈。約莫一二分鐘,生煎師傅揭開厚厚的木蓋,隨即撒上一把蔥花,再撒一些芝麻,然后起鍋。剛出爐的生煎,最具煙火氣,瞬間就被搶光。買到生煎的人,提著還燙手的生煎興高采烈地揚長而去,沒買到的只有心灰意懶地等待下一鍋了。
生煎、油炠粉絲湯或一碗豆漿,撫慰著我們日益嬌貴的腸胃,簡單至極,但也美味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