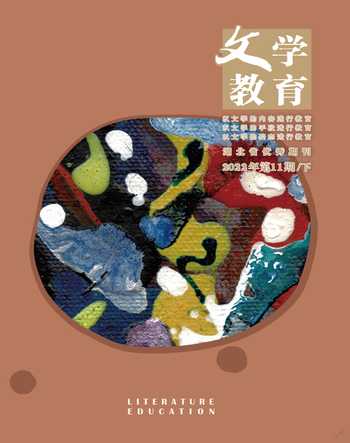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佩劍的符號變遷
賀嘉玚
內(nèi)容摘要:本文通過對古代中國知識分子——士佩劍的歷史進行梳理,分析劍的符號變遷。本文認為,從對抗皇權(quán)的工具之一,到皇權(quán)的授予物,再到文人精神的象征,最后成為一種藝術(shù),直至消亡,“士佩劍”符號變遷的背后,是中央集權(quán)對分封制的摧毀、皇權(quán)的擴張及士地位的下降,以及市井生活的興起。
關(guān)鍵詞:中國古代 知識分子 劍 符號
中國的王朝更替頻仍,但中國的統(tǒng)治階層在“現(xiàn)在和過去,整整兩千年以來,始終是士。”作為統(tǒng)治階層,士的構(gòu)成在兩千年的歷史中發(fā)生了一些變化,這一點,在兩千年來士佩劍的演變中可以發(fā)現(xiàn)。
劍在史前社會先被作為武器使用,由原始人類打磨而制成,它小巧便攜,能夠藏在衣服內(nèi)貼身攜帶,“是一種防備意外的防身兵器”。而古代獵頭習俗盛行,本身就有著象征勝利、證明勇氣、威嚇敵人的意味,而劍在獵頭時能夠發(fā)揮切割敵人頭顱的作用,也擁有了象征的意義。
考古學家在商朝中晚期、北方草原地區(qū)的墓葬品中發(fā)現(xiàn),青銅劍往往出現(xiàn)在青銅禮器旁邊,裝飾精美。劍隨著青銅器一同進入祭祀當中,變得神圣化、禮制化,是祭祀規(guī)定制度化的一種象征。神話傳說中,黃帝作劍、蚩尤作劍的故事和爭論使得劍本身具有了象征意味,劍是“五兵”之一,孔子責罵蚩尤作劍的說法,認為蚩尤貪婪、見利忘義、六親不認,因這些而喪命,他這種人作不出任何武器,劍已經(jīng)與美德聯(lián)系在一起。“在商代中晚期,劍主要被用在祭祀之中……從此,劍不但開始有了一些真正文化或統(tǒng)治秩序意義上的象征作用,還被更加深入地渲染上了一層神秘主義的光環(huán)——玄奧可通鬼,威權(quán)緣自天。”
一.規(guī)范:區(qū)分地位和階級
周時期的鑄劍水平并不高超,劍身較短,在以戰(zhàn)車為主要作戰(zhàn)工具的當時,長柄武器、弓箭才是軍事作戰(zhàn)中更常用的武器,短劍只能用作近身自衛(wèi),貴族隨身佩劍先是為了自保。除此之外,劍的制作工藝也十分復雜,普通人在經(jīng)濟上無法負擔得起,再加上對貴族“文武兼修”的要求——既能精于詩書禮樂,又能統(tǒng)兵為帥——這種文化就為劍作為禮儀裝束的流行和被認可提供了豐富的文化土壤。隨后,西周“西戎獻劍周穆王”的故事描畫出強盛的周王朝對少數(shù)民族的武力優(yōu)勢,劍在其中成為外交的符號,劍具有了更高的地位。此時的中原地區(qū)貴族的墓葬頻繁發(fā)現(xiàn)青銅劍,這顯示出少數(shù)民族崇劍的習俗對中原文化的影響,劍突破了禮器和武器,成為貴族的裝飾品。從這時起,劍的主要功用已經(jīng)轉(zhuǎn)變成了貴族身份的象征,貴族帶劍之風蔚然形成了。
德國社會學家格羅塞曾說過:“在較高的文明階段里,身體裝飾已經(jīng)沒有它那原始的意義。但另外盡了一個范圍較廣也較重要的職務(wù):那就是擔任區(qū)分各種不同的地位和階級。”劍在當時就是區(qū)分地位和階級的符號之一。周公旦所規(guī)定的世襲制和嫡長子繼承制作為宗法制度規(guī)定了貴族的繼承原則,貴族與平民之間、各級貴族之間有著明顯的禮制規(guī)定,不可僭越。《春秋左傳正義》寫道:“車馬、旌旗、衣服、刀劍,無不皆有法度”。劍的佩戴具有了劃分階級的色彩,只有貴族才可佩戴。《老子》中提到“服文彩,帶利劍”,描繪了貴族熱愛穿華服、帶利劍的情形。
二.象征:品性的高潔
屈原在《楚辭》中寫道:“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長鋏即劍,貴族屈原佩戴原本作為武器的劍,劍指示身份的功能之外,更暗含美德。
士將長劍看作是自己的好友,甚至是自己的象征。孟嘗君的門客馮諼向孟嘗君抱怨自己生活待遇低,吟唱道:
長鋏歸來乎!
食無魚。
長鋏歸來乎!
出無車。
長鋏歸來乎!
無以為家。
馮諼對著自己的長劍發(fā)牢騷,實際上是在向孟嘗君提要求,第三個要求被認為是非分之情,但孟嘗君沒有斷然拒絕,而是給馮諼的老母親送去吃食用品。一來沒有破壞規(guī)矩,二來拉攏了馮諼,三來顯示出他的雅量,吸引更多人才,他也得到了馮諼的效忠。在這里,馮諼隨身攜帶的長劍是他傾訴的對象,就算馮諼生活貧困,但他依然必須有自己的佩劍,而且還無比珍重,回家也要一塊兒回——劍是士高潔氣質(zhì)的代表。
劍指向權(quán)力與指向正義兩種取向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經(jīng)定型,從此,劍既成為身份的象征,又寄托了文人的情懷,面對著皇權(quán)的擴張,劍的這兩個方面也愈發(fā)清晰。
三.武器的權(quán)力意志
宗法制里各貴族層級遞減,跌落到士——貴族最底層——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曾經(jīng)接受過教育,在動蕩的社會中也有一番抱負,是當時社會的知識分子。戰(zhàn)國時期養(yǎng)士之風盛行,士成為為大貴族建言獻策的門客,擁有參政議政的權(quán)力。
佩劍原本是貴族的標志,在戰(zhàn)國,舊的分封制分崩離析,新的封建制度在改革下誕生,佩劍的權(quán)力下放到平民。公元前409年,秦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七年,“令民初帶劍”,能夠帶劍的群體大大向下延伸,主要是“士”這個階層。秦簡公面對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主動改革,把原本只由上層貴族才能享受到的特權(quán)下放,士一級的貴族擁有了更多的權(quán)力。
士佩劍擁有了與權(quán)力相抗衡的能力。按遂執(zhí)劍質(zhì)問楚考烈王為何猶猶豫豫不能定奪合縱之事:按劍這個動作是一種威懾。唐雎更是面對權(quán)力毫無懼色,面對秦王的憤怒及是否聽過天子之怒的威懾,唐雎以士之怒回擊,直接舉出“專諸刺王僚、聶政刺韓傀、要離刺慶忌”的例子,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為回應(yīng),挺劍而起。可見在戰(zhàn)國時,士是能夠佩劍直面皇權(quán)的,且他們有著武器,有著剝奪王肉體存在的能力,因而在很多情況下是對皇權(quán)的制約。
庶人佩劍又讓貴族佩劍有了更加高貴的內(nèi)涵。莊子在勸說趙文王停止觀看人斗劍的愛好時,講述天子之劍、諸侯之劍、庶人之劍的區(qū)分,他細細講了每一級別劍的象征:天子之劍象征天子的權(quán)威,諸侯之劍象征諸侯的威勢,庶人之劍則與斗雞無異。在《莊子》的故事中,劍是不同的,天子、諸侯的劍始終是為了國家和社會,只有庶人的劍是為了個人欲望。這和錢穆關(guān)于知識分子的觀點不謀而合,傳統(tǒng)中國的知識分子多以參政議政作為實現(xiàn)社會理想和抱負的唯一途徑,能夠從普遍的道德倫理規(guī)范中推演到超越階級屬性的政治構(gòu)想來。這種對階級的超越在戰(zhàn)國時期最為明顯:“戰(zhàn)國知識界,雖其活動目標是上傾的,指向政治,但他們的根本動機還是社會性的,著眼于下層之全體民眾。他們抱此一態(tài)度,使他們不僅為政治而政治,而且為社會而政治,為整個人文之全體性的理想而政治。”也就是說,春秋戰(zhàn)國時期政治大門的打開,知識分子得以通過政治對人類文明做出貢獻。孔子周游列國,孟子見梁惠王、齊宣王等,無不顯示出古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對政治和社會的熱愛,他們著眼的,總是全體民眾,而不是個人興趣。
而后,隨著皇權(quán)的集中,臣子上朝被剝奪了佩劍的權(quán)力,荊軻不得不將匕首藏在畫卷中謀刺秦始皇,而殿內(nèi)沒有一個大臣能夠救他。在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秦始皇)銷天下兵,則民間刀劍戟槊鏑盡以為金人十二。意者吏尚帶劍而民則莫敢有劍者矣。”民間佩劍的現(xiàn)象消失,佩劍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特權(quán)。到漢代,“劍履上殿”成為皇帝表彰功臣的禮儀之一,唯有功勞巨大或權(quán)力滔天的臣子才能被皇帝特許持劍上殿。持劍上殿成為禮儀上極為貴重的符號,是皇權(quán)賜予的。
四.落寞的俠義
漢初,劍逐漸被利于砍殺的刀所取代,一些將校官吏由佩劍改為佩刀。劍作為武器的意味逐漸降低,劍被文人墨客視為氣質(zhì)和性格的標志,借以抒情,具有高度的審美意義。除此之外,還與舞蹈結(jié)合。
東漢,太學興盛,士擁有極高的社會地位,他們的社會地位讓他們藐視政治權(quán)力,“他們的人生,成為一件藝術(shù)品。”高尚不仕的風氣讓士在政治之外,成為純粹平民式、書生式的階級,名士之風誕生,這種傳統(tǒng)從東漢一直延伸至南北朝,名士再加上門第,維系了中國文化的延續(xù)。在南方,東晉門閥政治治下,士族人才日趨退化,政治腐朽,玄學興盛,名士為自我的滿足而清談;在政局動蕩的北方,各門第依然為著穩(wěn)定的政府而進行戰(zhàn)爭。這時的名士非常多:竹林七賢、陶淵明、鮑照、謝靈運等寄情山水,不同流俗,阮籍以劍作為詩歌中的重要意象,抒發(fā)自己在政治上不得不緘口莫言的悲憤哀怨之情,陶淵明詠誦荊軻的俠義,重點也放在他的劍上,云:“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鮑照以劍直抒胸中悲壯激烈的情懷,慷慨而高貴。
隋唐時期,門閥勢力興盛,唐代的士多從門第而來,對政治積極合作,氣度恢弘,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帶有豪杰氣魄;其后科舉制成熟,政權(quán)向普通人開放,唐的進士們與門第分庭抗禮。唐朝的文學也闊大,詩歌走上高峰,詩人們延續(xù)魏晉南北朝的傳統(tǒng),用劍作為抒情揚志的意象。李白一生好酒愛劍,寫下了“我家青干劍,操割有余聞”,“愿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撫劍夜吟嘯,雄心照千里”的瀟灑淋漓詩句,表達了報國立功的心聲,慷慨豪邁。而當他在政治上遭遇挫折時,也是借劍來抒發(fā),劍象征著他的政治才干:“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裙王門不稱情”,劍也是李白蔑視權(quán)貴、熱愛自由的象征符號:“不待金門詔,空持寶劍游”,“起舞拂長劍,四座皆揚眉”。杜甫在二十歲時浪跡天涯,表達自己“拔劍欲與龍虎斗”的氣概;在經(jīng)歷了多年的流離顛簸之后,老年時發(fā)出了“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的感嘆。邊塞詩人岑參以劍舞入詩,劍與舞蹈結(jié)合,充滿了濃郁的文化氣息和旺盛的藝術(shù)生命力,表達邊塞官兵濃濃的思鄉(xiāng)之情。劍作為文學中抒發(fā)感情的重要意象流傳至今,具備了凝練的審美:劍是友誼、自由、浪漫、風流、修身、神圣的象征。
舞劍則是在斗劍基礎(chǔ)上形成的具有較高審美情趣且呈現(xiàn)程式化的項目。從春秋起,舞劍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孔子·家語》記載“子路戎服見孔子,仗劍而舞”,舞劍已經(jīng)是君子修身的方法。秦以來,劍作為士隨身佩戴的武器擁有了藝術(shù)的色彩。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故事帶有明顯的軍事、政治外交色彩,項莊是以“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作為舞劍的原因,說明那時已經(jīng)有舞劍藝術(shù)了,且確實能夠揮劍助興,烘托場面。到了東晉時期,劍術(shù)開始遵循“重術(shù)輕擊,多練少戰(zhàn)”的理念發(fā)展,士依然隨身佩劍:祖逖“聞雞起舞”,劉琨“枕戈待旦”,為著報效祖國而練武健身,舞劍成為文人鍛煉身體的方式。隋唐之后,劍舞文化達到高潮,甚至女性也可以舞劍,杜甫在《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中描繪到:“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舞劍具有了震撼天地的藝術(shù)色彩。劍舞從隋唐開始,走上舞臺,成為表演藝術(shù)。
宋代門第不再,科舉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重要補充,一時書院風起云涌,“一個尚武、好戰(zhàn)、兼顧和組織嚴明的社會,已經(jīng)為另一個活潑、享樂和腐化的社會所取代了。”文人佩劍的場景已不多見。到了南宋,劍舞基本從舞臺上銷聲匿跡。元朝對武器管控嚴格,且普遍帶刀不帶劍,直至明清,治學風氣盛行,尚武不再,士佩劍的現(xiàn)象從此消失。
從春秋到戰(zhàn)國,再到秦漢大一統(tǒng),佩劍的權(quán)力由貴族擴大到平民,逐漸下放,又從平民收回到統(tǒng)治階級,劍從制約皇權(quán)的工具,變成皇權(quán)的授予物。從魏晉南北朝到北宋,劍由士的象征轉(zhuǎn)為一種藝術(shù),士佩劍逐漸失去其象征品格的意義,最終,士佩劍消亡在宋明清繁華的世俗生活中。
從對抗皇權(quán)的工具之一,到皇權(quán)的授予物,再到文人精神的象征,最后成為一種藝術(shù),直至消亡,“士佩劍”符號變遷的背后,是中央集權(quán)對分封制的摧毀、皇權(quán)的擴張及士地位的下降,以及市井生活的興起。
參考文獻
[1]湯學智.臺灣暨海外學界論中國知識分子[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韋伯.儒教與道教[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5.
[3]陳肯.挑燈看劍:混在殺戮里的浪漫情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4]楊彥鵬.戰(zhàn)國秦漢劍的凡俗化研究[D].西北師范大學,2014.
[5]格羅塞.藝術(shù)的起源[M].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87.
[6]杜預,孔穎達.十三經(jīng)注疏·春秋左傳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7]司馬遷.史記[M].上海:中華書局,1959.
[8]吉燦忠,郭強,劉帥兵.劍“文”化進程之研究[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6,50(09):50-55.
[9]楊祥全.中國武術(shù)思想史綱要[M].逸文武術(shù)文化有限公司,2010.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