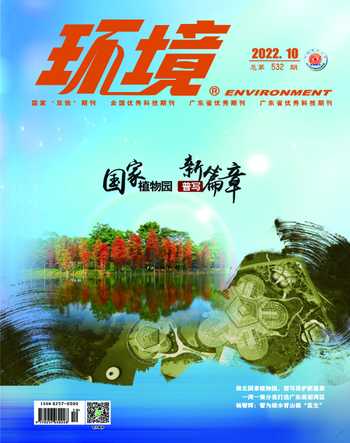黃宏文:提出“國家植物園體系”概念的“學界第一人”
張曉芒
隨著2022年7月11日華南國家植物園在廣州正式揭牌,“黃宏文”這個名字頻頻被人提起,不少業(yè)內人士都說:“華南植物園能這么快入選‘國家隊,有黃宏文大量的心血和功勞,他是我們學界公認的提出‘國家植物園體系概念的第一人。”黃宏文是誰?他與華南國家植物園有著什么樣的故事?在筆者與華南國家植物園工作人員的交流過程中,一段段黃宏文與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以下簡稱“華南植物園”)的往事漸漸退去塵封浮出水面。
學界“第一人”
畫國家植物園體系“藍圖”
黃宏文,1957年出生,湖北武漢人,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現任國際植物園協會(IABG)秘書長、中國植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植物園聯盟副理事長;國際生物多樣性計劃中國委員會及中國科學院生物多樣性委員會委員、中國園藝學會獼猴桃分會榮譽理事長、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主任……
這位低調的植物學家,極少接受媒體采訪,筆者只能從“百度百科”搜索關于黃宏文的信息,一連串的任職信息,無不告訴我們,這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植物學“大咖”。而他與華南植物園的緣分,其實從2006年就開始了。
2006年11月,黃宏文被中國科學院從武漢植物園調任到華南植物園擔任主任。在工作正式交接之前,黃宏文仍作為武漢植物園主任以“東道主”的身份,舉辦了2007年4月在武漢召開的世界植物園大會。這次大會有來自9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千余名代表出席會議,共同展望中國以及世界植物園的發(fā)展未來。也正是這次會議之后,我國國家植物園體系發(fā)展的序幕被正式拉開。
這次大會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植物保護組織——國際植物園保護聯盟于2008年首次在中國設立了項目辦公室。項目辦公室應黃宏文要求被設立在華南植物園內,其主要職責是協助《中國植物保護戰(zhàn)略》的實施,其目標是將直接的植物保護行動與硬性的法規(guī)結合起來以促進中國的環(huán)境教育和能力建設。此舉為華南植物園的日后發(fā)展注入了國際視野,也為華南植物園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fā)展空間和展示平臺。
也正是這次大會之后,黃宏文意識到“國家之間將面臨著生物資源的激烈競爭,誰先擁有豐富的植物資源并掌握保護、利用植物資源的新知識和新技術,誰就掌握了主動權”,隨即在2007年6月的《瞭望》雜志提出,我國“急需國家植物園創(chuàng)新體系”。這篇文章,為黃宏文成為提出“國家植物園體系”概念“學界第一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也為我國下一步發(fā)展國家植物園體系提出了具體設想。
在這篇文章中,黃宏文分析了我國植物園的發(fā)展現狀及面臨的問題,尖銳地指出“由于統(tǒng)一行業(yè)標準和運行管理機制的缺乏,已嚴重阻礙我國植物園體系的良性發(fā)展”,同時具有前瞻性地提出“結合實際制定中國國家植物園組成成員標準,先評估核定中國科學院的5個核心植物園和9個重點植物園作為國家植物園基本組成,形成中國植物資源保護和研發(fā)的國家體系,再逐步形成擁有約30個國家級植物園的國家植物園體系,引領全國約200個植物園在植物資源保護和可持續(xù)利用上的作用,逐步成為國際植物園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文為我國國家植物園體系從學界的角度規(guī)劃了一張“藍圖”。此后,黃宏文懷揣建設國家植物園的夢想,深深扎根于華南植物園這片土壤,用近十年的耕耘,為華南植物園的未來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地奉獻著自己的全部力量。
“救活”溫室
邁出國際化建園第一步
從高空俯瞰,華南植物園中的湖畔靜謐地盛開著四朵巨大的“木棉花”,這就是被認為是廣州標志性建筑之一的“世界植物溫室群景區(qū)”。
展覽溫室項目為中國科學院、廣東省、廣州市共建的重點項目,由一主三副共四個不同主題的獨立展館組成,外形取自廣州市花——木棉花的形態(tài),總占地面積約1萬平方米,主要用于保育、展示熱帶雨林、亞高山植物、多漿植物和奇花異果。
“溫室中的植物保育工作,需要考慮溫度、濕度,還有病蟲害等防治,是一個非常系統(tǒng)的工程,需要深厚植物學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支撐。”“知情人”告訴筆者,當年黃宏文的調任,正是為了建設溫室景區(qū)建設“臨危受命”而來。
當時,由于前期施工單位缺乏專業(yè)經驗,且未充分發(fā)揮植物學家在溫室項目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導致大量遷地植物不管怎么種植,始終長勢不好,溫室群景區(qū)也就無法達到如期向公眾開放的既定目標。
在這樣的情況下,黃宏文離開了工作、生活了多年的家鄉(xiāng)武漢,前往廣州“救火”。剛一到任,他就以其豐富的專業(yè)知識對溫室內景觀設計施工、生境營造、植物布置的基本理念及技術進行了重新設計。新設計方案遵循國際先進植物園景觀溫室的設計及布展理念,注重新、奇、險原則,充分展示千奇百態(tài)的植物多樣性及和諧的景觀布局一致性,同時還注重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景觀及植物配置創(chuàng)作理念,體現“雖自人工,宛若天開”的效果。此外,新方案還充分考慮溫室內外連續(xù)完整的布局,注重建筑、植物及周邊環(huán)境的協調以及三維空間的完整性,既符合植物園建設的發(fā)展方向,又富有植物學與生態(tài)學內涵。
歷經四年興建,耗資近億元,華南植物園溫室群景區(qū)于2008年建成并正式對外開放,獨特的造型、豐富的主題及特色鮮明的園林景觀讓它成為廣州市的標志性建筑之一,也是全亞洲乃至全世界最大型的植物景觀溫室之一。據植物園園藝中心相關負責人介紹,“共建完成后,華南植物園不僅是廣州市民休閑娛樂和科普學習的重要場所之一,而且是廣東省生物經濟發(fā)展重要平臺和中國南方璀璨的綠寶石。”
此后,華南植物園在物種保育、科學研究、資源利用和科普旅游等方面都實現了跨越式的發(fā)展,在全國開創(chuàng)了院地合作開展大型建設項目的先河。
此外,在黃宏文的推動下,華南植物園早在2009年就開展了國際戰(zhàn)略評估。世界著名植物園主任和國內外知名植物學家組成評估專家組對植物園進行的國際戰(zhàn)略評估認為,華南植物園是全球引領性植物園及研究機構之一,并給出了30多條寶貴建議。
“國際戰(zhàn)略評估的成功舉行,為華南植物園科興謀劃后續(xù)的發(fā)展,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華南植物園相關專家告訴筆者,此次的評估對華南植物園的發(fā)展具有里程碑意義,是華南植物園對標國際發(fā)展的重要舉措,“國際戰(zhàn)略評估也進一步提高華南植物園在植物學研究領域中的國際地位和影響。”
就這樣,在黃宏文的“掌舵”之下,華南植物園對標國際植物園建設標準,不斷接軌國際體系,一路向著高水平國家植物園方向穩(wěn)步發(fā)展著。
編志建庫
提升華南植物園學術地位
“在華南植物園遷地植物研究發(fā)展史中,不得不提到一本書。”華南植物園工作人員口中的這本書,正是由黃宏文牽頭主編的《中國遷地栽培植物志》。
眾所周知,華南國家植物園不僅代表了華南地區(qū)植物園建設的最高水平,在植物科學研究方面也具有相當的專業(yè)高度及廣泛的國際影響力,特別是在遷地保護方面,涵蓋了華南地區(qū)各植物類型。作為該書編研工作牽頭單位時任負責人,黃宏文于2011年初就立足我國植物園遷地保育植物的全面整理,開始籌備植物志的編撰工作。
“《中國遷地栽培植物志》的編撰,無論在思想、原則和進展,都尚屬世界首例!”黃宏文表示,這是一項大型學術編研計劃,項目組要對現有遷地栽培大于100種的科和特殊類群進行編冊,預計成冊80—100卷(冊),計劃實施10—20年。
“歷經10年對活植物收集整理,我們構建了我國遷地保護植物綜合數據庫,基本摸清了我國植物園遷地保護植物‘家底。”2022年上半年,黃宏文在廣州接受采訪時介紹說,“《中國遷地栽培植物志》致力于創(chuàng)建一本‘活植物志,成為支撐我國植物遷地保護和可持續(xù)利用的基礎數據信息平臺。”
截至2022年3月,《中國遷地栽培植物志》已正式出版19卷(冊)、審校排版2卷(冊),完成了一批活植物名稱修訂、物種分類學描述及特征補充,發(fā)表了一批新分類群,提出了新增一批受威脅等級植物,為我國農林、醫(yī)藥、環(huán)保、新興生物產業(yè)提供源頭資源信息和種質資源保障。
目前,以科或重要屬成卷(冊)的《中國遷地栽培植物志》仍在陸續(xù)編纂之中,華南國家植物園掛牌后,也將繼續(xù)進行這項大型學術編研計劃。隨著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進入新階段,遷地栽培植物志的編纂,將對國家植物園發(fā)揮遷地保護功能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據專業(yè)人士表示,這也是繼植物學界巨著《中國植物志》后,中國植物學研究領域又一重大的植物基礎性項目。
《中國遷地栽培植物志》植物志的多年編撰工作,使華南植物園在產出大量學術成果的同時,也打造出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隊伍,對提高華南植物園專業(yè)管理水平和人才隊伍培養(yǎng)具有重要意義,為華南植物園升級為國家植物園奠定了學術和人才基礎。
鑒于此基礎,華南植物園近年牽頭編制了《中國植物園植物引種收集與遷地保護管理規(guī)范》,出版了《中國遷地栽培植物志》和《中國植物園標準體系》,開發(fā)了“植物信息管理系統(tǒng)(PIMS)”和移動終端數據采集APP,為我國植物園建立了遷地保護規(guī)范管理體系和活植物研究體系。
雖然黃宏文早已卸任華南植物園主任一職前往廬山植物園工作,但在廣州這座美麗的大城名園中,將一直流傳著這位植物學家為推動國家植物園體系發(fā)展、建設華南植物園成為世界一流名園的故事。黃宏文的名字,也將和眾多為華南植物園的發(fā)展傾情奉獻過的科學家們一起,被寫入華南國家植物園的發(fā)展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