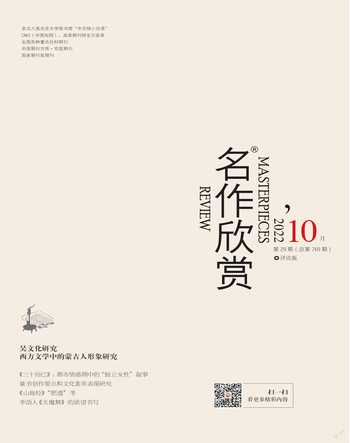從《文城》看余華的創作變化
關鍵詞:余華 《 文城》 創作變化 文本結構 人物形象
20世紀80年代,余華作為先鋒作家出現在文壇,他的小說關注苦難與死亡,關注暴力和罪惡,小說的形式是以背離生活日常經驗出發,將人性之惡推理到極致,達到觸目驚心的地步。這種寫作以格式的特別吸引了眾多的目光,盡管那時的文字還有諸多問題,比如作家判斷事物常常陷入極端化的境地,在人性的挖掘力度上有些力不從心。
余華是一個很有反省能力的作家,很快,他的作品從想象中突圍出來,從先鋒走入現實。《在細雨中呼喊》應該是先鋒和寫實主義創作的一座過渡橋梁,小說開始重新打量個體與世界的關系,將時光的碎片進行重組,追述了自己及他人過去的故事,更好地闡述了人的生存哲理、命運無可預知性、家庭倫理的無序性,童年孤獨和幻想性等,在這些敘述背后,愛與恨、恐懼與敬畏、憤怒與自卑等情緒沖突彌漫在作品中。
先鋒作家需要不斷地超越自己。此后,余華又開辟新的寫作空間,在轉型中完成對自己以往創作經驗的顛覆和解構,當然這種顛覆不是完全推翻過去的創作理念,而是藝術手法的調整和疊加,在先鋒和現實中穿梭自由。從創作初期到新近作品《文城》,他向小說的深度挖掘,不刻意追求形式的新穎奇崛,作品外表更加樸實,內蘊卻更加深厚。
一、創作手法的變化——冷漠敘事到激情描寫
余華在前期創作中,瘋狂迷戀寫非正常人的生活和精神狀態,因為瘋子的世界是和常人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們的行為不受大腦的控制,所以荒誕就成為一種可能性。《一九八六年》中,余華用冷漠敘事寫了一個人的發狂史,也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發狂史。一位被抄家、被關押的歷史老師,發瘋流浪二十年后,回到小鎮。這個業余研究中國古代刑罰史的老師,在幻覺中對周圍的人群施以酷刑,實際上他用破刀、鋸條等在自己的肉體上做著各種可怕的自殘行為:劓、剕、宮、凌遲。場面血腥令人不寒而栗,而余華卻鎮定自如地再加上一筆更可怕的描寫,這個瘋子的附近,他已改嫁的妻子與他的女兒只是擔心自己的幸福生活被打擾,感到無比的恐懼,直到瘋子死了,她們如釋重負,又回到了所謂的幸福生活中。人性的卑劣和殘忍被描述得如此清晰。余華的作品,常常能使人想起他的前輩同鄉魯迅,那種深廣的憂憤之情,一直抑郁在他的胸口。他懷著知識分子的良知,探尋歷史的真相,以向死而生的勇氣,揭示病態社會的病態人生,給人以心靈的震撼。對余華而言,先鋒寫作,是打破了既有的思維定勢,而現實主義的寫作是隨著年齡的成熟,視野的開拓,理解人世深入的必然結果。
早期的余華在敘事的時候,突破現實秩序的羈絆,不受日常生活經驗和常識的規定,不受既有邏輯規則的限制,用冷靜客觀的目光窺視著這個世界,講述著暴力、血腥、屠戮、殘忍,突出個體在巨大的事件面前的弱小和無能為力,甚至有時歸之于命運的安排。
然而,在《文城》中,余華的創作手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先鋒時期,他顛覆他人的創作經驗,現在,他顛覆自己的創作經驗,這一點,在其他作家身上比較少見。他慣常的冷靜敘事不見了,在《文城》中,很多片段常常能看到作者帶著極大的激情在敘述。比如,溪城保衛戰,可以用“壯烈”二字來形容也不為過,團領朱伯崇,一生戎馬,從清軍到西北團,再到溪鎮的民團,率領著曾被土匪割去耳朵的民眾浴血抵抗,最后犧牲在城墻上,十八個民團士兵與一百來個土匪戰斗,最后全部壯烈犧牲,其場景讓人讀之落淚,不能不感嘆中國普通民眾的韌性,他們曾經膽怯過,但當保衛家鄉的重任賦予他們時,他們舍生忘死的精神激勵了溪鎮的所有人,民眾拿出家里的菜刀、柴刀、木棍、長矛,一齊殺向城外,終于擊退了土匪。一個作家就是有責任寫出這些高尚的靈魂,激勵更多的人鼓起勇氣對抗邪惡。在這里,余華不再像早前一樣冷眼觀世界,而是寄予了這些底層民眾極大的贊譽,飽含熱情地敘寫他們的英勇和不朽。我們透過文本聽到一顆溫暖的強有力的跳動的心聲,那是對這個世界的大愛、對人類生存在的追問、對人性正義的追問,通過作品,預見人類未來的精神走向。
二、文本結構的變化—— 碎片拼接到以偏補正
余華早期的創作顯示了他先鋒派的特征,用碎片化的、看似凌亂的故事編織起一張巨大的網,人物符號化。細讀他以往的先鋒小說,因果鏈完全破碎,故事的前因后果不甚明了,動機常常被瘋狂的舉動取代。顛覆一切、解構一切權威和現有秩序,是他小說的源動力,在支離破碎的片段化故事中,每個讀者都在用自己的想象力重新組裝文本,得出的結論也是多元化的,就像一個多棱鏡,折射出不同的光彩。
《 十八歲出門遠行》中,碎片是由少年、司機、蘋果、汽車、老鄉組成的。少年尋找旅館,遇到司機,司機遭遇搶劫卻毫不在意,最后,司機搶了少年的東西駕駛拖拉機揚長而去,而少年坐在司機留下的沒用的卡車里,卻有找到了旅館的感覺。
《在細雨中呼喊》仍是由無數的記憶碎片組成,童年在村里的池塘邊游蕩、弟弟被淹死的鏡頭,祖父、父親、兒子三代間的隔膜,寡婦與眾多男子的情欲糾纏,與蘇家兩兄弟的青春往事,等等。文本的敘事沒有按時間順序,而是通過一個孩子的視角,如剝筍般,層層閃現孫光林的童年生活,四個部分既是一個整體,又能單獨成文。余華在創作中不斷總結、反思。在余華看來,記憶是通往現實的一個神秘通道。在返回記憶的過程中,不需要受太多的時空限制,虛幻性和現實性的結合,使作品真真假假、變幻莫測,形成獨特的審美效應。這種文本結構的變化,并非突然而來,而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看待生活的態度自然會有所變化,現實的世界更加吸引著作家的注意力。這種內外因素,引導著作家從文本形式向文本深度探尋。
1992 年發表的《活著》,文本結構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化。這部十二 萬字的長篇小說,線索已經非常清晰,作品以福貴的一生作為主線,它描述了福貴數十年間坎坷崎嶇、令人唏噓的命運遭際。小說的敘事以“我”在樹蔭下聽福貴講故事起筆,以福貴的口吻回憶他的一生,敘述的中途又常常被打斷,龍二之死、有慶之死、家珍之死、苦根之死后都是回到現在時,回到田埂上。小說呈現了“現在——過去——現在”的結構布局,首尾分別用福貴的歌聲呼應,開頭的歌謠“皇帝招我做女婿,路遠迢迢我不去”,設置了懸念;結尾處的歌謠“少年去游蕩,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則意味深厚,有著蒼涼的韻味。
《文城》的謀篇布局與以往的作品完全不同,采用了“正篇”+“補篇”的方式,“正篇”七十五個章節,“補篇”三十六個章節。“正篇”以男主人公林祥福為主,敘寫了這個北方漢子的傳奇一生。從他五歲時父親去世寫起,十三歲跟隨管家田大下地視察,去鄰村的木匠師傅那里拜師學藝,十九歲母親病倒、去世,二十四歲遇到小美和阿強,二十五歲小美離家出走,留下女兒林百家,其后的十七年時間里,他帶著女兒南下到了溪鎮,尋找小美,在這個過程中,開辦木器社,認識陳永良、顧益民,最后,被土匪頭子張一斧殺害。“補篇”是以小美為主線,從她十歲以童養媳的身份進入溪鎮織補店沈家寫起,敘述了她在沈家兩次遭遇休書的故事,最后,阿強偷偷拿了家里的錢財,帶著她一起去北方私奔,花光了所帶錢財后,所坐馬車車輪破碎,他們投宿林祥福家。走投無路下,阿強謊稱他和小美是兄妹關系,設計讓小美留下,并約定在定川車店相見。小美偷取金條后,與阿強相會,誰知已懷上林祥福的孩子,又回到林家,將孩子生下后,與阿強重返故里,直到懷著羞愧之心,在城隍閣的祭拜儀式上凍死。“補篇”以揭開謎底的方式,補敘了十七年前的種種懸疑,和“正篇”的內容相互呼應。小說的布局奇妙之處正在于此,“正篇”一次次布下迷局,文城在哪里?小美和阿強在哪里?溪鎮是文城嗎?林祥福會找到小美嗎?每一個疑問,在文本的閱讀中都激起了讀者的探險意識,這不能不說是余華寫作技巧的高明。就像一個相聲演員,永遠把包袱放在后面抖開,“補篇”就起到了抖開包袱的作用。在《文城》中,農村社會尖銳的階級對立被弱化,人性的力量被強化。作品中的鄉紳具有了儒家的仁義情懷,是一種民間英雄的形象。如果說碎片化的寫作帶來的是多元化的解讀效應,那么“以偏補正”這種在傳統寫作道路上的回歸與創新,則使小說的指向更加明朗,作者要表達的情緒更加明顯。
三、人物形象的變化——卑微忍讓到堅強崇高
余華早期作品中,人物在面對苦難時,往往采用的是忍讓的態度,人物在生活的苦難現實面前要么自我釋懷,要么默默忍受,直至死亡。《十八歲出門遠行》中,少年忍受著不可思議的欺詐和暴力,最后無可奈何坐到被遺棄的汽車里;《活著》中,福貴面對親人們的離去,束手無策。福貴的性格里藏著中國古老的生存哲學,對現世的忍耐和執著的生存意志。
到了《文城》,小說中的主人公有一個成長的過程,從卑微忍讓到堅強崇高。《文城》并不是一個三角戀的故事,這篇小說與情愛無關,與人性相關,與苦難相關,與成長相關。文城在林祥福的想象中,是一個“出門就遇河,抬腳得用船”的南方小城,那里沒有北方的毛驢。那里的女人都像小美一樣頭戴藍印花布的頭巾,穿著木屐,“尤其是夏天傍晚的時候,在河邊洗干凈腳以后,穿上木屐在城里的石板路上行走,木屐響成一片,就像木琴的聲音”。那里的人說話語速快,有自己特有的腔調。余華沿用了他一貫的寫法,用不連貫的,卻又相關的事件編織了一個復雜、多層次的敘事故事之網,將幻覺、現實、想象、回憶穿插在一起,進行了時間的重新排序,表現了人性在任何一個歷史時代的存在的重要性。這種想象使筆下的故事和人物都獲得了自由,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傳奇故事,更是這個故事背后隱藏的深層次的象征意義。
在《文城》中,苦難依然沒有退出生活的現場。老實本分的林祥福一次次面臨著小美和阿強的欺詐,一次次選擇忍讓。他們向林祥福借宿一宿,卻謊稱是兄妹,這是第一次欺詐;當林祥福收容他們,并告訴他們“在方圓百里之內他算得上富裕之戶”時,阿強的眼睛閃亮了,接著開始設套——小美突然病倒,哥哥離開到定川的車店等待小美詐騙成功,等到小美如愿拿到了七根大金條,一根小金條后,他們如愿離開定川的車店,這是第二次欺詐;當小美在良心的驅使下,決定把林祥福的孩子生下,又一次來到林家,林祥福追問阿強是什么人,小美仍然回答“我哥哥”,林祥福既往不咎,隆重舉辦婚禮,小美當天生下女兒,幾個月后,再次逃離,到臨川的出租屋和阿強會合,并南下回鄉,這是第三次欺詐。盡管在敘述的過程中,作家采用第三視角,寫出了小美的很多無奈,但一次次的欺詐背后,讓人看到了人性中的卑劣。小美們在對目標的追逐中,拋棄了自我,沒錢他們窮困不能生存,得到金條后,他們精神貧乏,終日活在內疚和恐慌里,完全喪失了自我。林祥福面對欺詐,卻沒有用欺騙回報這個世界,而是用他的處事方式——忍讓,善待這個世界。他知道小美和阿強的名字是假的,文城也一定是假的,可是還是執著地去尋找,與其說他在找一個地方,一個人,不如說他在尋找一個充滿真善美的理想桃花源。
在林祥福的兩大人生事件中,前一個尋找小美,是他性格中堅強的體現,后一個刺殺土匪,則是他崇高的表現。他也曾懦弱過,經歷了龍卷風,來到溪鎮,并沒有找到小美時,他的心里凄涼了,那一刻他想回家了,想到家鄉的毛驢、田地、宅院,但是他看到女兒時,他堅強起來,女兒需要母親,他需要小美,這個信念又使他義無反顧地重新踏上尋找之路。在刺殺土匪的情節里,文本大量描摹了土匪的為非作歹。土匪水上漂對溪鎮綁票的虐待——鐵鉗烙屁股、割耳朵等事件,寫得細膩而殘忍,讓讀者驚醒:我們生活的世界,獸性已經吞噬了僅存的人性而不自知,人的兇殘到達了泯滅良知的地步。當大家指望他去贖回顧益民時,他猶豫,但終于戰勝恐懼,答應去贖回顧益民。面對土匪的威脅,他吃了人肝,卻不敢嘔吐,但聽說土匪把朋友顧益民殺害并挖了心肝炒了吃時,這個原本忍讓的北方漢子眼睛血紅了,拿了尖刀刺向土匪頭子張一斧,最終被張一斧刺死。 死亡讓林祥福的生命終止了,但是他的精神維度卻獲得了新生并高大起來,他的重情重義、他的仁厚寬容,他的堅強崇高都成了一種象征,帶有了崇高美學的意義。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里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對善和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
余華的創作風格總是在不斷變化,就像筆下的林祥福在執著追尋一個遙不可及的文城,余華在追求文學上的至高境界。《文城》里沒有自序,但可以想見,“高尚”二字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作家的終極追求,一個作品若能寫出一個時代的變遷和真相,留給后人的就不僅僅是趣味性,文學性,更多的是哲理和歷史的深思。從《在細雨中呼喊》到《文城》,余華追尋的就是在歷史時間中的事件的意義,而在追尋的過程中,創作方式的多變,使文本的閱讀趣味和深度都得到了加強。他的創作力再次證明了他是一個不重復自己的實力派作家,我們有理由期待他的下一次變化。
作者:沈濱,文學碩士,江蘇省泰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