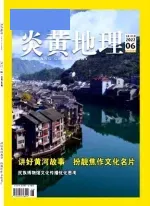中國傳統(tǒng)仕女紋樣的研究
李晶津 王志強



對仕女畫的歷史進行梳理,選取仕女圖中變化明顯的面部特征展開分析,并比較現(xiàn)代女性的審美風格;通過列舉現(xiàn)代活化仕女紋的案例,總結出將傳統(tǒng)仕女紋應用到現(xiàn)代設計中的方法;此外,結合當下時政、社會背景,從不同維度分析將傳統(tǒng)紋樣運用到現(xiàn)代設計中的要求,引發(fā)讀者對時下熱點詞匯的審美思考。
在古代,官宦人家的女子是“仕女”一詞的指代,也作“士女”。仕女畫一般指以封建社會中上層婦女為題材的國畫[1]。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這個概念越來越廣義,凡是表現(xiàn)以女性為主的美人畫都可以稱之為“仕女畫”。仕女畫作為中國傳統(tǒng)人物畫中的一個分支,迄今發(fā)現(xiàn)最早的實體仕女畫,可以追溯到戰(zhàn)國的《人物龍鳳帛畫》,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2]。前人將中國仕女畫的風格概括為一種平緩柔順的整體靜態(tài)之美。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仕女圖中的女子大多笑不露齒,儀態(tài)往往沒有一絲動態(tài)感,這和漢代的儒學、宋明理學下的封建禮制思想息息相關。現(xiàn)將對仕女畫的歷史進行梳理,并對其展開分析,從不同的維度上提出將傳統(tǒng)紋樣運用到現(xiàn)代設計中的應用要求。
不同時代仕女紋體現(xiàn)的特征
仕女畫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兩漢時期,這個時期在許多繪畫當中出現(xiàn)了女性的形象,可以說是仕女畫的萌芽時期。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仕女畫實物是戰(zhàn)國時期的《人物龍鳳帛畫》(如圖1),同時期還有《人物御龍圖》,這兩幅帛畫雖然在技法上都比較稚拙,但其單線墨筆勾勒的畫法為后世的繪畫形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秦漢時期,繪畫中的女性形象逐漸豐富,出現(xiàn)了仕女、農(nóng)婦、歌舞伎等形象;應用場景也很豐富,例如在墓室壁畫、畫像石、畫像磚中都有所應用;畫面場景豐富,出現(xiàn)了宴會、雜技表演等場景。到了六朝時,前人在人物畫的畫法和技巧方面已經(jīng)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這一階段可以稱之為成熟期。宋人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形容此時的仕女畫是“歷觀古名士畫……有婦人形相者,貌雖端嚴,神必清古,自有威重儼然之色”[3],由此可見此時的仕女形象典雅端莊,當時的繪畫技法已經(jīng)能夠成功地表現(xiàn)出人物的情感和氣質。
到了隋唐五代時期,仕女畫已經(jīng)歷經(jīng)了近千年的沉淀,此時仕女畫的繪畫技藝有了新的突破。具有代表性的畫作有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張萱的《搗練圖》等,其中唐代的仕女以雍容華貴為特點,面部豐腴、柳眉星眼、直鼻小嘴、披帛繞胸,神情泰然自得,色彩濃艷雄厚,整體畫面十分生動。五代時期的仕女畫是一個轉折點,此時的風格有些保留了唐代濃麗豐肥的形象,而有些人物身材則變得更加修長,衣著的線條紋樣也更加簡潔,與唐朝的風格有著明顯的差異,比如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如圖2),顯然已經(jīng)接近宋代仕女修長秀美的風格。
唐五代之后一直到兩宋時期,仕女畫比前幾代更加豐富,不再局限于對封建社會上層貴族女性的描繪,也出現(xiàn)了表現(xiàn)社會中下層女性真實生活的畫作,畫師們把題材擴大至平民婦女,突破了貴族范圍“仕”的羈絆[4]。仕女形象由豐腴變?yōu)樾揲L,整體風格由華麗奢靡變?yōu)榍逍阄难拧T院螅娜水嫷陌l(fā)展速度超過了仕女畫,這個時期可稱之為徘徊期。
明代開始,由于社會文化藝術發(fā)展的繁榮,畫家在審美取向上多以商人和市民階層的需求為主,以仇英、唐寅等人為代表的明代畫家創(chuàng)造了“世俗美”的仕女形象[5]。代表作品有唐寅的《秋風紈扇圖》、仇英的《修竹仕女圖》和陳洪綬的《女仙圖》等[6]。然而,明中期以后,仕女形象過于千篇一律,弱不勝衣,了無生氣。清代仕女畫從故事、詩詞、民間傳奇、戲曲小說等題材中取材,仕女造型蘊藉委婉,多是尖臉、削肩、柳腰、蓮步的病態(tài)形象[7]。彼時,中國封建社會即將走向沒落和衰亡,仕女“病態(tài)美”的形象也是畫家對時代不滿的寫照,例如費丹旭的《金陵十二釵》、改琦的《紅樓夢圖詠》等。同時將這種孱弱的特征不斷強化,暗示了當時女性極低的社會地位和不自主性。
不同時代下,仕女紋樣中表現(xiàn)出的審美特征也在不斷發(fā)展和變化,通常與當代的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的發(fā)展息息相關。對文化藝術作品的解讀,也是對社會歷史發(fā)展的透析,比如唐代的富饒表現(xiàn)在仕女豐腴奢華,清朝的社會風氣糜爛表現(xiàn)為女性的病態(tài)之美,這些不同的時代背景造就了不同的紋樣表達方式和造型特點。
從漢代的儒家思想再到宋明理學,封建禮教思想對女性的種種禁錮和束縛導致當時的女子不能拋頭露面。縱觀仕女圖紋,在一幅幅優(yōu)美的畫面中,女子很少有手舞足蹈、眉開眼笑的動感表情,往往只是在花園或庭院中賞花、吟詩、作畫、教子。仕女圖中的仕女多笑不露齒、行無大步,體態(tài)和神情幾乎沒有什么動感和節(jié)奏感[8]。筆者將重點從變化較多的容貌特征著手,探討傳統(tǒng)視域下對女性審美趨向的變化,將其和現(xiàn)代女性審美作比較。
傳統(tǒng)視域下仕女紋容貌審美變革的規(guī)律
臉型指面部的輪廓,也代表了一個人的容貌,其中“容”指儀容、儀表,是人的神韻和氣質所在,“貌”指外貌,也就是指五官大形,如瓜子臉、柳眉、杏眼、櫻桃小嘴、粉面朱唇等可視的外表[9]。中國古代仕女的面部妝容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秦漢女子流行畫廣眉,面部妝容以濃艷為美,面部已經(jīng)開始用鉛粉涂面[10],并且當時的繪畫以神仙形象為主,因此發(fā)型主要以飛天髻為主。
唐代民風自由開放,女子妝容多姿多彩,就以眉形為例,從唐玄宗命畫工繪制的《十眉圖》可見一斑,當時流行的眉形有鴛鴦眉、八字眉、遠山眉、三峰眉、垂珠眉、月棱眉、分梢眉等,在盛唐時期光唇式就出現(xiàn)了17種。并且彼時出現(xiàn)了貼花鈿、描斜紅的女子妝容,影響了今天許多影視作品的妝容創(chuàng)作。據(jù)《中華古今注》載:“長安婦人好為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絕。”由此可見,這種盤桓髻在長安風靡一時[11]。
宋代時期女子以高髻為尚,有代表性的為朝天髻。仕女妝容也與唐朝有著很明顯的區(qū)別,女子摒棄了濃妝,偏愛淡抹[12]。
明朝開始,女子以細眉為美,發(fā)髻以低為主,很少梳高髻,女子妝容上也非常有特點,通常采用“三白法”——即在額、鼻和下顎三個部分暈上夸張的白粉,表現(xiàn)面部層次。
清代仕女畫的層次更多,大體上可以分兩部分來研究,一部分為康乾盛世時期,另一部分為清末晚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跨越百年,反映到藝術當中,其變化更是顯而易見。以彩瓷仕女為例,康熙時期的仕女高髻素衣,細眼彎眉,臉呈杏核形;雍正時期仕女臉施薄粉,吊眉細眼,臉呈鵝蛋形;乾隆時期仕女松髻華衣,額寬頰窄,五官緊湊[13]。仕女妝容素雅,往往上唇不涂唇妝,只在下唇內側略施唇脂,有點類似今天流行的“咬唇妝”。在發(fā)式方面,滿族女子多梳“兩把頭”,到了清末,這種發(fā)式越來越高,漸漸變成了“大拉翅”,與此同時還興起另一種“后垂髻”與“盤髻”的發(fā)式。
將以上變化精簡地概括為圖3,使讀者可以更好地掌握仕女紋容貌。
現(xiàn)代視域下仕女紋“活化”的應用
“活化”這個詞語原本是化學和物理范疇內的專用詞語,但現(xiàn)代視域下“活化”被賦予了新的語境,即為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提供新的用途,使其獲得了新的生命,服務于當今的經(jīng)濟和文化發(fā)展。
現(xiàn)代女性審美風格
近年來,女性的審美風格產(chǎn)生了極大的變化。如仕女紋樣作為當時應用廣泛的形式,就其形象而言,《詩經(jīng)》中就有對其的描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如今,隨著偶像文化的引入,“白、幼、瘦”成為如今大火的審美標準之一。而不可否認的是,現(xiàn)代審美逐漸走向多元化,越來越多的人提出女性美不應該再被傳統(tǒng)局限,不應該再被定義。正如藝術家Hanna Lee Joshi用鮮艷的漸變色調,表現(xiàn)真正的女性之美是不受限制,她們突破了現(xiàn)有社會對女人的局限,其作品優(yōu)美而富有象征意義。
仕女紋活化的運用
2021年河南省春晚節(jié)目《唐宮夜宴》的播出,在網(wǎng)絡中產(chǎn)生了爆炸性的影響,熱度持續(xù)不下。其中穿插了水墨畫、賈湖骨笛、簪花仕女圖等環(huán)節(jié),不僅體現(xiàn)了藝術創(chuàng)作的價值,還體現(xiàn)了非遺文化唐代仕女圖的“活化”運用,有助于提高國人的文化自信,有助于文化傳播。
仕女紋活化的方式
對非遺文化的活化,我們首先要充分了解民族文化,了解我國歷史的發(fā)展,以文化的內核作為傳播的基礎;同時要深入了解人們的內心,激發(fā)民族認同感。其次,現(xiàn)代信息技術已經(jīng)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將現(xiàn)代技術與文化充分結合,使文化的內核更廣泛地傳播。例如,虛擬現(xiàn)實技術、微信表情包的運用、交互設計等。最后,活化離不開經(jīng)濟、政策的支持,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運用多元化的活化方式,說好中國故事,推動文化的傳承和發(fā)展。
現(xiàn)當代對于仕女紋的總結及反思
當今時代的背景
面對當前社會的變遷,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文化的創(chuàng)新,繼承傳統(tǒng)文化,提升文化自信,是我們國家提升軟實力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經(jīng)濟的發(fā)展離不開和諧、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也需要深厚的歷史底蘊與傳統(tǒng)傳承。很多傳統(tǒng)元素被運用到現(xiàn)代生活中,尤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而其“活化”就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本身的價值體現(xiàn),也為世界人們多角度、多方位地了解中國文化提供了一個實際而有效的平臺。
如何避免活化爭議
出于對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尊重,要合理運用活化手段。首先,在創(chuàng)作前要充分了解不同時代的物質文化,根據(jù)文化的實際情況具體分析,如在設計前我們要考慮四個方面:區(qū)域、民族、國家、時代以及它們之間的不同,同時還要考慮到文化的排他性。其次,在創(chuàng)作中充分尊重受眾才會贏得市場,要考慮作品的普適性和大眾性。最后,在創(chuàng)作后針對同時期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和文化產(chǎn)品要具備不同的適應性,例如在歐洲文化當中,歐洲女性用中國的仕女紋飾表現(xiàn)當時的審美狀態(tài)。而在中國,其本身就符合歷史和國人的審美狀態(tài),實現(xiàn)了社會文化體系的適應性發(fā)展。
綜上所述,歷史文脈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中國價值的核心。通過對傳統(tǒng)仕女紋樣的了解研究,提出了非遺文化的“活化”傳播,需要將中國的傳統(tǒng)藝術與現(xiàn)代技術進行結合并繼承發(fā)展,同時注意避免活化爭議,實現(xiàn)必要的社會適應性發(fā)展,傳達出中國哲學“和而不同”的中和之美、以人為本的人性化之美、自然和諧之美以及對于整體意境的重視與把控。
建立由內而外的文化自信,在有文化自覺的前提下,我們也不應該對一些藝術創(chuàng)作過于敏感,過度的敏感反而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xiàn),比如稍有異動就去批判和否定。我們不僅要重視發(fā)揚傳統(tǒng)文化,更要警惕借“傳統(tǒng)”話題擾亂國內輿論的行為,避免在沒有充分了解傳統(tǒng)文化和設計動機的前提下展開爭論,從而陷入話語的陷阱。我們要做到尊重審美的多元化,提倡文化自信,不斷發(fā)揚和傳承非遺文化,因此,我們還有很長的文化發(fā)展之路要走。
參考文獻
[1]夏征農(nóng),陳至立.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2]楊冬,徐澤.從明清文人仕女畫看“才子”的“佳人”夢[J].臺州學院學報,2005(02):17-19+27.
[3][6][7][9][11][12]徐麗慧.中國傳統(tǒng)仕女藝術[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
[4]呂建昌.含蓄逸雅和浮華媚艷——中國仕女畫與日本美人畫散論[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01):53-59.
[5]沈輝凌.淺析釉上彩仕女圖的藝術特色[J].景德鎮(zhèn)陶瓷,2014(01):92-93.
[8]張小萍.從陶瓷仕女圖紋看古代女性文化[J].中國陶瓷,2006(02):64-65+68.
[10]賈瑤.從古代女性面部妝容看中西方審美文化的差異[J].青年文學家,2020(06):170-171.
[13]馬未都.馬未都談瓷之紋 天時人事日相催——人物紋(下)[J].紫禁城,2012(06):66-91.
【作者簡介】李晶津(1996—),女,碩士在讀,研究方向:藝術設計、視覺傳達。
【通訊作者】王志強(1970—),男,碩士,教授,研究方向:藝術設計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