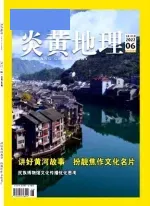論屯田制對湘西苗疆“國家化”的影響
清朝相繼于黔東南苗疆、大小金川等地施行屯田制度,是一體化治邊理念的重要實踐。乾隆嘉慶年間,國家力量進入湘西苗疆,地方治理由前代的羈縻治理一躍變為中央王朝直接管理,初步完成“國家化”進程,“國家化”對穩定地方及中華民族“一體多元”格局的形成,都有較大作用。
屯田制作為一種軍事生產活動,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裘錫圭、于省吾等學者對屯田制的古文考釋,深刻揭示了屯田制度的本質特征。隨著中國版圖的擴大,屯田制的實行愈發廣泛。西漢以來,趙充國等人創行移民屯邊,為后世邊疆治理提供了一種新思路。明朝時期,衛所制度與屯田制緊密相依,全國各地都有軍隊大規模移民墾殖活動,湘西苗疆也不例外,但規模僅限于衛所體系內部。清乾隆末年,隨著地方政治格局開始發生轉變,屯田制在各廳縣廣泛實行,給這一地區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對于這場地方制度的評價,凌純聲、芮逸夫、石啟貴等民國學者持有否定觀點,這當然也迎合了當時“革屯”運動浪潮的現實呼聲。新中國成立以后,姚金泉等學者就認為:“傅鼐在湘西苗區實行的屯田制直接阻礙了苗區經濟的發展,間接阻礙了苗區文化的進步。”持類似觀點的代表學者還有吳榮臻、石邦彥等人。與此不同的是,伍新福等人批評屯田制產生階級分化等負面作用,同時也肯定了其對社會穩定、農業經濟發展、文化交流、民族交往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學界對于清代湘西苗疆屯田制度的評價,眾皆有論,觀點各異。本文更多地將以國家權力與基層治理的互動入手,從“國家化”的視野透視,審視這場意義深遠的社會實踐。
湘西苗疆屯田
關于湘西苗疆的范圍定義論述眾多,最早可追溯至明朝侯加地、劉應中等人的文章中。他們從寬泛的地理限制上定義,并不是細化到州縣,所以不夠清晰。清中后期,湘西苗疆均屯執行以后,出現了兩種對湘西苗疆的官方定義,第一種是以清朝無名氏所編篡的《苗疆屯防實錄》曾將這個范圍界定為鳳乾永古保四廳一縣,第二本是但湘良編篡的《湖南苗防屯政考》則將所涉及范圍擴大到鳳乾永古保瀘麻七廳一縣。無論是五廳縣,還是七廳縣,其中都有屯田活動的實踐。筆者采用七廳一縣的說法,在此范圍內足以更好地為本文的相關論點展開闡述。“國家化”通常表現為地方社會訴求與國家力量下沉,二者之間回應、互動。湘西苗疆屯田制的施行,正是社會失序后,國家權力的深入與調適,不斷推進其“國家化”進程,直至初步完成。
屯田制出臺的原因及過程
湘西苗疆自古是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其政治面貌、經濟活動、社會形態等多與“內地”有別。乾嘉之際,湘西苗疆再次進入失序狀態,針對這次事件的起因,馬少僑、孫秋云、譚衛華等人都對乾嘉之際社會失序原因有過不少剖析。馬少僑對此總結為兩個原因:第一是由于政治上的不自由,第二是土地問題。當時,廣大窮苦的苗民同胞就曾提出了“逐客民、復故地”的口號,我們也可從中窺見土地問題的嚴重性。譚衛華更是在前人基礎上提出了七種原因論,其中將土地問題歸為地方社會失序的重要原因。土地問題的爆發大致從雍正時期開始,清廷對西南土司大面積的革去,促使原有的民苗界限被打破,因此事端多出。乾隆朝雖對此多有調控性的政策頒布,但于事無補。土地問題牽涉甚廣,特別是對于如何解決其中復雜的矛盾,清廷歷來是只求邊境寧謐,不生是非,很少直接解決。這種治邊思想深刻體現在和琳的苗疆善后章程中的“厘清苗疆田畝界址”“民地歸民,苗地歸苗”等設想,目的就是希望恢復舊時湘西苗疆的安寧。不過,由于和琳突然去世,加上湖北戰事又起,急需大量兵力,清廷為避免兩面作戰,屯田制開始成為首選。
苗疆的屯田制最早由張廣泗提出,并實踐于黔東南苗疆,后移置于大小金川。屯田制仿自漢朝舊制,乾隆就曾質疑此法是否適合貴州苗區。在實際操作中,黔東南苗疆的“九衛軍屯法”取得了較好的治理成效,一直實行至清末。除此以外,在大小金川和臺灣,清廷也首選屯田制作為地方治理的措施。由此可見,雖然朝廷在加以施行屯田制的時候,通常會經過深思熟慮,但是屯田制還是邊疆治理中的通行之策。但在局勢復雜的大小金川,屯田制取效不大。由此可見,在當時屯田制并非通行之法,朝廷在施行的時候,通常要經過深思熟慮。在朝廷討論如何處理湘西苗疆善后事宜的時候,時任湖南巡撫姜晟的幕僚嚴如熤,一位支持屯田的積極倡議者,提出了“廣設屯田以省軍費”“以農寓兵,最為經久之計”等見解,得到當時各級官員的推崇。此后,嚴如熠輔佐鳳凰廳同知傅鼐直接參與均屯事務,他在此期間還著有《屯防書》一冊,但此書今已不可見。傅鼐本人也撰寫了《屯田論》《練勇論》等多篇文章敘述他自己的屯田思想,他對屯田的思考與考量更加現實。傅鼐對屯田的思考,受到了嚴氏的啟發,但考量更加現實。可以說,傅鼐實踐于屯田的治理思路與嚴如熠的思想雖有部分差異,但幾乎一致。
土地的“國家化”
嘉慶善后措置以來,湘西苗疆共有兩次大規模均屯活動,第一次所均為民田,稱“民屯”,第二次所均則為苗地,稱“苗屯”,兩次均屯持續約十五年,這兩次均屯不僅完成了土地“國家化”的預期目標,也為后續屯田事業的發展打開了新局面。嘉慶四年(1799)五月,鳳凰廳士民請求均出田畝,養丁守碉。時任鳳凰廳同知的傅鼐提議廳內田畝按照“存三均七”的比例均屯,率先開始了湘西苗疆土地的“國家化”。嘉慶六年(1801)正月,湖南總督書麟、巡撫祖之望奏請“均田開屯”,并奉諭旨與相鄰廳縣一體籌酌辦理。自此,傅鼐力排眾議,又開始主持乾州、永綏、古丈坪、保靖、瀘溪、麻陽等六廳縣均田事宜。然而均屯的過程并不順利,乾州廳同知閻廣居就以乾州、鳳凰兩地差異較大為由,明確反對均屯。鳳凰、永綏、麻陽等廳縣人民和生員都以抗阻、煽惑、退田等不同方式反對均屯,然而官民很快統一了認識,甚至川楚邊民都主動支持國家均屯,主動獻出自己在湘西苗疆所置辦的田畝。
嘉慶十年(1805),“民屯”基本完成。七廳縣共均出民田六萬余畝,朝廷對屯弁、屯丁、練勇、苗兵均嚴以管理,以及對屯資貯谷等事作了詳盡的安排。同年,永綏直隸廳發生石宗四和石貴銀事件,第二次均屯因此開始,由于所均土地為苗人田地,故又史稱“苗屯”。均屯活動直至嘉慶十二年(1807)才大致完成,隨后陸有田地清丈均出,截至嘉慶十九年(1814),共均出十五萬二千余畝。這對于土地的均與屯,是一次土地“國家化”的嘗試,其既不同于漢魏唐時期的移民戍守活動,也與明朝時期的軍隊墾殖截然不同,通過歸公已開墾土地,最終取得了苗漢土等各族群的共識。清廷根據不同州縣苗疆的“內外”差異,均田程度也各有不同,如瀘溪、麻陽自明朝以來即通行保甲制度,所以均田相對較少,約為“均三存七”。而鳳乾永三廳系苗疆腹地,均田則較多,從“存三均七”到“寸土歸公”不等。土地集中在國家的手中,從根本上解決了苗民因土地引起的紛爭問題。在實際執行屯田制度時,朝廷實行授田與民,又允許所授屯田在一家一戶之內襲替,一定程度上又默認屯田的出讓,既滿足了苗民對土地的要求,又通融了屯田制度下苗民對土地財產權利的訴求。土地的“國家化”是屯田制施行的前提,這一套制度的運行與發展,給湘西苗疆帶來了發展契機,其歷史意義不言而喻。
屯田制的影響
屯田與區域建制“國家化”
湘西苗疆均屯的完成是奠定清中后期湘西苗疆政治格局的關鍵事件。鳳凰廳同知傅鼐主導的這一套以“屯防練勇”為核心的改革中,屯田制的施行原因就是為了解決土地問題。伴隨著這一制度的運行,湘西苗疆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司法和社會福利等多個社會制度層面,逐漸落實與內地建制一體化,在嘉慶年間初步完成了“國家化”進程。
在國家的統一主導下,湘西苗疆有屯各廳縣的屯務展開順利,田畝的清丈統計與田產的收取支用逐步走向規范化。除國家對屯租的補助外,地方所收齊的屯租,無需上繳中央,得以留用地方,并開創了清朝地方財政自留自用的先例。屯租提供了屯官與苗弁所需的帑費,各廳縣的書院、義學所需的“束脩膏火”均來自朝廷撥田的屯租。嘉慶十四年(1809),湖南布政使朱紹下令在鳳乾永三廳設立育嬰堂和養濟院時,也撥田以供經費。這些措施都體現了“取之于苗,用之于苗”的原則,是初步實現湘西苗疆“國家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制度的進入與流變,意味著湘西苗疆區域性整體的社會發展進步。
屯田與邊疆民族關系
湘西苗疆地處內陸邊疆,族群眾多,清時期就有苗、土、民、客、章等多個族群聚居于此。康雍兩朝,隨著五、筸、永、保土司的裁革,民族交往日益密切,民苗雜處漸成常態。直至乾隆年間,漢人巧買豪購,占據了大量苗民土地,民族矛盾日益復雜,民族關系逐漸緊張。和琳、畢沅、鄂輝等都考慮過如何處理此事,他們主要解決辦法是厘清民苗界址,再解決客民生計問題,但這些設想中所提出的“隙地”在湘西苗疆難以尋覓,“安插之法”的執行難度較高,這些難以執行的善后措施不得不因此很快被擱置下來。
隨著鳳凰廳興辦屯田事宜收效良好,湖南自督撫提鎮以降的地方官員力排眾議,陳述中央,大力倡行均屯的好處,最終得以說服中樞。屯田制的推行最終遍及三省,所涉及廳縣范圍幾乎含括了湘西苗疆全域。在這個地理范圍內,幾乎包括了所有當地的族群。屯田制極大地減少了苗地流失的可能性。通過對苗疆田地的再分配,實現“民苗皆有田”,最終達到“民苗為二以相安”。屯田制極大緩解了苗族與其他族群之間的關系,在挽救邊疆民族危機、重塑邊疆民族關系、促進邊疆民族團結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屯田與“一體多元”
中華民族的“一體多元”最早由人類學家費孝通所提出,凝練概括了大一統中央王朝體系下多元社會的歷史發展面貌。這種思想在清朝表現尤為突出,清廷在新疆、黔東南苗疆、大小金川、臺灣、湘西苗疆等處都開展一定規模的屯田活動。
這些屯田事業鑒往得失,滌濯糟粕,不同于全國通行政治制度,與整體的中央王朝統一制度安排并不沖突,而是對地方社會失序后的一種重構與調適。清廷以“一體”建制為治理考量,加以結合區域的特殊性,融通地推行屯田制,體現了一貫以來治邊理念中的“多元”。“一體”是維護國家邊疆穩定的重要基石,而“多元”是國家尊重區域差異、維系地方和平的重要保障。“一體”的存在是“多元”發展的前提,“多元”的發展則更好地維護了“一體”理念的貫徹落實。
以湘西苗疆屯田制度為代表的“多元”的良性運行,取代了舊有的軍事征服活動,從制度建設的層面上使得國家的“一體”建制得以長治久存,地方社會從原有的失序混亂回歸安定和平。清廷實行的屯田制更好地維護了“大一統”的歷史王朝,為之后乃至當今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貢獻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
屯田制起源于商周時期,歷朝歷代均有設立發展。清朝以來,清廷為維護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和平穩定,融變古制,加以推行屯田制。湘西苗疆屯田制起于地方失序,國家力量進入,得以重塑社會秩序。屯田制度的施行首先經過各級政府官員的談論與商議,后凝結共識,得到朝野的支持。均屯先在鳳凰一廳實行,最終再綜合考慮推行至七廳縣,呈現了一個穩步進展的態勢。通過執行均屯法,土地得以實現“國家化”,從根源上緩解了社會再次失序的可能性;其次,國家對苗民的土地分配較為公平,在執行中變通性較高,充分照顧了苗族民眾的感情,最終給地方帶來了長久的和平安寧。屯田制施行的同時,給地方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清廷從政治、軍事、經濟到文化方面展開了一系列的“國家化”措施,促進了湘西苗疆在建制上與國家總體安排的一致性,加速了湘西苗疆“國家化”進程,并最終得以初步完成。屯田制的良好運行,極大地推動了民族交往與民族交流,促進民族團結與民族融合。屯田制度作為少數民族地區一種特殊的政治制度安排,體現了中國幾千年以來“一體多元”的歷史事實,鞏固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基礎,維護了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嘉慶年間興起的屯田制,汲取了傳統古典教義中“兵農合一”的思想理念,又結合了苗疆的特殊性,加以變通融合,給湘西苗疆帶來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穩定,對湘西苗疆的社會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佚名.苗疆屯防實錄[M].伍新福,校.長沙:岳麓書社,2012.
[2]伍新福.試論清代“屯政”對湘西苗族社會發展的影響[J].民族研究,1983(03):32-40.
[3]伍新福.清代湘西苗族地區“屯政”紀略[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02):78-81.
[4]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兼論“侯”“甸”“男”“衛”等幾種諸侯的起源[J].文史,1983(19):95-98.
[5]于省吾.略論述西周金文中的“六”和“八”及其屯田制[J].文史,1964(03):152-155.
[6]姚金泉.試析傅算在湘西苗區的屯田[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06):55.
[7]馬少僑.清代苗民起義[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6.
[8]徐珂.清稗類鈔[M].北京:商務印書館,1917.
[9]譚衛華.清中后期湘西苗疆社會秩序的調適于重構[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
[10]嚴如熠.嚴如熠集[M].長沙:岳麓書社,2013.
[11]蔣琦溥.光緒乾州廳志[M].刻本.林書勛,修.張先達,撰.林書勛,續修.乾州:[出版者不詳],1877(清光緒三年).
[12]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M].刻本.[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883(清光緒九年).
[13]張映漢,李堯棟,翁元圻,等.嘉慶湖南通志[M].刻本.[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820(嘉慶二十五年).
【基金項目】湖南省民族學研究基地開放基金項目“論屯田制對湘西苗疆國家化的影響”(項目編號:21JDZB026)。
【作者簡介】田晨鈺(1997—),男,碩士,研究方向:專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