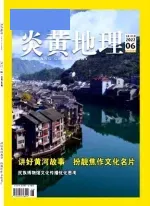傳統婚禮的恢復性舉辦與非遺建設的“協同創新”
張旭 左振廷
婚禮儀式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是當下非遺工程的“搶救”對象。以貴州某村寨舉辦的恢復性傳統婚禮為研究個案,討論其背后的社會意義。同時,認為這種恢復性婚禮是各方合作的開放性成果,包含一種“氣力”,即德勒茲式“質的綿延”。
一場西部方言:“白苗”的恢復性婚禮
紫云縣少數民族文化資源豐富,西部苗族婚俗獨具特色。近年來由于年輕人大批外出務工,傳統文化傳承嚴重衰退,包括婚禮儀式在內的一些文化習俗正在消亡。為此當地政府有意識地安排了一次恢復性的婚禮,以求回歸傳統,傳諸后代。2009年對該縣的一個“白苗”村寨婚禮的恢復性舉辦做了重點調查,對其中個案做了詳細調研。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縣位于貴州省西南部,隸屬于貴州省安順市,縣境東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長順、羅甸兩縣,南抵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望謨縣,西界鎮寧縣,北靠安順市。此次調研的自然寨隸屬紫云縣水塘鎮二關村(行政村),位于紫云自治縣水塘鎮東北方,屬“麻山”貧困地區,是一個以苗族為主體的寨子(自然寨,行政上稱“組”)。根據我們統計的數字,寨子里有61戶人家,300多人,除了5戶姓方的家庭是漢族外,其余均為苗族。他們以苗語Hmong Dawb(漢字音譯“蒙逗”)自稱,用當地的漢語方言稱之為“白苗”或“白族”。當地婦女的民族傳統服飾是頭包黑長帕,穿右衽衣,衣袖、領、前胸后背等鑲有繡片(挑花);下裝是白色麻布百褶裙,系長腰帶,前后系圍裙,裹綁腿。
該個案中的新娘和新郎是自由戀愛,雙方是同鄉,都在外地打工,相識相愛已有3年,雙方家長也都同意舉辦婚禮。舉辦恢復性婚禮是新娘家的意思,但是新郎的父母都已去世,只有新郎的哥哥出面,而且新郎家經濟條件一般,因此婚禮費用大部分由新娘家籌集。現在這一帶年輕人結婚不再舉行過程復雜的傳統婚禮儀式,大部分都簡化或省略部分婚禮流程。在新娘家的這個寨子里,除了少數幾位寨老詳細掌握傳統婚禮的知識以外,大部分中年人對此不過略知一二,年輕人則完全不了解。這次婚禮的各種安排要仰仗寨老的指導。整個婚禮需要三天(第一天主要為接待)才能完成。
婚禮于2009年12月19日和20日舉行。以下為儀式展演的大致過程。
12月19日—12月20日凌晨。婚禮全部在新娘家舉行。按照傳統,新郎和新娘各自的叔叔、舅舅擔任媒人。在這次婚禮上,充當女方媒人的是新娘的兩位舅舅,而男方的兩位媒人則是從小貓場村邀請的兩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媒人除了演唱儀式歌曲,帶領結親、送親的隊伍,也負責其他相關的儀式細節。男方需要組織一支接親隊伍,主要是兩位媒人和一些青壯勞力,共十幾人左右,他們要在送新娘的前一天帶著禮品、禮金、傘和豬腿趕到女方家。
雙方敲定婚事的各種事宜后,需要協商聘禮的數量,男方會提交部分聘禮,剩下的部分在男方接親隊伍到達當天結清,也被稱為“割尾巴”。
“割尾巴”的過程并不復雜。雙方四位媒人首先對飲一輪“雙杯酒”(每人連續喝兩碗),男方的媒人便將“尾巴”即余下的聘禮和聘金交放于桌上,女方當場清點禮品。首先是一些做苗衣所用的料子布和麻布,擺放到桌上之后由女方的兩位婦女當場查驗清點,然后男方的媒人將剩余的禮錢擺放于桌上(分別裝于兩個紅包之中)。把酒碗斟滿,四位媒人對飲一碗,男方的媒人便開始唱歌。歌畢,再飲一碗酒,女方媒人便打開紅包清點禮金,確認無誤,女方兩位媒人對飲一碗,然后將禮金交予新娘的父母,之后新娘的父親飲“雙杯酒”,雙方媒人再對飲一次“雙杯酒”。到此,割尾巴的儀式便基本結束。按照傳統,每次飲酒都應該是雙杯,但由于男方媒人的年紀都比較大,所以喝的時候就只喝一碗。
之后的“搶新娘”是婚禮的重要環節,也是“保留節目”,他們將這個儀式的時間改為送新娘的當天下午。按照傳統規矩,女方送親的親友離開時,男方家人和新郎新娘都要一直送到門外,在道別時,新娘的舅舅會將新娘拉住,假裝把新娘搶走,不讓她回新郎家。這時新郎就要唱歌,并且給紅包,把新娘要回,然后新娘要假裝哭,舅舅再把新娘搶回,如此進行三次之后,新娘哭著同娘家親友告別。整個婚禮儀式就算全部結束了。
在整個婚禮過程中,當地專業機構都派人專門拍攝和記錄,當場景與他們的記錄發生沖突時,他們會要求重新拍攝,以滿足記錄的需要。如在20日新娘出閣的時候,按照原來的程序新娘出閣與媒人在堂屋中對歌是同時進行的,由于專業攝影師們事先不知道有對歌的環節,只帶了一部攝影機,捕捉完新娘出門的鏡頭之后,又發現這里另有儀式,就提議重新開始,用攝像機記錄下來。
恢復傳統與“協同創新”
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并于2003年頒布《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來,相關的學術研究和公共宣傳在我國便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中國政府的態度十分積極,社會各界也反響熱烈。
非遺保護是國家工程,在政府眼中是一個新的凝聚人心的平臺,政府想要打造“文化軟實力”,就需要建設“精神文明”,需要讓國民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對未來有憧憬。近年來,我國開始大力推進“建設共有精神家園”,提倡回歸傳統,重塑道德。當然,無論非遺保護工程如何實行,如果沒有來自基層的支持,沒有民眾的廣泛參與,它就難以生根開花,落地成真。由地方政府推動的非遺保護無疑也為當地民眾提供了滿足自身文化需求的良好機會,盡管各群體、各階層甚至每個人的需求不同,但他們中有不少人會在這個國家工程中找到自己的傳統記憶,找準自己的位置。當地村民舉行傳統婚禮,不僅是為了滿足“明媒正娶”的需要,以符合傳統規矩,也是為了響應政府工作,促進非遺保護與傳承。民族學、人類學以及其他有關專業的老師和同學來這里做田野調查,可能是出于撰寫畢業論文,做好學術研究的需要,但在研究過程中也將傳統的婚禮儀式記錄和保存下來。這場旨在恢復傳統習俗的運動,不管是否能夠“夢想成真”,終究是各界人士、政府官員和地方民眾“協同創新”之舉,最終實現了各方所需和所求。
從官員到專家,從學者到村民,對非遺有不同的態度,其中有褒有貶,也有模棱兩可、疑惑不解的。2015年11月23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一篇署名“文木”的文章《別讓“文化遺產”變成“文化遺憾”》,反映了人們對非遺保護的復雜態度。如中國傳統村落保護發展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曹昌智直言:“歷史風貌已經破壞殆盡。都破壞成這樣了,還申什么遺?!”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指出,農村正在“空心化”,一個層面是有形的,村民外出打工,村莊無人居住;另一個層面是無形的,一些傳統村落原有的特質文化已經消失,造成“文化空心”,不少“文化遺產”正在變成“文化遺憾”。
“非遺”保護是人類學的理念,也是人類學的實踐。人類學自從告別了殖民主義,就積極加入反種族主義運動當中,同時也不斷自我反思,尤其在《寫文化》[1]一書出版之后,人類學學者大多開始同情、聲援和扶助弱者,他們關注文化生產的過程,關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關系[2]。“互為主體,共同參與”是非遺保護的人類學口號。從上述紫云縣的個案可以看出,非遺保護在落地的時候,存在大量隨機多變的情況。原本將要衰落的婚禮習俗,因為有政府非遺工程的推動而得到部分復興。
女方的媒人是新娘的兩位舅舅,而男方的兩位媒人則是外村請來的兩位老者;新郎的父母雙亡,就找來哥哥代替;男方接親人同女方的兩位媒人一同落座后,按規矩由女方的媒人唱歌,敬葉子煙,但由于兩位媒人都不會唱歌,所以請會唱儀式歌曲的長者代替;文化局派來拍攝的人錯過了儀式,就重新舉行……這是對傳統的創新性恢復,是多主體互動的“新產品”。多方參與的“非遺工程”,已經成為“萬眾創新”的新財富和新資源。
“氣力”與“質的綿延”
婚禮作為儀式具有象征性和實用性的雙重意義。從法國猶太裔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涂爾干的立場出發,儀式具有強化集體情感和整合社會的功能,也有形成集體表征或者促使集體轉型的作用。英國語言學家、哲學家利奇認為儀式表現了人類行為的象征性,它可以是一個連續體,一端是象征,另一端是實用;布洛克批評某些儀式象征分析忽視了背后的權威表達;巴特也認為儀式知識和成丁禮崇拜表達了尊老愛幼的社會風俗。從最近的研究可以看出,即便在同一個群體內部,人們在儀式中表現出來的態度、感情和信仰都會有所不同,表面形式不能遮蔽內部差異[3]。人類學的實踐理論更加強調儀式活動的異質性,在具體場景下,參與者對于儀式的解釋各不相同[4]。隨著市場化、信息化、城鎮化程度的加深,人群內部利益分化嚴重,態度、感情和信仰也變得更加復雜多樣,代溝也比過去大。在全球化和數字化的背景下,無論是傳統婚禮還是現代婚禮,都逐漸成為人們各取所需甚至利益博弈的場合。其實婚禮本身是一個開放的過程,是各種力量發揮作用,創造和創新意義的過程,所以我們更愿意稱之為“協同創新”運動。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政府、非政府組織、志愿者、學者、當地民眾,還有開發商,都會加入非遺保護的“協同創新”工程,實現各方所求,達成各方所望。
德勒茲引用伯格森關于運動的論述:運動總是出現在兩個瞬間的空隙中,屬于“質的綿延”,而綿延就是變化,即運動是質的變化;同時,對于瞬間的靜態切分(抽象時間)會失去運動[5]。運動就是變化,質的運動或質的綿延就是質的變化。德勒茲也引用皮爾士指導理論闡述同樣論點:所有僅僅以對立、決斗方式存在的東西都屬于第二性:努力—反抗、動作—反應、刺激—回應、情景—行為、個體—環境……“第二性的第一種形態,就是質—力量變成‘力。”[6]質屬于第一性,是一種感官沖擊,這種沖擊可以來自視覺、味覺、嗅覺,也可以來自觸覺和聽覺,從心理反映上看,這些初級感覺尚未來得及指向他物,只屬于它們自己,是“征象”(sign);但它們馬上會指向他物,進入質—物相關的第二性,接著又轉入第三性,指向象征。質從一開始就充滿動能,要指向他物。亞里士多德把語言的起源歸因于“靈魂激情”,即激烈的質感讓靈魂發聲[7]。伯格森和皮爾士關于“質的綿延”和“氣力”的觀點,有利于我們深入分析紫云縣傳統婚禮的恢復性舉辦。我們的經歷豐富多彩,質感物覺也變化莫測,對于“結構”“時段”的把握只能靠切割和懸置的辦法。這種“結構”和“時段”屬于觸摸不到的“直覺”,要靠我們的身體或者其他物體作參照物[8]。我們每個人身上或心理都帶有某種共性,會在實踐中感同身受,發生共鳴,因此彼此總能夠大致掌握這樣一種“結構”和“時段”。在地方民眾那里,這種“結構”和“時段”就是祖宗傳下來的那些東西,就是“這個理兒”“不這么做怎么做”。
在類似于紫云縣那場婚禮的儀式中,不同的人帶著不同的經歷和記憶,帶著不同的期待和目的來到現場,與不同的個體進行互動,以各自的方式產生“質的綿延”,這種“質的綿延”是一個開放的過程,伴隨著皮爾士指號活動:“質感”(如顏色、氣味、聲音)指向物感,物感指向他物(如新郎—新娘、飲酒—唱歌),他物指向象征(婚禮文化)。
這場“白苗”舉辦的恢復性婚禮是非遺“協同創新”工程的縮影,不存在“原汁原味”,只存在臨場發揮,不存在“靜止”,只存在“靈活”。孔夫子早就提到“禮崩樂壞”,但正是在這樣的“禮崩樂壞”“禮行樂奏”當中,規矩已被傳承下來,習慣與傳統在“氣力”的推動下延續。不同的人群以自己的方式存活下來,雖然“克己復禮”者大有人在,但是“克”和“復”每次都發生在創新和臨場之間。
參考文獻
[1]James Clifford,George E.Marcu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2]納日碧力戈,胡展耀.“非遺”中的互為主體與人類學的社會擔當[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43(06):24-29.
[3]Charlotte,Seymour-Smith.Macmillan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M].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1986.
[4]Alan Barnard,Jonathan Spencer.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0.
[5]吉爾·德勒茲.電影I:運動-影像[M].謝強,馬月,譯.湖南:湖南美術出版社,2016.
[6]納日碧力戈.從皮爾士三性到形氣神三元:指號過程管窺[J].西北民族研究,2012(01):40-50.
[7]苗力田.亞里士多德全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
[8]George Lakoff,Mark Johnse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基金項目】2018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認知人類學視域下西南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研究”?(18XMZ048)。
【作者簡介】張? ?旭(1984—),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南方民族歷史、文化遺產;左振廷(1985—),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學、文化人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