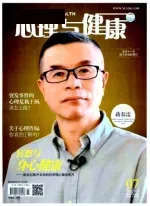怎么做才能不拖延?不如問問那個打游戲從不拖延的自己
黃彬彬

相信大家都在年初設立了不少flag(目標),請問:新的一年已經過去大半,你開始完成你的flag了嗎?
比flag仍然“亭亭玉立”更扎心的是,當小伙伴喊我玩游戲,我竟然毫不遲疑地點開了游戲……我不得不開始三省吾身:為什么學習我拖延?為什么工作我拖延?為什么打游戲我就不拖延?
揭露拖延本質的新研究
浙江大學的張順民博士分析了人們的拖延行為,認為拖延的機制包含兩個維度。
一是對于當前任務的厭惡程度。我們之所以選擇逃避,通常是因為不喜歡這個任務,而且越不喜歡,就越可能拖延。你很可能拖延寫作業、寫代碼、寫方案,但打游戲、領紅包或者回復喜歡的人消息時可不見你拖延。
二是任務帶來的收益多少。我們愿意立即去做某個任務,通常因為想要通過完成這個任務獲得獎賞,或者避免無法完成任務而受到懲罰。就算一個項目的難度很高,但完成它就能領到高額提成,或者完成不了就會被炒魷魚,那你很可能還是會去做的。
但任務就在那兒,你變著法兒地“躺平、擺爛、裝死”,最后也得做。你會拖延到什么時候才開始行動呢?研究者提出了一個時間點:當你認為完成任務獲得的收益(或是完成不了而遭受的懲罰)超過了你對任務的厭惡程度時。
任務一直是那個討厭的任務,不會隨著deadline(最后期限)逼近而變得可愛;但人們預期的任務收益卻不是一成不變的:相比于未來,我們更看重短時間內就能獲得的收益,這種機制叫作“延遲折扣”。比如在明天立即拿到1000元獎金和一個月后拿到1000元獎金,我們當然會選擇前者。
這一點延伸到令人拖延的負面任務也是成立的:如果周五要交一篇論文,周一的你或許并不會感受到不交論文的后果有多嚴重,還可以東搞西搞作天作地;但到了周四,錯過“死線”的悲慘后果近在眼前,完成這個任務就顯得無比重要,你不得不黑著眼眶熬著夜內心哭泣著把論文寫完。正如卡爾加里大學哈斯凱恩商學院教授皮爾斯·斯蒂爾(Piers Steel)所認為的,人們最容易在那些目前令人討厭、回報遙不可及的事情上拖延。
基于這樣的分析,張順民博士給“拖延”下了一個新定義:自愿且不理性地推遲任務。在此之前,拖延常被認為是一種情緒問題,拖延者覺得自己目前的情緒不適合完成任務,而且拖延之后的情緒就會變好。然而,選擇拖延并不完全是因為討厭任務,畢竟完成任務通常會帶來收益。拖延可能是因為有充裕的時間,時間讓預期收益大打折扣;而拖延到最后終于開始去做,則是因為獎勵或懲罰的不斷臨近讓它看起來更加“誘人”,也就制造了“Deadline是第一生產力”的常態。
斯金納的經典實驗
知道了拖延的本質,那怎么解決自己的拖延呢?這里提供一個新思路:不妨問問那個打游戲從不拖延的自己。
心理學家斯金納曾用小白鼠做過一個著名的實驗:他先在箱子里裝了食物,老鼠按一下裝置,就能吃到從箱子里掉下來的食物;后來斯金納不再給食物,老鼠怎么按都沒有收獲;再后來,斯金納嘗試偶爾給食物,偶爾不給。實驗結果發現,不固定給食物的方式更容易讓老鼠上癮,因為在這種條件下,老鼠只有不停地按裝置,才能增加得到食物的概率。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這樣的。如果游戲很簡單,你一打就過關,你可能就不會玩了;一直打不過關的游戲也會讓你氣得卸載;而那些部分關卡簡單,部分關卡需要你練習才有可能過關的游戲,你才會不拖延去玩。
面對一個棘手的任務也是如此。我們總會先想到那些令人厭惡的部分,就像知道怎么按壓也不會得到食物的老鼠,躺平睡大覺的拖延順理成章成了當前獲益的最佳方式。是因為我們的想象力太差,看不到任務完成帶來的價值及成就感嗎?未必。這往往是因為任務本身復雜,截止時間又晚,哪怕完成任務,眼前也得不到什么獎賞—— 這樣的任務看起來就像一個難以通關的游戲,讓人想直接卸載,擱置幾天再說。
試試游戲闖關法
這種時候,把一個“大游戲”細分成諸多可能過關、能夠摘到金幣的小關卡,是一種可行的應對方法。你可以嘗試將任務進行分解,并給每個分任務定制截止時間。這樣一來,大的任務成了許多個小目標,完成每個小目標都會獲得收益。將完成學習或工作任務設計成闖關游戲的形式,讓任務的進度條得到推進。
我們可以先列出一些放松開心的活動,寫在小卡片上,完成任務之后就可以抽取其中一項獎勵自己,讓我們帶著對未知獎勵的期待去完成任務。任何我們感覺到輕松愉悅的活動都可以是獎勵,可以把自己最想吃的零食、最想買的東西寫下來,每張卡片寫一種獎勵;接著把任務拆分成多個階段,每天根據自己的能力設定一些小目標;每當自己完成一個小目標,就從卡片里隨機抽取一種獎勵;如果目標沒有完成,就不可以給自己獎勵,甚至要給自己一些懲罰。
像這樣不確定的即時反饋方式,能夠提升任務的潛在意義及完成任務能帶來的愉悅感,讓我們帶著期待去完成flag,就像玩闖關游戲一樣有趣。
持續的心理暗示也是重要的輔助過程。雖然相比于未來的收益,我們總是更容易看到眼前對任務的厭惡,但如果多提醒自己未來將會獲得的巨大價值,會讓我們更重視任務,更愿意喚醒自己的力量執行任務。因此,請不斷提醒自己完成任務的好處,越細致越好。
如果你嘗試解決、卻無法喚醒自身的力量去應對拖延,也可以向身邊執行力強的朋友或者專業心理咨詢師求助,一起探索和解決你的拖延問題。傳統的認知行為療法(CBT: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通過直接改變不良的認知和行為,可以對拖延起到較好的改善作用。近年的研究又找到了另一種更加有效的方式:接納承諾療法(ACT: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通過原諒、接納和理解自己的不良情緒,踏出緩解拖延的第一步。
大多數拖延的人想必對愛因斯坦的“時間是幻象”深表贊同,但時間一直在流逝,最后期限總會臨近。過去拖延,無法決定你未來是否拖延。與其選擇在拖延里不安,不如試著把艱難的學習和工作當成一場游戲吧!
參考文獻
Geng, J., Han, L., Gao, F., Jou, M., & Huang, C. C. (2018). Internet addiction and procrastination among Chinese young adul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84, 320-333.
Zhang, S., & Feng, T. (2019). Modeling procrastination: asymmetric decisions to act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9,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