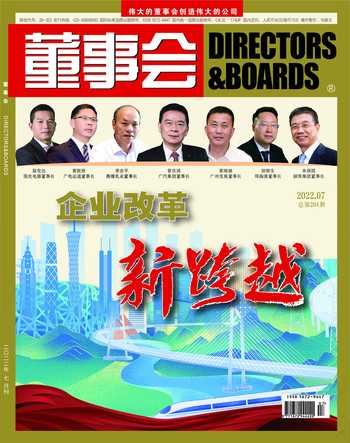微評
“閑置”募資改道他用挑戰公司治理
2020年6月,澤達易盛成功登陸科創板,募得4.05億元,募資凈額3.4億元,擬用于新一代醫藥智能工廠平臺升級、研發中心等4個項目。2021年7月,澤達易盛董事會通過議案,同意使用不超過1億元(含本數)的閑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公司流動資金。2022年7月5日晚間,澤達易盛披露無法按期歸還閑置募集資金。
【微評】
像澤達易盛這樣處置閑置募集資金的情形在市場上并不少見,甚至見怪不怪。募集資金何以被“閑置”?募集資金未來是否會出現“閑置”風險和浪費,早就應當在規劃考慮之中,也就是說在募集資金之初,就應當考慮到避免“資金閑置”的發生。但現實中,無論是發行人還是券商,基本上是以“能募盡募”作為募集目標的,而沒有充分考慮到資金閑置的風險。
閑置募集資金可否被改變用途?從理論上講,凡改變閑置募集資金用途的做法,都有悖于投資者的投資目標,也與招股說明書、募集資金項目文件等法律文件上的資金使用承諾背道而馳。而資金閑置本身也會造成發行人資金成本增加、資金風險加大等問題。因此,安全、有效利用閑置資金,保持資金的保值增值符合投資者以及上市公司的基本利益。事實上,現行的規則系統并未完全禁止發行人變相改變“閑置”募集資金使用計劃的可能。一方面在實體上,要求利用閑置資金的目的在于“保值”,利用期限多為“臨時”,而使用目標則宜為低風險產品;另一方面在程序上,則要求經過董事會會議、甚至臨時股東大會會議投票表決方能實施。似乎如此行事,一切縝密周詳,滴水不漏。但實際上,在董事會中心主義的現實背景下,董事會就有很大的機會改變“閑置”募集資金的使用用途。
閑置募集資金的利用要考慮資金結構。根據公開信息可以推算:2020年6月,澤達易盛募資凈額3.4億元;截至去年末,募集資金累計使用金額7337.95萬元,僅占募集資金凈額的21.58%;結余金額1.37億元,占40.29%;使用閑置募集資金購買的尚未到期的銀行理財產品3700萬元,占8.72%;以及不能歸還的補充流動資金1億元,占29.41%。從上述符合募集資金用途的資金利用僅占21.58%來看,該上市公司募集資金出現“閑置”的情形,其原因是結構性的;即使去除資金使用期限錯配等因素,也無法避免募集資金“閑置”的出現,顯然這不是資本市場期望實現的社會資金合理配置,反而有聚集投資風險的可能。那么,是不是可以結合發行人募集資金使用效率和閑置資金情況,制定更為合理科學的閑置資金利用規則,尤其是結合發行人資金利用結構對其進行有效規制,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顯然,這是一個監管部門和上市公司內部治理中都需要關注并著手調整的問題。
還有一點,是“補流”資金無法歸還的悖論。澤達易盛2021年7月通過董事會決議將1億元資金用于“補流”。現在“公司目前運營仍然存在資金壓力,具體歸還時間存在不確定性……爭取12個月內盡早歸還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募集資金。”換句話講,就是上市公司不僅用“補流”的1億元“閑置”募集資金,填了流動資金缺失的無底洞;而且無法將這筆資金按時歸還至公司募集資金銀行專戶。通過此番輪回,發行人不僅擺脫了募集資金用途的限制,更將還款義務架空到一個缺乏還款責任人的未來。
礦業服務年限超過100年?“理論推測”
2022年6月9日,深交所向興業礦業下發關注函,要求公司說明銀漫礦業探礦工作開展情況及探礦成果,詳細說明銀漫礦業服務年限“有望超過100年”的依據及計算過程,是否存在估算依據不充分、估算過程不謹慎等誤導投資者的情形。6月24日晚間,興業礦業回復深交所稱,“有望超過100年”是按照礦床學理論從找礦遠景上的理論推測,并非既成事實或基于現有備案儲量計算得出的謹慎結果,未考慮地質環境以外的其他內外部生產經營環境影響,系僅考慮礦山地質特點推測的結果;截至目前,探礦工作未有階段性成果,未來探礦工作及探礦結果仍存在不確定性。
【微評】
顯然,興業礦業的回復重點在于“服務年限有望超過100年”是“僅考慮礦山地質特點”的前提下所做的一種“理論推測”,這種“理論推測”的依據是礦床學理論;而深交所關注函所關注的是100年服務年限的估算依據是否充分,以及估算過程是否謹慎等問題,關鍵在于是否存在誤導投資者可能。
或許,100年服務年限的“理論推測”或者“理論計算”在礦床學上并無不當,也存在技術上的合理性與可能性;但在證券市場信息披露規則中,即使是白璧無瑕的科學合理的“理論推測”及其結論,也不一定具備信息披露規則所要求的真實性與準確性。簡言之,在信息披露中,不能簡單以“理論推測”代替“事實情況”,更不能利用普通投資者對特定行業技術知識的缺乏,來誤導投資者的投資判斷。而后來興業礦業所澄清的“并非既成事實或基于現有備案儲量計算得出的謹慎結果……未來探礦工作及探礦結果仍存在不確定性。”的表述才更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
不難看出,交易所所要求的信息披露,是那些更接近投資者、對投資者決策產生影響的信息的真實與準確性,而不是這些信息背后遙遠的背景知識或者理論的科學與合理性。
五大風險考問蕉下營銷模式
4月,戶外露營產品企業蕉下向港交所遞交招股書,擬登陸港股市場。據報道,2021年公司實現營業收入約24億元。但同時,蕉下通過巨額廣告投入換取流量與銷售額的營銷模式也引起人們議論。據統計,2021年蕉下的廣告及營銷開支占收入的比重為24.4%,較2019年增加了約15個百分點。
【微評】
從公司經營角度分析,尚無法律直接規定公司廣告投入的額度或者比例限制,當然公司章程一般也不可能對此進行直接的規定和限制。從本質上說,這是公司經營自主權的內容之一,只要符合公司內部經營決策的權利安排與議事規則。蕉下通過與600余名網紅(KOL)合作換取14億關注者以及45億瀏覽量,大幅提高品牌及產品的知名度,從而提升公司零售額以及營業收入的做法,本無可厚非。如此營銷行為,未違反公平競爭規則,亦未影響市場秩序。
但如此不計成本、不管收益的敢死隊般的營銷策略,蘊含諸多潛在風險:
高投入營銷模式勢必增加公司現金成本,現金流壓力相對增大,這一點從蕉下的毛利率和經營利潤率差距懸殊——“2021年毛利率為59.1%,但經營利潤率僅有6.1%”,就可以看出端倪。顯然,微薄的利潤能否支撐這樣的經營模式,這一做法的可持續性有待謹慎觀察。
所謂“關鍵意見領袖”也就是網紅的影響力因子的波動性,尤其是突發意外負面事件,帶來的影響力沖擊甚大。觀察近幾年的相關事件,當網紅明星負面事件發生時,相關企業通常會在第一時間進行業務、形象的切割,積極止損的結果就是顆粒無收。
粉絲的忠誠度與其消費力很難劃等號。這不僅與粉絲的年齡、性別、收入狀況密切相關,也與產品的更新換代情況密切相關。常常老一代產品明明銷量很好,但一旦更新迭代,人氣與銷量齊齊下滑,慘不忍睹。
過度依賴第三方電商平臺,也是這一模式潛在的風險之一。據報道,2021年蕉下的線上店鋪和電商平臺收入占比分別達到68.3%、12.6%,兩者合計貢獻了八成的收入。渠道的集中,往往也意味著風險的集中。
此外,近年來國內旅游市場的冷落,以及戶外活動管控的限制,使得未來的需求或許下降。
蕉下也意識到了這種營銷模式的風險,它在招股書中指出:“我們的成功部分取決于營銷活動,如營銷活動不能以具成本效益及高效的方式有效吸引客戶,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經營業績及前景可能會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其實,蕉下營銷模式的背后,其基礎邏輯相當清晰。其一,以時間換取收益,保持領先消費者一步,永遠在消費動力出現不足之前換擋、換方向,保持刺激;保持“營銷鏈”(沒錯,不是“資金鏈”)不掉鏈子。其二,蕉下營銷模式是典型的“消費主義”哲學的積極應用,但是這一策略會不會成功,或者會不會一直成功,則需要謹慎期待。至少,消費主義哲學所遇到的各種挑戰,蕉下也會遇到。
點評人楊為喬系西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