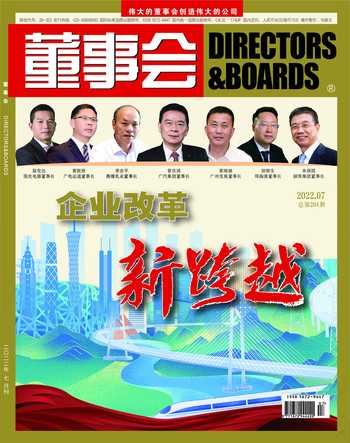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披露推動資本向善
王駿嫻

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披露制度是人類發(fā)展中的經(jīng)濟、社會、環(huán)境等宏觀議題在企業(yè)微觀主體的具體體現(xiàn),并以信息披露的方式呈現(xiàn)。從歷史的經(jīng)驗來看,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披露是從道德層面對企業(yè)個體的約束,彌補經(jīng)濟和法律在制約個體利益損害公共利益所存在的不足。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具有經(jīng)濟外部性,以描述性、預測性信息較多,同時兼具全球共性和地域特點。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的外部性需從經(jīng)濟學層面解決。建議可持續(xù)發(fā)展報告獨立于財務報告,國際可持續(xù)信息披露準則需給予各國家或地區(qū)一定的自主權。
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貫穿人類發(fā)展史
了解人類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淵源歷史,才能明晰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本質。
可持續(xù)發(fā)展并不是現(xiàn)代的產(chǎn)物,它是人類社會得以延續(xù)并發(fā)展壯大的智慧,只不過用現(xiàn)代的語言更易于當代人的理解。人類不斷地通過與外部的自然環(huán)境以及內(nèi)部的各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得以可持續(xù)發(fā)展。在農(nóng)耕文明時代,反復無常的自然迫使人們從本性上敬畏自然,使得古人善于觀察、總結自然的規(guī)律并運用在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中,《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西方的經(jīng)濟思想史中重農(nóng)學派也是將自然規(guī)律引入到經(jīng)濟思想中。在古代中國的社會關系中則強調仁義,“利者,義之和也” “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古希臘哲學重視內(nèi)省,提倡正義與美德。文藝復興運動之后,人類社會逐步進入了工業(yè)文明時代,減少了對外部自然環(huán)境的依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啟了資本主義自由經(jīng)濟,但亞當斯密在早期所撰寫的《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道德情操論》討論道德的力量,同情和仁慈限制人的私欲,構建一個公平的社會,《國富論》就是建立在這個假設之上,討論個人如何受經(jīng)濟力量的引導和制約,競爭引導自我利益的經(jīng)濟趨向社會福利。《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共同協(xié)調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但在工業(yè)革命的浪潮下,個人主義日益增長,農(nóng)業(yè)文明基礎的禮教受到挑戰(zhàn),新的道德共識伴隨著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應運而生。
由此可見,人類通過經(jīng)濟發(fā)展、道德倫理、法律制度等方式不斷促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披推動資本向善
市場經(jīng)濟無法解決的環(huán)境、氣候問題
新古典經(jīng)濟學將資本積累、人口增長、技術進步作為經(jīng)濟增長的源泉,而將環(huán)境、氣候作為外部效應和公共物品的范疇。隨著工業(yè)經(jīng)濟的不斷發(fā)展,工業(yè)生產(chǎn)引發(fā)環(huán)境污染、溫室氣體排放、資源枯竭等問題,受到廣泛爭議。
環(huán)境庫茲涅茨曲線及生態(tài)閾值。環(huán)境庫茲涅茨曲線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收入與環(huán)境狀態(tài)的關系。經(jīng)濟發(fā)展初期,隨著收入的增加,環(huán)境會惡化;經(jīng)濟發(fā)展到一定水平后,消費者收入的增加,環(huán)境會隨之改善。但這里存在一個生態(tài)閾值的問題,若資源產(chǎn)權不明晰、環(huán)境成本的外部性沒有內(nèi)部化,無法實現(xiàn)帕累托最優(yōu),則經(jīng)濟的增長會使人類社會承受較高的環(huán)境成本,超過生態(tài)不可逆閾值,將影響人類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當前全球的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就存在這樣的危機。
無法內(nèi)部化的環(huán)境、氣候外部性問題。新古典經(jīng)濟學認為環(huán)境、氣候問題可以采取外部性內(nèi)部化的方式來解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外部性問題都可以采取內(nèi)部化來解決。氣候變化外部性影響范圍廣、時間長、不確定大,局部均衡分析過于簡單化,且氣候變化很多問題不能被市場化、貨幣化,例如氣候變化引發(fā)的生態(tài)損失、公共健康影響、溫升的厚尾效應等。
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及聯(lián)合國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
人類社會的內(nèi)部還存在著諸如種族歧視、性別歧視、貧困等問題。聯(lián)合國發(fā)布的2015年至2030年全球17個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SDG)涉及經(jīng)濟、環(huán)境、社會三個方面。這17個發(fā)展目標分別是無貧窮、零饑餓、良好健康與福祉、優(yōu)質教育、性別平等、清潔飲水和衛(wèi)生設施、經(jīng)濟適用的清潔能源、體面工作和經(jīng)濟增長、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和基礎設施、減少不平等、可持續(xù)城市和社區(qū)、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chǎn)、氣候行動、水下生物、陸地生物、和平正義與強大機構、促進目標實現(xiàn)的伙伴關系。這些目標體現(xiàn)的是全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共性問題,各個國家會根據(jù)自身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制定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NSDS)。
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披露的作用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根據(jù)聯(lián)合國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制定適用于企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報告指南》,通過信息披露促使企業(yè)踐行聯(lián)合國的SDG目標。
從歷史的經(jīng)驗來看,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披露是從道德層面對企業(yè)個體的約束,彌補經(jīng)濟和法律在制約個體利益損害公共利益所存在的不足,如同《道德情操論》引導企業(yè)個體利益趨向社會福利,推動企業(yè)向善和資本向善。
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披露的多重特質
具有經(jīng)濟外部性
從經(jīng)濟學的角度來說,大部分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具有外部性,無法被內(nèi)部化。傳統(tǒng)財務信息屬于可以被內(nèi)部化、貨幣化的信息,從而用于資產(chǎn)定價。被內(nèi)部化的信息例如碳稅或碳排放權交易,已有較明確的會計處理規(guī)范。由于經(jīng)濟外部性,使得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難以通過會計處理和金融體系,對企業(yè)的賬面價值或資產(chǎn)價格產(chǎn)生實質性的影響。在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和金融框架下,企業(yè)披露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無法直接促進盈利,會導致其缺乏內(nèi)在動力。
描述性、預測性信息較多
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披露主要是從道德層面對企業(yè)進行約束,可定量的信息較少,以描述性的信息居多。這容易導致企業(yè)力求披露對自身的聲譽有利的信息,而避免披露使其聲譽受損的信息,以及產(chǎn)生信息冗余的問題,影響決策有用性。另外一些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例如氣候變化的厚尾分布、可再生能源價格、碳排放權交易價格、政策監(jiān)管趨勢等。企業(yè)需要預測影響公司未來可持續(xù)發(fā)展因素的變化情況,而預測信息存在概率問題就會降低信息的可靠性及可驗證性。這使得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更容易出現(xiàn)粉飾的現(xiàn)象。
既具有全球共性也具有地域特點
可持續(xù)發(fā)展可以是全體人類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例如聯(lián)合國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以及與之相適應的GRI《可持續(xù)發(fā)展報告指南》;也可以是某個國家或地區(qū)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例如歐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歐洲綠色協(xié)議》等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公司可持續(xù)發(fā)展報告指令》《可持續(xù)金融信息披露條例》;再如我國頒布的《生態(tài)文明改革總體方案》《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每個國家或地區(qū)都會根據(jù)經(jīng)濟發(fā)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階段性的社會問題等制定適合自身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并定期進行調整。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披露是根據(jù)國家或地區(qū)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進行制定的,它既具有全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共性,也具有地域特點。
如何做好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披露?
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的外部性需從經(jīng)濟學層面解決
處理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外部性的問題,必須從經(jīng)濟層面解決,單純的金融、會計原理沒有辦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例如氣候變化。從氣候變化經(jīng)濟學的角度來看,傳統(tǒng)經(jīng)濟學外部性內(nèi)部化已經(jīng)無法完全解釋和解決氣候變化對經(jīng)濟的影響,工業(yè)文明所倡導的刺激消費、投資和出口拉動經(jīng)濟的做法,產(chǎn)生的過度消費和過度生產(chǎn)對人類社會并不可持續(xù)。氣候變化對生產(chǎn)力的影響越來越大,一方面溫室氣體的排放權對發(fā)展中和欠發(fā)達地區(qū)來說是經(jīng)濟發(fā)展權;另一方面氣候容量對生產(chǎn)力或資本回報率有著顯著的影響。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經(jīng)濟發(fā)展需要氣候要素資產(chǎn)的高效利用而形成的零碳高生產(chǎn)力,并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氣候和生態(tài)友好的消費、技術、資本和生產(chǎn)方式。經(jīng)濟發(fā)展迫切的需要從工業(yè)文明向生態(tài)文明進行轉變,并發(fā)展出與之相適應的經(jīng)濟學原理(潘家華,2014)。這也是當前綠色金融發(fā)展所面臨的最大障礙。如何更準確地定義綠色資產(chǎn),又如何針對綠色資產(chǎn)落實綠色金融政策,外部性內(nèi)部化的理論基礎已經(jīng)不能滿足綠色金融的發(fā)展,需要依托氣候變化經(jīng)濟理論研究建立起新的綠色金融理論分析框架。
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披露可獨立于財務報告
基于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披露的特點,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披露較難成為財務報告的一部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兩者性質不同,會計是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單位,通過會計程序來反映企業(yè)財務狀況和經(jīng)濟成果的經(jīng)濟信息;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披露是在經(jīng)濟和法規(guī)之外對企業(yè)的道德約束,具有經(jīng)濟外部性。兩者性質上有本質的不同,較難合并。二是財務報告的受眾群體以資產(chǎn)所有者為主,而可持續(xù)發(fā)展報告是對企業(yè)道德層面的約束,受眾群體主要以資產(chǎn)所有者之外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為主。三是財務信息的質量特征要求其具有較高的準確性且可驗證,而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以描述性和預測性居多,無法達到財務信息的質量特征要求。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的質量特征多以重要性(實質性)原則為主,企業(yè)根據(jù)自身的商業(yè)模式、經(jīng)營業(yè)績、社會影響力等方面來評估哪些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是重要的,進而對重要的信息進行披露。重要性原則決定了企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披露的廣度和深度,同時可給予企業(yè)一定的靈活性。若要將財務信息和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合并則可能會影響財務報告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同時影響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的重要性。
國際可持續(xù)發(fā)展披露準則需給予各國家或地區(qū)一定的自主權
從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的特征來看,建議國際可持續(xù)發(fā)展披露準則在制定過程中參考聯(lián)合國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SDG),而同時給予各個國家或地區(qū)一定的自主權。如同聯(lián)合國制定SDG,每個國家再根據(jù)SDG制定各自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NSDS)一樣,由于文化背景、經(jīng)濟發(fā)展階段、政治體制等因素的不同,每個國家或地區(qū)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各不相同,需要根據(jù)各自國情制定與之相適應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信息披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