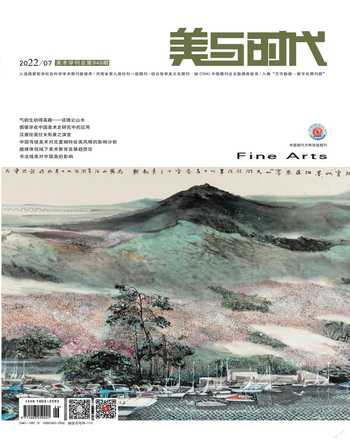古代繪畫中屏風自然風景圖像意義探究
摘 要:屏風作為傳統室內空間的藝術產物,以圖像形式在宋代傳世繪畫作品中屢屢出現,其中“畫中畫”的屏風又多填以自然風景圖像,這種繪畫模式與宋代文人雅士的作畫心境有著密切聯系。屏風中的自然風景畫在不同的繪畫題材以及情景下所承載的藝術表達內容也不盡相同。描繪宋代文人日常生活,自然風景屏風圖像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闡述詩詞中的屏風意象和自然風景屏風畫繪畫題材的基礎上,探討自然風景屏風在畫面上的內容與作用,并解讀自然風景屏風畫的世俗化及其與宋代文人之間的情感共鳴。
關鍵詞:屏風;自然風景;圖像意義
屏風作為室內空間裝飾與分割的重要工具,最早源起西周,但直到西漢,“屏風”一詞才真正出現。隨著歷史的發展與時代的更替,保留至今的屏風實物少之又少,屏風已化作特殊的傳統文化符號,開始以其他形式出現與傳播。屏風圖像很早就出現了,在不少傳世繪畫作品中都有出現屏風,例如《勘書圖》(南唐王齊翰)、《重屏會棋圖》(南唐周文矩)、《搗衣圖》(南宋牟益)等,屏風中的自然風景圖像的繪畫手法是很細致。屏風圖像通常繪于人物身后,作為人物背景圖像出現,在畫面中占比往往也比較大。從屏風圖像繪畫中,可以清晰看出文人雅士濃厚的屏風情結,以及其對山水畫的熱愛與重視,文人雅士的情感思想和屏風自然風景畫緊密相連。
一、詩詞中的屏風意象
屏風在詩詞中出現的頻率也是非常高的,在《全唐詩》《全宋詞》中有不少帶有屏風意象的詩篇。如秦觀《浣溪沙·錦帳重重卷暮霞》中的“錦帳重重卷暮霞,屏風曲曲斗紅牙,恨人何事苦離家”,“錦帳”暗示了主人公內心的寂寞,“屏風”再一次生動地刻畫出主人公因相思而失神的狀態。又如趙令畤《蝶戀花·欲減羅衣寒未去》中的“飛燕又將歸信誤,小屏風上西江路”,主人公嘆息人去卻無來信,看著屏風上的西江水路,泛起無限愁情。同樣的借屏風表達愁緒的詩句還有“夜深困倚屏風后”“屏風幾曲畫生枝”等。有的詩則點明了屏風分割空間的功用,比如蔡伸《滿庭芳·玉鼎翻香》中描述道:
玉鼎翻香,紅爐疊勝,綺窗疏雨瀟瀟。故人相過,情話款良宵。酒暈微紅襯臉,橫波浸、滿眼春嬌。云屏掩,鴛鴦被暖,敧枕聽寒潮。
從詞中不難看出,屏風主要用于分隔出內外空間。
二、自然風景屏風畫繪畫題材
自然風景題材繪畫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絕后的發展,宋代文人雅士鐘情于自然山水,常在詩文、繪畫中借景抒情,人與山水進一步的情感聯系是在人自然而然被秀美、多彩的風景吸引并為之觸動后發生的。《論語》中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可見,山水自古就具有一定象征意義。從相關宋代文獻中,也可以看出山水如何在宋代文人雅士生活中產生意義的,如《浮溪集·翠微堂記》中說:“山林之樂,士大夫知其可樂者多矣,而莫能有,其有焉者率樵夫野叟、川居谷汲之人,而又不知其所以為樂。”宋代文人把這種對自然風景的喜愛表現到了繪畫之中,又在繪畫之中以屏風為載體繼續呈現。自然風景題材繪畫在宋代頗多,大部分以全景式構圖展開,對于某些局部的刻畫也頗為在意。宋代的自然風景屏風圖像在傳世作品甚至是墓室壁畫都有出現。
關于宋代自然風景屏風畫的繪畫題材可大致分為三大類:山居圖類、仕女圖類、日常活動類。
(一)山居圖類繪畫
山居圖類繪畫的畫面內容以表現怡然自得的山居生活及環境為主,以簡單且直接的方式表現山水之樂,居住的房屋建在自然山水中,屏風也被繪于室內,這類屏風所占面積比較少。例如南宋劉松年的《四景山水圖卷之三》,亭屋建筑被山水靈泉環抱于其中,雖然亭屋面積只占據畫中一角,還是能較清晰地窺見隱藏在屋內的屏風,且屏風上繪有山水圖像。
(二)仕女圖類繪畫
屏風在古代室內有遮蔽、分割空間的功能,女子閨房中通常設有屏風,室內屏風的出現代表此刻環境是一個私密的空間。屏風除了用于隔絕內外室之外,也暗示了男女禮儀之意。出現于室外的女性周圍的山水屏風,更多代表的是一種內心情感的表現。例如,北宋蘇漢臣的《妝靚仕女圖》中,正在梳妝的仕女坐于一扇巨大的屏風前,旁邊站有一女侍從,仕女面對的巨大屏風上繪有纖細的水波紋,整幅作品氛圍嫻靜又略帶憂傷。
(三)日常生活類繪畫
日常生活類繪畫很普遍,描繪人們日常生活飲酒、享樂、休憩等場景。這類畫面可以視為對宋文人雅士現實生活的再現,而畫中屏風的出現,使得畫中場景像真的發生過一樣,屏風上的圖案也起到了烘托氣氛的作用,使畫面擺脫乏味單調。如北宋傳世名畫《重屏會棋圖卷》中,畫面屏中有屏并且繪有山水圖像,使場景籠罩上了一層真實且虛幻的意味。
三、自然風景屏風在畫面上的內容與作用
(一)情感隱喻
雅各布森的詩學理論,解釋了借喻和隱喻,繪畫中的屏風裝飾通常具有隱喻性。在整體布局中,用繪畫的形式傳達一種無法言表之意,而且畫中的屏風也往往和它面前的人物相關聯。宋代的屏風圖較前代變得逐漸詩意化,巫鴻在著作《重屏:中國繪畫中的媒材與再現》中說過,“畫屏”形象詩意化就意味著屏風裝飾的主要作用在于映射人們的情感、思想和心緒,這些都是無形的東西,在人物畫中很難加以表現。再看蘇漢臣《妝靚仕女圖》,這幅畫作于一面團扇上,前文提到過畫面中一名年輕貌美的女子正坐在梳妝桌前,面前的銅鏡映出她姣好的容顏,頗有對影自憐、孤芳自賞的意味。而在她面前的寬大的屏風上則是無數微細的水紋,此刻的屏風也正如這位年輕女子面前的鏡子,不同之處在于,屏風這面鏡子反映的并非女子的容顏,而是此刻她的內心情感世界。相似的情感色彩表現在北宋畫家李公麟所繪的一幅白描仕女圖中,主人公同樣為年輕貌美的女子,這次畫面中的女子是坐于榻上背對著屏風,身后的偌大屏風呈現了優美的山水風景,暗示畫中女子內心深處向往著自由,期盼著美好生活。王詵的《繡櫳曉鏡圖》同樣繪在精美的團扇上,畫中一名年輕女子站在一面葵花鏡前,凝望著鏡中的自己,旁邊一個侍女手捧茶盤,另一婦人正伸手去盤中取食盒,位于女子身后的一小面屏風孤獨地置放在床上,屏風中同樣是山水圖像,空蕩的山水畫面正如此時女子孤獨的內心。畫中的屏風和女性形象一同出現,屏風往往映射的是她們內心壓抑的情感。這種用屏風表達的隱晦方式,使主人公的情感抒發更加委婉,已經褪去了波濤洶涌,嫻靜中透露出幾許憂傷的無助感,內心世界和現實的外在世界有了較為明顯的對照。
(二)虛實相生
如果現實中的屏風是一種準建筑形式,對所處的三維或者四維空間起著分割與劃分的作用,那么繪畫中的屏風圖像便是表現于二維繪畫平面上的繪畫空間。此時屏風繪畫表現的是一個虛擬空間而非真實的,更像是想象中的現實圖景。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幅南宋繪畫作品《槐蔭消夏圖》中,一位高士上衣半解,袒胸露乳,在床榻上恬然入睡,左手自然放在腹部上,右手上舉放于頭旁,神情愜意灑脫,床榻周圍有屏風、案桌、硯臺、書卷等物品。整個畫面首先映入人眼簾的是一棵巨大的枝葉茂密的槐樹。畫者以水分大的點葉法用筆,使槐樹每簇葉子盈滿端莊而又略有風動,讓觀者不禁有涼爽、舒適之感,也符合繪畫的主題。而床頭立著一面屏風,上面繪有雪景寒林圖,給人一種清涼撲面的感覺。畫中槐樹與屏風之景似為一體。當代吳玉龍的《長安醉市圖》頗有相似之處,畫中屏風中的山石畫和后面的松石巧妙自然地交疊在一起,屏風里山石的磅礴氣勢襯托了高士們醉酒的悠然自得,烘托出高士心境曠達、自然逍遙之態,表達了遠離塵囂、淡泊名利、脫離世俗的精神向往。
還有個非常經典的傳世屏風繪畫作品——南唐周文矩的《重屏會棋圖》。畫中“多層屏風”使觀者對假象圖像產生似真實的感受,畫家用引人入勝的作圖手法,有意混淆并“誘惑”觀者進入畫中的虛擬情境且產生共鳴。畫面中主人公們正在下棋,周圍有觀弈的人,四周擺放有床榻、桌子、瓷器,主人公們的身后放置著一面寬大的單扇屏風。非常有意思的是,單扇屏風中同樣也繪有一面三折屏風,在觀者看來,此時正好像在窺探單扇屏風后面的內室活動。這里也許可以結合白居易的詩來理解這幅畫的重屏現象。“放杯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與展青氈。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暮年的詩人已行動不便,沉溺于一種半夢半醒般的松弛狀態之中。對他而言,日常的生活瑣事是如此遙遠和虛幻。它們只不過是幻想,就像投射在屏風上的場景一樣。畫家也許是受了白居易的詩的啟發,所作之畫有虛實錯位、內外延伸的特點。
元代畫家劉貫道所畫的《消夏圖》和周文矩的《重屏會棋圖》構圖方式極為相似,但前者畫中的士大夫儼然更像是一個超然脫俗的仙人。畫中士大夫慵懶地斜躺在床榻上,然而身后的屏風又顯示出士大夫自己另一個日常生活場景。屏風畫中這位士大夫所坐床榻與屏外的床榻相似,身邊有三位書童正在準備筆墨紙硯。畫中畫的屏風景象在此刻變成了想象中的美好隱居生活。因此,畫中屏風既是空間的藝術,又是時間的藝術。屏風畫與文人活動共同構成了一幅完整的世俗生活情景圖像。
四、自然風景屏風畫的世俗化及其與宋代文人
之間的情感共鳴
宋代自然風景屏風畫的盛行使畫家得以重新將自然景象與人物形象融為一體:這種屏風轉變為一種繪畫母題,用于輔助對人物形象的再現。從大量的宋代書畫作品中可以發現,自然風景屏風畫逐漸世俗化,不再局限于特定身份地位的人物,畫面的主人公可以是文人雅士,也可以是平民百姓,自然風景屏風儼然成了主題人物的背景。士人文化下的自然山水題材慢慢轉移到中國人物繪畫的題材中。在這一過程中,它失去了其特定的信息和象征意義,而成為“文”——文化或文雅——的一個寬泛象征。
文人雅士的思想心境通過藝術再現得到升華,畫面中的主人公一方面與屏風中所繪的自然風景共鳴,另一方面也與現實中的場景互動。再回看蘇漢臣《妝靚仕女圖》,坐在屏風前的年輕女子只能通過身后的屏風來表現自己的內心情感世界了。在整幅畫中,主人公和面前的銅鏡以及屏風之間的關系相互羈絆,屏風中所繪景色奠定了畫作略帶孤獨、憂郁的情感基調。這種表現手法使觀者對畫面有更深層次的了解,人物形象也更加生動,富有情感。
宋代文人畫家在構圖上的獨到之處在于,用隱秘的手法向觀者傳達畫面信息,畫中的情感也許也正是現實生活中畫家本人的真實寫照。文人士大夫追求身心自由,崇尚自然,而這種思想一旦受到壓迫就會迸發出炙熱的火花,特別是在動蕩時期。文人畫家們渴望平淡安逸的生活,但事實上,他們之中很少有人能夠做到歸隱山林,不為五斗米而折腰,因此,心中向往只能在書畫中體現,縱然被現實社會所束縛,但也要保持一顆純真、隱逸的心。理學在宋代頗具影響力,“存天理,滅人欲”是理學的主要觀點。為了彰顯自己超脫世俗的志趣,自然風景屏風畫逐漸成了文人雅士表達心境的重要媒介,因此宋人普遍在繪畫中加入屏風自然風景圖像。
五、結語
屏風自然風景圖像作為宋代繪畫中重要的題材,演變得越來越富有詩意。宋詞中常常用屏風作為映射思緒、情感的意象,表情達意,引起人們的共鳴。在宋詞中,“屏風”一詞也常為渲染詞意氛圍而出現,屏風中的自然風景圖像更類似于銅鏡中的影像,在畫面構成中是含蓄、隱晦的,更多時候是主人公內心活動與心境的投射物,所以屏風自然風景圖像在繪畫作品中不僅僅是裝飾性的存在,繪畫作品的藝術性也因此得到了升華。
參考文獻:
[1]盧曉菡.移畫入屏:屏風畫的視覺隱喻[J].愛尚美術,2018(1):100-107.
[2]彭時海.五代至宋繪畫作品中的屏風研究[D].湘潭:湖南科技大學,2017.
[3]郝遠.宋代文人的屏風情節[J].天津職業院校聯合學報,2016(4):121-124.
[4]杜晨.畫屏內外:淺析古代繪畫中屏風圖像的精神意義[J].人文天下,2021(11):90-93.
[5]劉蓉蓓.宋代文人屏風的生活美學探究[J].美術教育研究,2021(5):22-23.
[6]孟藝璇.中國古代傳統屏風圖式中的隱喻性表達[J].大眾文藝,2021(2):85-86.
[7]趙悅君. 從“畫中畫”看宋人對山水屏風的使用習慣及取向[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20.
[8]李婧怡.宋代女性形象的深層次解讀:以圖像史料為證[J].書畫世界,2020(3):94-95.
[9]曾憲洲.漢畫屏風圖像論[D].西安:西安美術學院,2019.
[10]李文琪.山水屏風、山居圖與書齋圖:宋代以來三種山水圖像之間的演變與聯系[J].中國書畫,2018(11):4-9.
作者簡介:
鄔楠,寧夏大學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裝飾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