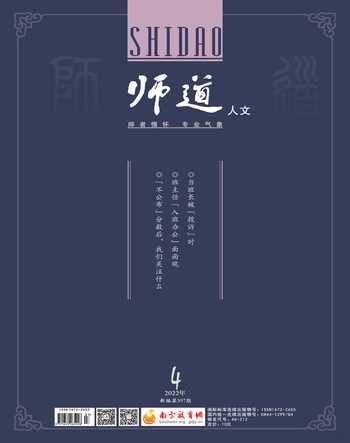打撈志怪文學的傳統
方棠

幾年前,和女兒共讀深見春夫的繪本《怪房子》時,其中一頁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怪房子的五樓,住著一些會動的家具,那些肉乎乎的家具長著孩子一樣的小腳丫,在房間里四處走動……彼時正閑讀《聊齋》,這幅畫面令我聯想起其中一則,頓感親切:“嘗見廈有春凳,肉紅色,甚修潤。李以故無此物,近撫按之,隨手而曲,殆如肉耎,駭而卻走。旋回視,則四足移動,漸入壁中。”(《宅妖》)合上書后不禁感嘆,沒想到能在日本的低幼繪本中偶得《聊齋》之遺風余韻。
后來,和女兒涉獵更多繪本后才慢慢發現,在日本童書中,鬼狐精怪故事可謂屢見不鮮——
我們曾讀過新美南吉童話改編而成的繪本《變成木屐》:小河邊的赤楊樹下,貍貓媽媽在教小貍貓變形的幻術。可無論是變小和尚還是變武士,小貍貓都變不好,令媽媽很失望。他最拿手的是變成木屐,于是變作一對木屐,躺在赤楊樹下。一位武士經過,穿起木屐就急匆匆地走了。貍貓媽媽嚇得目瞪口呆,擔心地跟在后面;小貍貓被壓得受不了,大哭了起來。武士發現真相后,到店里買了一雙新的木屐,給了小貍貓一塊錢,說:“辛苦你了!”小貍貓得到錢,全然忘記了痛苦,興高采烈地回家去了。
一個簡簡單單的小故事,卻生動而豐富,呈現出諸多層次和內涵:幼兒學習技能時遭遇挫折的情狀,母親對孩子的失望和擔憂,小孩子的單純和樂以忘憂的天性,以及作為人類的武士與動物精怪之間的融洽相處……
后來,我們又遇見了新美南吉更廣為人知的故事《小狐貍買手套》,由黑井健配圖的繪本描繪出如夢似幻的美麗場景:大雪天,小狐貍凍得爪子都僵硬了,于是媽媽帶他去鎮上的商店買手套。走到半路,媽媽實在邁不開步子,只好讓小狐貍自己去買。她把小狐貍的一只爪子變成小孩子的手,告誡他一定要從門縫里伸進這只手,否則會被人類抓走,關進籠子里。可到了商店門口,緊張的小狐貍卻伸錯了手。好在老板不以為怪,還是賣給了他一雙毛線手套。小狐貍在鎮子上流連,聽到了人類溫暖、柔和的談話聲,突然很想念媽媽,就飛奔著回到了媽媽身邊……
故事中,母親的高度警惕和孩子的全無防備仿佛是人類的寫照,懵懵懂懂的幼兒情態、母子間的親昵和柔情,令讀者的心也跟著柔軟起來。尤其與孩子共讀時,懷中有個同樣大小、懵懂的幼兒,似乎和書中的角色相映成趣。
除了新美南吉之外,安房直子筆下那片夢幻迷離的森林也深深地吸引著我們,那里充滿了花妖狐魅,有各種妖怪和精靈出沒,有各種奇異的事情發生:《狐貍的晚宴》中想親近人類的狐貍父女,《花香小鎮》里騎橘黃色自行車的花精們,《風的旱冰鞋》中偷臘肉的黃鼠狼,《手絹上的花田》里郵遞員夫婦因為貪心被變成了酒壺里的小人兒,《藏紅花的故事》里誤入森林的女孩被一個神秘的老婆婆變成了一只小黃鳥……在這個神秘幽深的世界里,動植物可以化作人形,人也可以被變成動物,人與自然之間、現實世界和非現實世界之間的界限變得微妙而模糊。
狐貍,黃鼠狼,花精,山精;隨意變形,幻化人形,在人類面前現出原形的恐懼;對人類的親近或敵視,與人類接觸時的小心翼翼……這一切讀來如此親切熟悉,因為這些都是我們傳統志怪小說中再熟悉不過的元素,是流淌在我們血液中的文學記憶。
除此之外,日本繪本中還有其他“神魔鬼怪”層出不窮,蔚為大觀,既有本土文化中的各種妖怪(如《木匠與鬼六》《小達摩和小天狗》),也有外來的幽靈(如《妖怪油炸餅》),乃至神話人物、怪獸等等。
常常忍不住贊嘆,這些兒童文學作家似乎都有一種魔力,他們能把種種光怪陸離的元素隨手拈來,將神秘、怪誕的因子融入兒童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像技藝高超的大廚一般,在最常見的食材中添加別有風味的作料,化樸素為神奇,烹制出別樣美味的佳肴來。
我不禁好奇,國內是否有許多類似的繪本呢?我們擁有如此悠久的志怪文學傳統,書中有過數不清的神仙鬼怪、花妖狐魅,可謂坐擁一整座寶庫。如果呈現在繪本中,又會是怎樣一番光景呢?
于是我找來了蔡皋繪圖的《寶兒》一書,它曾獲第 14屆布拉迪斯拉發國際兒童圖書插圖展“金蘋果”獎,是國內首部獲此殊榮的繪本。書中,商人的兒子“寶兒”憑借智慧、勇氣辨認出作祟于母親的狐貍精,并巧施妙計消滅了他們,從而拯救了母親,最后一家人其樂融融。故事由《聊齋》中的《賈兒》改編而來,是其中比較少有的以兒童為主角的故事。原文中商人盛贊兒子:“我兒討狐之陳平也。”清代學者但明倫也在文后點評道:“胸有成竹,目無全牛;膽大于天,心細若發。……討之于杯酒之中,玩之于股掌之上。”可見,《賈兒》是一個很適合改編成繪本的故事。它塑造了一個關愛母親、膽大心細的兒童“英雄”,比較容易引發兒童情感上的激蕩和共鳴,情節曲折生動,讀來頗有韻致。濃郁明艷的畫風和神秘緊張的氛圍也很吸引孩子的興趣,不愧為國產繪本的佼佼者。
查閱資料后發現,國內根據民間傳說、神話寓言、聊齋故事等改編而成的繪本數量眾多,如新蕾出版社推出的“中國神話繪本”系列、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國學啟蒙”叢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的“繪本森林·中國民間故事與神話傳說”系列、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的“繪本中華故事”大系列等等,不知凡幾。然而,對于有大量繪本閱讀經驗的讀者來說,卻很難列舉出多少膾炙人口的佳作,無非還是《寶兒》《一園青菜成了精》等少數個例。
是讀者們對國際大獎過于青睞、對國外繪本過于偏愛嗎?我想并非如此。究其根本,還是在于這些繪本大多是對定型故事的重繪重述,是對傳統文本的簡單改寫或沿襲;且大多帶有一定的目的性,比如向兒童普及我國的創世神話、民俗來歷,展示廣袤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化,對兒童進行“國粹”的啟蒙等。有些繪本在某種程度上是“主題先行”的,因而有時敘事難免淪為宣揚主題的“工具”,對傳統元素的使用也出現符號化的現象。它們往往具有較強的時代感,也缺乏足夠的童趣,并未真正關涉兒童當下的生活、關照兒童的情感和需求,與兒童的精神世界終究是有隔膜的。
然而,由《寶兒》的成功我們不難看出,傳統的精怪故事并未過時。它的文本依然有著強韌的生命力,而狐貍精等元素更是歷久彌新。由此,我忽然聯想起2019年風靡一時的科幻動畫短片集《愛,死亡和機器人》,其中第8集便講述了一個狐貍精的故事。它以聊齋故事為底本,卻雜糅了傳統、科技、反殖民、賽博格、復仇、女性主義等多種元素,奇幻而動人。可見,只要精心創作,傳統精怪元素依然能夠煥發出全新的面貌來。
好友談及自己五歲的兒子,曾無奈地說:“他還沒聽過嫦娥奔月,就已經知道月球上有環形山了。”現在的兒童也許很早便不再相信萬物有靈,不再相信童話。但是,《哈利·波特》依然風靡全球,“魔法”的吸引力依然無往不勝。我始終期待著,我們也能打撈志怪文學的傳統,了解、體察兒童,以兒童為中心,創造出更多奇異的、有生命、有真情實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