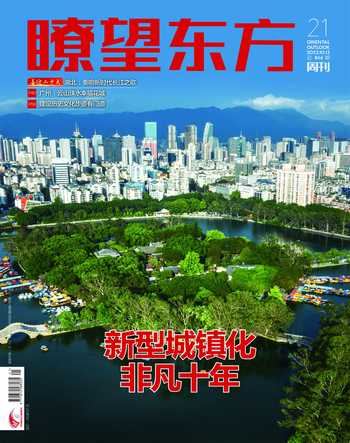“繡花式”治理
張靜

工作人員在上海長寧區新涇六村小區垃圾分類投放點清理垃圾箱外壁(方喆/ 攝)
北京市“接訴即辦”改革三年受理了6400余萬個民生來電,積累的大數據成為城市體檢報告的基礎;成都市在全國首設黨委序列的“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年投入15億元社區資金助力居民自下而上參與社區治理;南京市出臺全國首部社會治理地方性法規——《南京市社會治理促進條例》;上海市編織成型“兩張網”(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城市運行“一網統管”),讓數據在交換中“活”起來……
黨的十八大以來,依托黨建引領、社會參與、治理重心下移和智慧治理等方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快形成,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大幅提升。
精細治理提升品質
超大城市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中之重。進入新發展階段,以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超大城市為代表的中國城市成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排頭兵。
2018年11月27日下午,北京市石景山區金頂街街道辦事處,會議室里討論熱烈。圍繞背街小巷安裝路燈問題,住在附近的老街坊以及來自街道黨委、城管委、派出所、供電公司等單位的負責人,十幾個人各抒己見,好不熱鬧。
在全國率先利用人防地下空間建設智能立體停車場,優化存量泊位、升級停車引導服務,推進高精度停車地圖建設……青島從智慧停車出發,到“ 全市一個停車場”建設,正形成保障安全、提高效率、提升體驗、全面服務的交通管理新模式。
每當居民們生活中遇到難題,金頂街街道工委就會“吹哨”召集相關部門來到“老街坊”議事廳,一起探討解決問題的方案。這是北京市“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基層治理創新探索的縮影。
從黨建引領的“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到“聞風而動,接訴即辦”,再到“推動主動治理,未訴先辦”,黨的十八大以來,北京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斷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建設向縱深發展。
同樣,上海把法治作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的重要基石,立足超大城市管理需求,不斷細化、優化法制保障。
上海是全國第一個立法實施垃圾分類的城市。截至目前,《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已推行三年有余。
觀察上海的各個角落,可以發現許多因為垃圾分類而正在發生改變的地方:距離市中心東南約70公里的老港“消化”了全上海約50%的生活垃圾末端處理的填埋場,竟成了綠蔭環繞的生態保護展示窗口;在已經實現“濕垃圾不出小區”的新涇六村,市民侯阿姨投送到小區垃圾箱房的濕垃圾,經智能設備集中處理4小時后,變成了有機肥,又被侯阿姨拿回家養花……
深圳沙頭街道下沙文化廣場旁的商業街,干凈整潔,人來人往。“眼看著環境越來越好,住著越來越舒心。”居民黃先生說。這是深圳探索“物業城市”治理模式帶來的可喜變化。
“物業城市”,是深圳創新性引入市場化和社會化機制,將物業小區的管理模式延伸到城市層面的一種城市治理模式。
2021年1月,沙頭街道攜手萬物云旗下萬物云城全面開展“物業城市”“全域治理”合作,街道化身“大型小區”,管理小區的物業則升格為“城市管家”,共同對街道環衛、市政、城中村管理等各項工作進行監管。
“城市空間載體,是一座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面子,城市管理運營,是考驗城市治理水平和服務精細度的‘里子。”萬物云城相關負責人說,“物業城市”模式的創新價值在于把城市看作一個“大物業”,將物業管理的系統性思維和流程管理能力融入城市治理服務。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北上廣深這些受到世界矚目的中國超大城市,在城市治理現代化方面開展創新實踐,不僅關乎自身的安定有序、生機活力,亦是帶頭破解超大城市治理世界難題、彰顯我國制度優勢的深層使命。
社區治理走深走實
社區小窗口折射社會治理大發展。
從“坐等上門”變成“主動下沉”,十年來,社區治理的服務效率、質量和人才供應均得到有效提升。
合肥市包河區“60后”社區工作者杜世蘭回憶,早期的工作模式相對簡單,只要將上級政策精神傳達到社區,就算完成任務。2019年實行網格化管理后,網格員定期線上宣傳惠民政策,主動上門講解服務,延伸治理工作觸角。
社區治理理念由單純的管理轉變為主動細致的服務,春江水暖鴨先知,社區是否溫暖宜居,居民的體驗最真切。
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教授張軍等學者認為,為適應社區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的要求,就需要越來越多年輕人進入基層社區一線。
2022年,合肥市針對應屆大學生公開招考4000個社區“小管家”崗位,為基層治理注入青春血液,358名年輕的網格員赴社區任職。
據民政部統計數據顯示,當前,我國村委會、居委會主任大專以上學歷占比達到46.4%、82.6%。“年紀輕、學歷高、能力強成為新時代城鄉社區工作者的底色。”民政部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司司長陳越良表示。
黨建引領、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構成了新發展階段基層治理體系圖景。
2019年1月1日,天津市東麗區在全國范圍內率先建立“黨群網格”治理模式。利用信息化技術手段打通數據互聯互通渠道與網格員“3+N”的職責體系(3項基本職責:基礎信息采集、隱患巡查處置、聯系服務群眾;N為各部門申報的專項任務)進行深度融合,在提高基層治理效能的同時沉淀大量數據,再利用大數據分析結果推動基層治理工作,實現良性循環。

7月11日,浙江省湖州莫干山高新區的通航智造小鎮客廳,來自雷甸鎮的“小候鳥”在體驗通用機場投影數字沙盤
天津市東麗區張貴莊街網格員段曉靜在日常巡查中發現,小區花園涼亭橫梁斷裂存在安全隱患。她第一時間上報,街道網格中心調度職能科室隨即進行處置,不到兩天即完成維修工作。
人在格中走,數在線上跑。在網格化管理中心的大屏幕上,每個紅點就是一名網格員。“他們每天的行走軌跡、工作痕跡,系統都會實時記錄,在線呈現。”東麗區網格化管理中心主任袁懷國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網格員每天巡查2小時,發現問題和辦理事項,在系統的社區、街道、區網格化管理中心逐級上傳,分級辦理和存檔,成為動態管理數據。
2020年以來,平臺整合全區疫情快報、涉疫新聞、疫情卡口設置等關鍵信息,幫助全區各層級用戶快速了解轄區內當前疫情狀態。截至目前,東麗區網格員隱患巡查累計上報57.7萬件,處置解決55萬件,辦結率96.5%。
一個個網格支撐起社區治理高效能。據統計,全國村(社區)共劃分網格257.3萬多個,有網格員429.8萬人,北京等25個省份已經實現網格化服務管理全覆蓋。
黨和國家近幾年不斷對基層治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2020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構建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開放共享的基層管理服務平臺。
在陳越良看來, 2021年《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2022年《關于深化城市基層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若干措施(試行)》等文件發布,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城鄉社區治理的高度重視,也標志著我國城鄉社區治理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城鄉社區的地位得到顯著提升。
科技賦能智慧治理
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更新,為智慧治理開啟了全新窗口,推動城市治理步入正向循環——更多部門協同、更多場景落地、更多服務實現,由此沉淀出更多數據,不斷推動城市治理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
“物業城市”,是深圳創新性引入市場化和社會化機制,將物業小區的管理模式延伸到城市層面的一種城市治理模式。
游人如織的田子坊,是上海備受歡迎的打卡地。游客愛她的光鮮文藝,居民愛她的煙火氣息,管理人員看到的卻是可能存在的種種安全隱患。通過接入各種煙感設備、客流眼,田子坊成為上海實施數字治理的應用場景之一。
秉承讓市民企業“辦事像網購一樣方便”的理念,上海“一網通辦”已接入近3400項服務事項,累計辦件量約1.7億件。歸集各種電子證照超過600類,總數突破1.5億張。上海“一網統管”通過遍布全城的傳感器、攝像頭,將氣象、交通、安全等8大方面、430多類、1萬多項指標納入其中,實時感知城市生命體征,努力實現“治未病”“防未然”。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智慧城市從2015年開始大規模發力,近些年來聚焦城市大腦、一網統管和市域治理現代化,使城市治理越來越智能,一部手機管城市,城市治理的前瞻性、系統性和整體性顯著提升,城市的生態、韌性、宜居宜業等方面都有明顯提升。
近年來,更多的“大城智管”項目在全國各地城市鋪開,為城市治理武裝“頭腦”、擴展“視野”、延伸“手腳”,更多的公共服務領域實現了安全監管、智能響應、精準處置。
在全國率先利用人防地下空間建設智能立體停車場,優化存量泊位、升級停車引導服務,推進高精度停車地圖建設……青島從智慧停車出發,到“全市一個停車場”建設,正形成保障安全、提高效率、提升體驗、全面服務的交通管理新模式。
重慶市銅梁區城內所有大橋都裝上了健康監測系統,讓全區橋梁智慧化安全管理水平大幅提升。
義烏建設AR智能管網管理系統,深埋地下的供水管網立體實時地呈現在智能手機上,實現了供水設施智能化管理。
北京書院智慧社區基于AI、物聯網、云計算等技術,將室內的智能照明、智能用水、智能烹飪、智能健康等以及室外的智能門禁、智慧停車、AI安防等應用一體化深度融合,成為全場景智能社區。
天津河西區和京東集團搭建的智慧養老服務平臺建立應急救援機制,為許多獨居老人免費安裝“一鍵通”呼叫設備,開展全天候的應急幫扶。
……
“‘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中明確‘增強政府數字化治理能力,其中就包括‘強化政府數字化治理和服務能力建設。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仍是未來城市管理的發展方向。”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比如繼續推動‘場景治理理念,將場景治理作為數字化時代城市治理的主要方式。豐富數字技術應用場景,聚焦新經濟、消費、科創等領域,打造活力高效的經濟治理場景;聚焦交通出行、托幼養老、管理服務、智慧健康等領域,打造可感可及的社會治理場景;聚焦環保、交通、安全、執法等領域,打造安全韌性的城市治理場景。”

2021年5月18日,游客在位于杭州市臨平區塘棲鎮的塘棲枇杷產業博覽館觀看大數據數字大屏和鎮區沙盤(徐昱/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