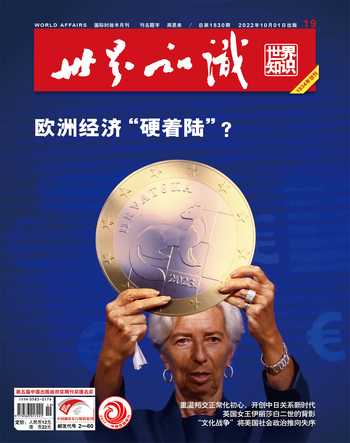成為第五大經濟體后,印度距發達國家有多遠
毛克疾
在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極端天氣等超預期因素疊加影響下,全球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前景都難言樂觀,但印度卻“與眾不同”。2022年9月2日,據外媒報道,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最新數據,印度已超過原宗主國英國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8月31日,據印度中央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2023財年第二季度(4~6月)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達13.5%,為二十國集團成員國中本季度最高增速;更早前的7月11日,聯合國報告預測,2023年印度將在人口數量上超過中國,成為全球第一人口大國;同時,印度又成為少數既能從七國集團、“四國機制”中獲益,同時又密切參與上海合作組織、金磚機制的國家。
在此背景下,2022年8月15日,在印度迎來獨立75周年紀念日之際,印度總理莫迪宣布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發展目標:到2047年將印度建成發達國家。那么,印度能否如愿實現發達國家之夢?
發展模式“揚短避長”
根據世界銀行2022年7月發布的最新標準,人均國民總收入須達到13205美元才能觸及“發達國家”的門檻。而2021年,印度人均國民收入為2170美元。照此情況,印度人均國民總收入必須連續25年至少保持7.5%的增速,才有可能在2047年成為發達國家。
為達成目標,中國的經驗恐怕最值得印度借鑒。同為人口超過十億的超大規模經濟體,中國保持兩位數的經濟增速近30年,成功推動中國農業經濟的工業化轉型,占據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關鍵位置,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不少印度學者指出,中國的秘訣在于“工業化”:通過激活內生勞動力稟賦,因時制宜發揮自身比較優勢,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并在其中不斷鞏固有利地位。
然而,長期以來,印度在超過50%的勞動力仍受雇于農業部門、90%的工人受雇于“非正規部門”的情形下,沒有利用自身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型制造業,反而越過初級工業化階段,直接進入服務業、資本密集型產業主導的階段。雖然印度常以信息技術(IT)服務、制藥等“高端產業”為豪,但其實質卻是“揚短避長”:資本密集型產業大量占用印度本就稀缺的資本,但充盈的人力資源卻遭閑置。這正是印度就業不足、出口乏力、貧富分化加劇等問題的源頭。
由于內生動力不足,新冠疫情暴發前印度經濟增速就已回落至4%的水平。從某種程度上說,莫迪若要實現發達國家之夢,其核心任務就是要深刻變革印度現行發展模式,借鑒中國以制造業為主導的工業化發展經驗,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
已有步入正軌跡象的工業化進程
無論從國際環境、國內條件,還是從莫迪政府的指導思想看,當前印度推動工業化已具備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
從國際環境看,新冠疫情導致的產品間斷性斷供,使一些西方國家更加重視分散風險,提高“供應鏈彈性”,同時美國對華產業、科技的“脫鉤”“斷鏈”也讓印度看到替代中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地位的絕佳機遇。作為全球唯一能夠在市場規模上對標中國的國家,印度被美西方寄予“替代中國”的厚望,莫迪政府還以此為“賣點”積極宣講。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印駐外機構就曾試圖以“增加供應鏈可靠性”為名,勸誘跨國企業“離華赴印”。在“四國機制”下,美日印澳也產生了“美國提供市場、日本提供產業解決方案、澳大利亞提供原材料、印度提供產能”的愿景。此外,印度與澳大利亞、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歐盟、加拿大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均取得不同程度的突破;2022年4月,印度聯合歐盟成立技術貿易委員會(TTC),旨在針對敏感領域、關鍵技術更好地協調雙邊立場;今年9月,印度還參與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談判四大支柱領域中的三個,即供應鏈、綠色低碳、公平經濟。這在貿易、技術、原材料供給等方面為印度推動本土工業化創造了有利外部條件。
值得關注的是,印度國內也出現諸多有利于工業化發展的變化。從執政方針上看,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臺便提出“印度制造”,此后又接續推出“印度自力更生”、生產關聯激勵計劃(PLI)等產業政策。莫迪政府已稱得上是印度自1991年實施市場化改革以來推動制造業發展最積極的一屆政府。從改革成效上看,莫迪政府不僅推出廢鈔令、商品服務稅(GST)改革、破產清算流程改革等強化經濟治理的舉措,還在聯邦和地方邦兩個層面有力推動勞工、征地等歷屆政府長期難以突破的改革,并取得初步成效。從地方政治上看,印度多邦政治勢力都開始在選戰中主打“工業牌”,承諾發展制造業,達到創造就業、盤活資源、拉動本地經濟的目的。各邦政府之間、邦內政黨之間圍繞制造業的競爭也達到全新高度。例如,印度人民黨執政的全印人口最多的北方邦的首席部長約吉·阿迪蒂亞納特就反復強調在邦內建設紡織服裝、電子裝配等特色產業集群,還創造性推出“一區一貨”的特色產業倡議。該倡議在北方邦取得初步成功后,還被聯邦政府采納,成為全國性產業倡議。

2022年4月20日,印度阿達尼集團創始人兼董事長高塔姆·阿達尼在第六屆孟加拉全球商業峰會上發表講話。
在內外有利條件的加持下,印度一些產業已取得突破性進展,其中手機制造業就是典型例證。2022年,印度不僅實現韓國三星、中國小米、OPPO、VIVO等在印度市場占據主流份額的智能手機的全部國產化組裝,還開始大幅擴產對本地產業鏈、供應鏈配套要求極高的美國蘋果公司的iPhone手機。專業調研數據顯示,2021年印度智能手機出貨量同比增長11%,達1.69億部,整體市場收入突破380億美元,同比增長27%。2021年,中國智能手機產量占全球的67.4%,而印度占比15.5%,位列全球第二。值得注意的是,蘋果、三星已開始加速自印度出口,推動2021年印度手機出口同比增長26%。
事實上,印度本土手機制造業的飛速發展已產生遠超其本身經濟意義的反響,不僅堅定了印度發展本土制造業的決心,還刺激印各級政府及企業向家用電器、汽車配件等更廣闊的制造業領域復制拓展成功經驗。
難以走出的“發展悖論”
然而,斷言印度已就此走上工業化快車道還為時尚早。近年來,印度經濟也暴露出諸多短板。
2014年莫迪提出“印度制造”時,制造業增加值占印度GDP比重是15.1%,但到2021年這一比重不僅沒有靠近25%的預設目標,反而落到14.1%。同時,根據印度學者統計,2020年印度每一個百分點的GDP增長創造的“正規部門就業數量”不到五萬個,僅為上世紀80年代的1/4。在印度經濟仍持續發展的情況下,制造業占GDP比重和GDP創造的正規崗位就業密度的雙雙下降表明,近年來印度制造業仍未能充分利用其豐富廉價的勞動力有效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
此外,盡管莫迪的制造業新政已產生一些積極效果,但其收益分配卻極不平衡——信實集團、阿達尼集團等大財團成為莫迪新政的最大贏家,而中小企業則趨于邊緣化。莫迪政府實施的廢鈔令、GST稅改等改革,雖然有利于強化經濟治理,但其清除灰色地帶后反而大幅推高中小企業的合規成本,利好規范經營程度較高的大企業。莫迪政府推行的降息、減稅、補貼、國企私有化等經濟刺激政策,雖旨在創造普惠性紅利,但大財團憑借自身體量優勢和緊密的政商紐帶屢屢攫取超額收益,進一步擠占中小企業生存空間。雖然印度經濟前景吸引了大筆國際熱錢和國內社會資本投資,但大財團憑借穩定盈利預期和強大政治靠山吸走大部分融資,中小企業融資困局并未得到明顯改變。
這種“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態勢正是印度工業化面臨的重大隱患。大財團享受超額政策優惠后,更傾向于發展鋼鐵、石化、能源、傳媒等獲利豐厚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同時努力避開利潤薄弱且極易產生各種合規糾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小企業雖已在勞動密集型產業賽道內,但卻難以獲得規模優勢,而一旦這些企業做大,又會逃離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本質上看,印度之所以長期無法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制造業部門,反而進一步固化扭曲的資源配置模式,正是因為這一悖論。
下一個全球地緣戰略事件?
目前,中國是全球第一個擁有十億級人口規模但徹底實現工業化的國家,而中國崛起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產生的影響毋庸置疑。從該角度看,印度工業化進程可能是今后一個時期內全球最重要的地緣戰略事件之一。
從某種程度上看,目前中國可能是印度崛起的最大受益者。例如,中印雙邊貿易額不斷擴大,2021年12月,兩國貿易額突破了1000億美元大關。同時,中國也一如既往地支持包括印度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走上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加快成長以鞏固“東升西降”的全球力量對比。
然而,客觀紅利并不是全部。從印度國內政策看,莫迪政府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不斷出臺對華經貿示強措施,其核心目的在于盡力排除中國經濟對它的影響,并試圖打斷中國在客觀上獲得印度崛起紅利的路徑。從全球地緣經濟態勢看,雖然印度目前遠未實現工業化目標,但卻試圖標榜自身為“中國替代者”來呼應部分西方國家的排華經貿政策。一旦印度具備了一定“替代中國”的產業貿易能力,或將大幅增加部分西方國家的遏華底氣。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看待有望成為“超大規模發達國家”的印度,不僅需要冷靜謹慎的戰術分析和揮灑寫意的戰略藝術,或許更需要從大國崛起的宏闊歷史圖景中汲取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