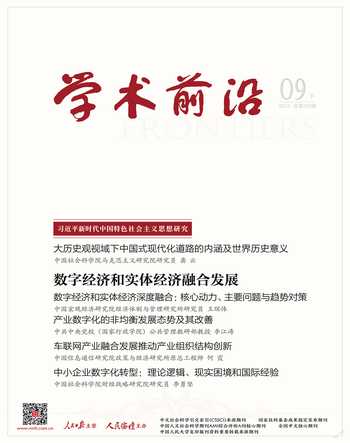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
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財富之源,是構筑未來發展戰略優勢的重要支撐;數字經濟是當今世界的科技革命先導、產業變革前沿,是搶占全球競爭制高點的關鍵領域。縱觀國家發展歷程,實體經濟存在于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為數字經濟的產生發展提供了基本條件和必要基礎。著眼全球發展趨勢,數字經濟在數字技術與人類社會全面融合中持續演進,為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注入強大動能和新的活力。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既是適應人類社會數字化變革的必然,也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要,同時是新形勢下我國主動把握新機遇、打造新引擎、帶動新發展的必備。
當前,我國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已經進入由大到強的發展階段,面對新的戰略機遇、新的戰略任務、新的戰略階段、新的戰略要求、新的戰略環境,亟需加快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支點。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成為重組實體經濟要素資源、重塑實體經濟結構、提升實體經濟競爭力的關鍵,數據資源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新要素,平臺經濟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新模式,數字設施為實體經濟提供新基建,數字貿易為商品和要素交易提供新方式,數字化轉型催動實體經濟出現新一輪擴張。
從國際角度看,鑒于數字經濟“贏家通吃”的發展特點,為搶抓其帶來的新機遇,各國都在提前布局,力求搶占數字經濟制高點。尤其是美歐發達國家期望利用新一輪數字技術,爭奪全球創新領導地位。一方面,這凸顯出當前與未來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態勢和趨勢,各國既有實踐和前瞻布局為我國提供了經驗;另一方面,在此過程中各國出現的網絡安全問題泛化、供應鏈安全隱患、數字治理與監管不足、勞動力擠出、數字鴻溝和算法偏見等問題,也為我國提供了鏡鑒。
從國內角度看,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和國家大數據戰略,拓展網絡經濟空間,促進互聯網和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支持基于互聯網的各類創新。黨的十九大提出,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建設數字中國、智慧社會。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
從國家層面部署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適應我國基本國情、主要矛盾、根本任務。近年來,我國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取得長足進步。2021年,我國產業數字化規模達到37.2萬億元,同比增長17.2%,占GDP比重32.5%;數字產業化規模達到8.4萬億元,同比增長11.9%,占GDP比重7.3%。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基于數字技術的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數字經濟在推動實體經濟恢復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在推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過程中,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各行業、各產業融合發展程度不均衡,數字技術尚未全產業鏈、全生命周期地融入實體經濟,關鍵核心技術外部依賴性大明顯制約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等問題也需要得到重視和解決。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推動制造業、服務業、農業等產業數字化,利用互聯網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這為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厘清了思路,明確了路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應進一步深刻認識“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本質與規律,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研判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趨勢,牢牢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戰略機遇,充分運用前沿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傳統模式進行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級,全面構筑起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的新優勢。
《“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把“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作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主線,并提出“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提質增效帶動作用顯著增強”的發展目標。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是搶抓數字經濟戰略制高點,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本期特別策劃聚焦“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敬請讀者垂注!
——《學術前沿》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