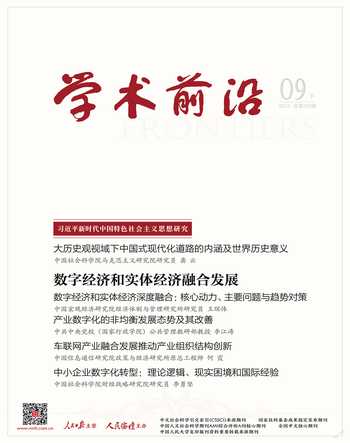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核心動力、主要問題與趨勢對策
王琛偉
【摘要】近年來我國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領域取得長足進步,但是一些前所未有的風險和挑戰也逐漸凸顯。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外部依賴性大,數字技術尚未全產業鏈、全生命周期地融入到實體經濟中,數字經濟本身也暴露出供應鏈安全隱患、數字監管缺失、數字鴻溝和算法偏見等諸多問題。從未來趨勢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越來越成為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機遇、推動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戰略制高點。為此,各國都在提前布局,力求搶占全球競爭主動權。新形勢下,我國應下決心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充分運用前沿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傳統模式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系統性改造升級,全面構筑起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的新優勢。
【關鍵詞】數字經濟? 實體經濟? 數字轉型? 關鍵核心技術
【中圖分類號】F49/F124?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8.002
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和命脈所在,數字經濟是當今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陣地前沿。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以數字經濟發展提升實體經濟發展水平、增強實體經濟綜合競爭力,成為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機遇,推動新一輪產業變革的關鍵環節。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明確要求:“要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推動制造業、服務業、農業等產業數字化,利用互聯網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特別是近年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數字化新產業、新業態不斷出現,數字經濟在恢復經濟、加快發展中的作用尤為突出。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已經成為新形勢下我國主動把握新機遇、打造新引擎,加快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實體經濟未來發展的核心推動力
數字經濟并非近年來提出的新概念,“信息經濟”是數字經濟的最初形態。早在1962年,美國經濟學家弗里茨·馬克盧普在他的《美國的知識生產與分配》一書中,提出信息經濟這一概念。伴隨科技水平不斷提升、信息技術廣泛應用,信息經濟的模式也在不斷演變發展,數字技術逐漸從信息技術中脫穎而出,成為標志信息技術發展前沿的代表。圍繞數字技術發展形成的經濟發展新模式,也逐漸形成一個新概念,即“數字經濟”。20世紀90年代,數字經濟開始逐步走向信息經濟的舞臺中央,1993年9月,美國政府公布“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行動計劃”(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即“信息高速公路”行動計劃,時隔一年又公布“全球信息基礎設施行動計劃”(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GII)。這兩個文件標志著數字經濟開始大規模付諸實踐。其后,北美、歐洲乃至亞洲各國也開始建立數字網絡、發展數字經濟,由此數字經濟在全球迅速發展。1995年,美國學者唐·泰普斯科特在《數據時代的經濟學:對網絡智能時代機遇和風險的再思考》(The Digital Economy Rethinking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一書中,首次正式提出“數字經濟”這一概念。
到底什么是數字經濟?國內外學者從三個層面給出定義。一是停留在從物質層面闡述定義,只是把數字經濟定義為信息通信基礎設施,或者擴展為信息的數字化(Brynjolfsson and Kahin, 2000)。這種觀點在數字經濟產生之初較為普遍,但是隨著數字經濟的深入發展,數字經濟的概念也隨之深化。二是著重從經濟層面定義數字經濟,認為數字經濟依托新技術,改變了傳統的經濟價值創造方式,數字經濟本身就是融合了數字技術的工業、農業和服務業,是數字化的實體經濟(鄔賀銓,2016)。可以說,數據只是主要的生產要素,數字技術只是提升生產效率的手段,而與此相關的全部經濟活動都屬于數字經濟的范疇。三是從對經濟社會影響的視角討論數字經濟的定義,認為數字經濟涉及生產、交換各個領域,涉及市場中的微觀經濟主體,促進了技術融合、產業融合、生產者和消費者融合,已經在新的經濟形態中處于核心地位,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裴長洪,2018;張亮亮等,2018)。在2016年G20杭州峰會上通過的《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指出,“數字化信息轉換為一項關鍵的生產要素,載體是現代的信息通訊網絡,助推劑是信息通信技術”,同時進一步定義,“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的數據作為主要生產要素、以信息通信技術和人工智能的有效使用作為載體的一系列經濟活動”。綜上可見,數字經濟是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數據資源是數字經濟的關鍵要素,數字技術是數字經濟的核心支柱,現代信息網絡是數字經濟的主要載體,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以及由此而來的一系列創新理念則是數字經濟的重要推動力,與此相關的一系列經濟活動都屬于數字經濟范疇。
近年來,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迅猛發展,數字經濟作為信息技術的陣地前沿,已經成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重要引擎。數字經濟具有不同于傳統經濟形態的突出特征。一是低成本和規模經濟。數字經濟使生產要素內容得到進一步擴展,數據成為繼勞動、資本、技術之后的又一基本生產要素。數據要素和數字產品存在非競爭性特征,可以接近于零邊際成本地無限復制,避免了傳統經濟形態中邊際成本先減少后增加的倒U形趨勢。除生產初期投入外,伴隨生產規模增加,數字經濟平均生產成本越來越低,出現規模經濟特征。二是融合性和平臺化。數字經濟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使產業邊界、行業邊界、市場主體邊界趨于模糊,第一二三產業之間及產業內部出現融合趨勢,生產者和消費者也出現融合現象。消費者在消費產品的同時,也生產數據信息;生產者在生產產品的同時,也在運用數字技術手段分析消費者偏好,消費和使用這些數據信息。生產企業和消費者、商品和要素在趨于融合的同時,也呈現出數字化的形態。例如,勞動者表現為學歷、工齡、專業等數字特征;資本則表現為資本規模、資本來源、抵押要求等數字特征。這些數字特征在共同面對連接平臺時處于平等地位,這為產品和要素、企業和消費者通過平臺進行交易和對接提供了可能。近年來,平臺企業迅猛發展,原因就在于平臺適應了數字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三是易壟斷性和易擴張性。與互聯網大企業相比,用戶處于弱勢地位。互聯網大企業以資本和技術優勢,壟斷著用戶的大量數據信息,通過分析用戶的消費偏好,使用戶對企業產生很強的粘性。互聯網大企業依靠這種優勢,不斷“吸附”用戶,使平臺在供需對接中處于壟斷地位。伴隨互聯網企業規模不斷擴大,邊際成本不斷降低,“平臺”表現出向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延伸的趨勢。
數字經濟在帶動各領域新技術不斷突破的同時,正在對實體經濟產生深遠影響。目前,企業正跨入數字時代的新階段,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加速推進,企業成功與否將取決于能否運用一系列新技術,為客戶、員工及業務合作伙伴帶來個性化的體驗(European Commission,? 2020)。數字經濟正在深度融入各行各業各領域,主要通過五個途徑全方位影響實體經濟發展。一是數據資源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新要素。這些數據來自于各種數字平臺上的個人、社會和商業活動的數字足跡。數字產業化已經打造并形成一個全新的“數據價值鏈”,其中包括支持數據收集、從數據中產生見解、數據存儲、分析和建模的各類公司。一旦數據被轉化為數字智能并通過商業用途貨幣化,價值創造就會出現(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9)。二是平臺經濟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新模式。近十多年來,全球各地涌現出大量使用數據驅動商業模式的數字平臺,打亂了現有行業劃界。數字平臺分為交易平臺和創新平臺,提供了讓參與者聚集在一起進行在線互動的機制(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9)。三是數字設施為實體經濟提供了新基建。數字產業快速崛起,5G、人工智能、區塊鏈、新一代高速寬帶等在技術層面有了巨大突破,推動基礎設施更新換代。特別是寬帶連接被廣泛認為是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關鍵因素。“有意義的普遍連接”(meaningful universal connectivity)的概念已經成為各國努力實現的重點方向(ITU/UNESCO Broadband Commiss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9)。四是數字貿易為商品和要素交易提供了新方式。數字貿易包括終端產品(如電影),以及依賴或促進數字貿易的產品和服務(如云數據存儲和電子郵件等工具)。數字貿易在全球范圍內不斷增長,增速超過了傳統的商品和服務貿易,對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超過了金融或商品流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9)。五是數字化轉型催動實體經濟出現新一輪擴張。數字技術的應用極大地提升了生產效率,產業數字化愈發成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方向,產業數字化的進程在不斷加快,展現出數字經濟融合實體經濟發展的強大生命力。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亞洲在產業數字化轉型方面已經走在前列,亞洲互聯網用戶占全球的一半,而且中國、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均位居世界數字化程度最高國家之列,即使是一些落后國家也在迅速推進數字化(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9)。
抓住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的主要問題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變著世界發展格局。黨中央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把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明確要求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繼續做好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這篇大文章,推動制造業加速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近年來,我國在數字經濟及其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中取得長足進步,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大背景下,一些數字化、智能化、“非接觸”的新產業、新業態不斷出現,數字經濟成為推動實體經濟恢復發展的重要形態。2021年,我國產業數字化規模達到37.2萬億元,同比增長17.2%,占GDP比重為32.5%;數字產業化達到8.4萬億元,同比增長11.9%,占GDP比重為7.3%(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
一方面,我國硬件設施已經邁入全球先進行列。我國已建成全球最大規模光纖和移動通信網絡,全面建成光網城市,5G基站、終端連接數全球占比分別超過70%和80%,全國行政村、脫貧村通光纖和4G的比例均超過99%,實現網絡、產業、應用全球領先(工信部,2021)。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上海數據交易所相繼成立,數據交易模式、交易平臺都在不斷完善。另一方面,我國軟環境瞄準國際一流水平不斷創新突破。《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更好服務市場主體的實施意見》等相繼發布實施,數字經濟“游戲規則”逐步規范,數字市場監管日趨完善,數據要素交易制度基本建立。我國在國際上參與各類技術標準制定的情況越來越多,截至2021年底,我國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中承擔的技術機構秘書處數量已達71個,占所有職位數的近10%,我國在技術創新中的國際地位正在明顯提升(中華標局,2022)。
但是也要看到,伴隨新技術快速發展和應用,一些前所未有的風險和挑戰也逐漸凸顯。從我國發展情況看,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各行業、各產業融合發展的程度不均衡。截至2021年底,我國第一二三產業數字化滲透率分別為10%、22%、43%(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2022)。第三產業數字化較為超前,但是第一二產業則相對滯后。科研和技術服務、文化娛樂、商貿服務等領域數字化滲透程度較高,工業領域數字化在加速,但農林牧漁等領域數字化進展則相對較慢。二是數字技術尚未全產業鏈、全生命周期地融入到實體經濟中。制造業是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關鍵環節,但相比于發達國家,我國制造業數字化水平仍有較大差距。2020年,我國制造業數字化滲透率為19.5%,2021年提高到22%,而德國、韓國、美國則分別達到43.9%、43.6%、36%,英國、愛爾蘭、日本、新加坡、法國等都超過33%的全球平均水平(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2022)。不少企業對數字技術的應用僅停留在辦公、服務等非生產環節,而企業生產的關鍵核心環節數字化程度仍然偏低,特別是中小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率更低。三是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外部依賴性大,仍然受制于人,對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形成嚴重制約。雖然歷經多年改革發展,我國在科技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要成就,但是,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總體科技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結構上,都存在較大差距。2021年12月,市場調研公司IC Insights發布報告顯示,在全球17家銷售額超過100億美元的半導體生產供應商中,美國有9家,歐洲有3家,中國僅有2家且均在臺灣地區。關鍵核心技術不能自主,深刻制約著數字經濟發展。一方面,一些產品的關鍵技術難以破解,在國際競爭中受制于人的情況時有發生。例如,近來美國在高端芯片領域對我國連續發難,甚至對“芯片之母”EDA芯片設計軟件斷供,這可能對我國芯片產業發展帶來十分不利的影響。另一方面,數字技術高附加值的受益者主要還是技術來源國,數字技術對我國制造業帶來的激勵作用難以得到充分發揮。目前,“中國制造”雖然遍布全球,但是占領的多為低端市場,核心技術及國際品牌仍然缺乏。
從全球情況看,伴隨數字技術在各領域廣泛應用,一些深層問題也逐漸顯現,影響著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一是網絡安全問題泛化,隱私保護存在風險。企業和個人對網絡產生明顯依賴性,但是一些涉及企業機密和個人隱私的敏感數據存在被盜風險,社會公眾普遍認為設備供應商可能在機器上設置“后門”,用來遠程控制系統或竊取信息。特別是5G的興起使物聯網安全危機四伏,面對與日增長的物聯網連接設備,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擔心物聯網的安全性。二是供應鏈安全存在隱患,設備和服務易被攻擊。不少數字產品技術專業性強、制造工藝復雜,整個產品供應鏈涉及多個國家的多個廠商,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只有你”的生產格局。供應鏈條各個環節都可能存在安全漏洞,供應鏈條的延長也給攻擊者增加了利用漏洞的機會。以芯片制造為例,一條芯片生產線可能涉及50多個行業、數千道工序,零部件供應商來自多個國家,防范供應鏈安全風險任務非常艱巨。三是監管體系有待變革,數字治理亟待強化。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已經遠遠超出傳統監管體系的約束能力。一些針對傳統經濟的監管手段,在面對數字經濟帶來的新產業、新業態時,既缺乏監管技術手段、技術標準,也缺乏有效的監管法律依據。特別是面對跨行業、跨領域、跨區域、多主體的數字生態系統,傳統監管體系基本無能為力。四是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數字鴻溝和算法偏見問題突出。數字鴻溝存在于不同國家、地區、行業、企業之間。由于數字技術水平并不均衡,技術應用程度存在差別,這使得國家、地區、行業、企業之間信息落差進一步加大,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算法偏見則存在于不同人群之間,弱勢群體容易被算法忽視,這些人因此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特別是一些未被發現和未被處理的潛在偏見,可能會使決策結果缺乏準確性和公平性,還可能使系統開發人員和用戶因違背反歧視法而承擔法律責任(Meltzer, 2019)。五是技術進步帶來勞動力擠出,數字經濟正在改變就業格局。技術進步對勞動力就業的擠出問題,最早起源于馬克思“機器排擠工人”的著名論斷。實際上,后來發生的經濟社會變遷,一直在證明這一論斷的正確性。Autor等(2003),分析了美國1960~1998年勞動力市場數據,發現計算機應用給勞動力市場帶來“極化效應”,程式化工作正在逐漸被計算機所取代。此后,Goos和Manning(2007)、Autor和Dorn(2013)以及Goos等(2015)分別對英國、歐洲勞動力市場數據進行分析,同樣發現這種“極化效應”。
把握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未來趨勢
加快數字經濟發展,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切實增強實體經濟的綜合競爭力,越來越成為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必然選擇和當務之急。誰能抓住這個“牽一發、動全身”的戰略關鍵點,誰就能在未來世界經濟競爭中搶占先機。科學研判未來數字經濟發展趨勢,準確把握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方向,對于我國抓住機遇實現彎道超車、高質量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從數字經濟及其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情況看,有幾個趨勢非常值得關注。
一是數字技術將充分釋放潛能,創造巨大的經濟價值。海量數據成為新興戰略資源,催生了云計算、人工智能、邊緣計算等新技術,不但釋放了生產潛能,提高了生產效率,也開辟了新的商業模式,大大提高了經濟效率。例如,根據布魯金斯學會預計,AI可能在未來10年為全球產出增值數萬億美元,并將推動經濟向服務驅動型經濟轉型(Meltzer, 2019)。同時,新技術還將極大地降低企業成本,波士頓咨詢公司預測,云計算有助于幫助企業節省15%~40%的IT運營成本(Dutta, 2019)。
二是數字經濟將改變社會運行模式,推動深刻的社會變革。教育、醫療和辦公等領域都可能發生根本性改變,遠程醫療時代可能到來,教育將加速向線上教育轉變,遠程教育將普及并服務于更多學生。多國政府已經在抓緊使用數字技術,打造“政策試驗臺”“監管沙箱”等工具,用于創新政策工具和方法,力求更為直接、高效地解決公眾訴求問題、數字監管問題。企業可能引入數字工作場所,實行遠程辦公,提高企業的生產率(European Commission, 2021)。此外,數字經濟還在深刻改變就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繼續快速重塑工作性質、就業模式、勞動法規和保護措施。
三是數字經濟將創新監管模式,構建全新的規制體系。雖然近年來,各國都在制定數字經濟領域的法律法規、政策措施,但是與層出不窮的新技術相比,監管措施和規制體系創新總是落后于技術進步的步伐。未來幾年內,數字經濟領域有可能迎來監管規則創制的高峰期,現行監管架構有可能全面重構,構建起全方位的新監管體系、新法律框架、新政策體系。監管創新是全方位的,涉及領域包括:倫理規范、公平和正義、隱私、消費者保護和數據可用性、產業政策、技術標準、創新生態系統、網絡安全、犯罪、執法、欺詐和欺騙、軍事應用等多個方面(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2021)。
四是各行業數字化轉型可能成為唯一發展路徑,顛覆性創新可能更易出現,勇于“取、舍”將是未來面臨的戰略選擇。數字經濟是技術進步的結果,也是市場競爭自然選擇的結果,數字經濟本身就代表當今世界技術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從18世紀60年代至今,人類社會已經經歷四次科技革命,每次科技革命都是一個技術進步與工業生產緊密結合的過程,也是一個在市場作用下大浪淘沙的過程。落后的技術和生產方式將被取代,而新興技術和生產方式成為下一階段的主流。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大背景下,數字經濟已經越來越深地融入實體經濟,貫穿整個產業鏈,融入生產制造、服務消費、技術研發等全過程,深深地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乃至人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環節。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廣度和深度都將前所未有地擴展,不能數字化轉型的企業、工藝都可能被市場淘汰。數字化轉型將成為企業存活、發展的唯一路徑選擇。
還需要指出的是,在傳統經濟數字化轉型的特殊歷史階段,任何一個公眾需求或工作場景都可能帶來技術創新,都可能形成對傳統工藝、傳統生產模式的顛覆性創新。例如,數碼相機的問世讓傳統膠片相機成為歷史,膠片做得再好也不會再有市場。面對尚未形成生產力的顛覆性創新技術,“取”則可能面臨未知的市場風險,還可能由此引發勞動力失業等社會風險;“舍”則可能失去顛覆性技術帶來的重大機遇。因此,企業可能經常面臨“取”與“舍”的艱難選擇。
為搶抓數字經濟帶來的新機遇,各國都在提前布局,力求搶先奪得主動權,搶占數字經濟制高點,特別是美國、歐洲均期望利用新一輪的數字技術,爭奪全球創新領導地位(World Economic Forum, 2019)。數字經濟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伴隨媒體、電信和科技的愈發集中,市場競爭將轉變為“贏家通吃”的壟斷競爭,引領數字經濟發展的國家將“成為世界的統治者”(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2019)。因此,從“起跑線”出發到率先搶占數字經濟制高點,成為數字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窗口期”,必將深刻影響全球競爭格局。2019年以來,美國密集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劍指抓住該“窗口期”。2019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維護美國人工智能領導力的行政命令》,發布《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規劃:2019年更新版》,決定啟動《美國人工智能計劃》,將AI定為國家優先事項,重點維持和加強美國在人工智能研發和部署方面的科學、技術和經濟領導地位,同時也從安全性、倫理和社會影響、數據共享、技術標準、研發人員、公私合作等角度提出了明確要求。隨后,美國防部網站公布《2018年國防部人工智能戰略摘要——利用人工智能促進安全與繁榮》,闡明了國防部加快應用人工智能的途徑和方法。
其他一些國家和組織也相繼制定出臺推動新技術發展的政策措施。2020年2月,歐盟委員會發布《塑造歐洲數字未來》戰略文件,提出歐盟數字化變革的理念、戰略和行動,力求建立以數字技術為動力的歐洲社會,將歐洲打造成為數字化轉型的全球領導者。2018年11月,德國發布國家AI戰略,不僅勾勒出本國AI發展戰略輪廓,同時也涵蓋了美國和中國的AI戰略關鍵要素,搶占全球戰略制高點的意圖非常明顯。2019年9月,德國正式發布《德國區塊鏈戰略》,決定在金融、技術創新、數字服務等多個重點領域采取支持措施。同時,日本也發布《科學技術創新綜合戰略2020》,針對AI、物聯網、大數據等革命性網絡空間基礎技術和機器人、3D打印等革命性制造技術,以破壞性創新為目標,制定戰略性創新創造計劃。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在數字經濟上的努力,凸顯出數字經濟及其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當前態勢和未來趨勢,也為我國經濟數字化轉型提供了經驗借鑒。
從我國情況看,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構建產業和技術競爭新優勢,已經成為我國增強經濟和科技競爭力,實現彎道超車、后來居上最現實的可行路徑。數字經濟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不僅對于我國是新的,對于發達國家同樣是全新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數字經濟將我國和發達國家放到同一條競爭起跑線上。加之我國人口多、數據資源規模大、數據應用領域廣,因此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較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優勢。從某種意義上說,加快數字經濟發展,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切實增強實體經濟的綜合競爭力,正在為我國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機遇,實現彎道超車、高質量發展,創造出極其寶貴的戰略窗口期。
深入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對策措施
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是搶抓數字經濟戰略制高點,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數字技術正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全面融入人類社會各領域和全過程,推動著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今后一段時期,應進一步深刻認識“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本質,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牢牢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戰略機遇,充分運用前沿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傳統模式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系統化改造升級,全面構筑起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的新優勢。
第一,下決心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切實改變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綜合相關材料可以發現,不同文章對數字經濟核心技術的界定有所不同,但是歸納起來,數字經濟核心技術主要包括五個領域:一是5G技術承載中國通信業彎道超車的重任。二是集成電路芯片代表國家高端制造業和電子信息產業的核心技術水平,也是國家信息安全的重中之重。三是量子通信是迄今為止唯一被嚴格證明為無條件安全的通信方式。四是通信、導航、遙感等應用衛星技術是國家空間基礎設施持續穩定、安全可控的重要基礎。五是大數據、算法、超級計算是人工智能的核心驅動力。雖然人工智能技術包括計算機視覺、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機器人和語音識別等多個領域,但是核心技術主要是指大數據、算法、超級計算等所有人工智能都必須用到的核心驅動力。
缺乏關鍵核心技術,一直是我國數字經濟領域產業創新和國際競爭的“軟肋”和“瓶頸”。當前,下決心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已經成為推動數字經濟發展,乃至加快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的關鍵所在,成為必須面對的一個“坎兒”。一是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全力推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對于一些周期長、風險大、難度高、前景好的戰略性核心技術和科研項目,應系統布局、系統組織,集中優勢資源,最大限度地激發各類創新主體的潛能、釋放各類創新主體的活力。充分發揮政府、市場各自的優勢,采取靈活產業政策,根據產業鏈條的動態變化適時進行政策調整,確保數字經濟產業鏈的高端化發展以及技術上的持續創新導向性。二是多途徑持續給予充足技術創新資金支持。除直接給予科研經費外,還應不斷創新資金支持方式。例如,美國通過發達的風險投資機制持續不斷提供創新資金支持,通過政府采購云計算服務的方式助力云計算的發展。這些做法都值得參考借鑒。三是逐步拓展軍民融合發展領域。在不涉及軍事安全的前提下,一些軍用技術可以用于助力突破核心技術。例如,美國政府能夠在滿足國家軍工需求的同時,長久地關注數字技術領域的基礎研究,有力助推了核心技術的突破,讓美國研發水平始終保持國際領先。四是更深更廣地參與數字經濟領域國際產業技術標準制定。條件適當的情況下,力求將本國技術標準國際化,爭取在數字經濟領域更大的國際話語權。五是構建超前的人才戰略體系,儲備一批數字經濟領域高端人才,千方百計幫助相關領域人才解決實際問題,最大限度地吸引、留住、用好人才。
第二,加快推動制造業全面數字化轉型,推動制造業全產業鏈實現生產模式、運營模式、企業形態的根本性變革。近年來,數字技術與制造業愈發呈現出融合發展的趨勢,制造業研發設計、生產流程、企業管理,乃至用戶關系都呈現智能化特點。推動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關鍵所在。因此,必須根據制造業的產業特點和差異化需求,加快推動傳統產業全方位、全鏈條數字化轉型,增強產業鏈關鍵環節競爭力,完善重點產業供應鏈體系,全面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一是深入實施智能制造工程。大力推動裝備數字化,開展智能制造試點示范專項行動,完善國家智能制造標準體系。培育推廣個性化定制、網絡化協同等新模式。二是大力支持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改造,支持企業加快推進線上營銷、遠程協作、數字化辦公、智能生產線等應用,逐步實現研發、生產、物流、服務全流程數字化轉型。三是加快推動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打造一批數字化新型企業,培育一批“專精特新”企業和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加快構建以企業為核心的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新形態。鼓勵和支持互聯網平臺、行業龍頭企業開放數字化資源,幫助傳統企業和中小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四是積極推動數字化產業鏈延伸。在抓住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這個核心的同時,還應加快推動農業、服務業數字化轉型,提高數字經濟在農業、服務業的滲透率,提升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均衡性、可持續性。
第三,加快優化數字營商環境,夯實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基礎。加快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運用數字化、智慧化技術,創造適應數字經濟發展、適合數字技術人才成長、保障數字信息安全、催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體制環境、政策環境。一是構建完善的新型基礎設施體系。在以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等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領域,要精心規劃、加大投入、加快建設,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支撐。同時還要打造大數據網絡中心、超算中心、工業互聯網平臺等,全面提升實體經濟數據采集、存儲、處理和分析的能力。加快對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與升級。二是打造國際一流的智慧政務服務。優化數字營商環境,用數字技術改造提升政務服務,積極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5G+數字政府”建設,在實施“一網通辦”上取得新突破。積極推進政府服務熱線標準化建設,探索推動“政務新媒體聯盟”平臺建設。大幅提升政務服務水平,繼續推進“一網、一窗、一門、一次”改革,打破數據壁壘,規范服務標準,提高窗口服務效率和水平。三是構建與數字經濟相適應的數字監管體系。加快數字監管領域的立法,明確數據產權歸屬,規范數據使用規則,加強數據安全保障,強化數據產權及隱私權保護,探索解決數字鴻溝、算法歧視、惡性競爭等數字經濟發展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推動制定AI倫理指南,創建“數據治理委員會”,讓更多利益相關者參與到數據治理中來。四是全面推動商務服務領域數字化轉型。在以數字技術提升政府服務的同時,還要加快推動商貿、物流、金融等服務業數字化轉型,優化管理體系和服務模式,提高服務業的品質與效益。推動產業互聯網融通應用,以供應鏈金融、服務型制造等為重點,培育融通發展模式,促進企業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數據鏈、資金鏈、服務鏈、人才鏈全面融通,以數字技術促進產業融合發展。
第四,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從根本上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當前,世情、國情深刻變化,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創新驅動發展任務十分艱巨。強化科技創新,不能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停留在表面,還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從根本上創造適合科技創新的有利環境,切實增強創新主體的內在活力和創新動力。新形勢下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必須牢牢抓住兩個關鍵領域。一方面,在科研成果不能市場化或難以市場化的原創性基礎研究領域,要構建“讓科研人員舒心的科研生態”。核心在于:充分尊重科研的自身規律,創造寬松自由的環境、尊重信任的氛圍、廣闊充分的前景、服務科研的機制、激勵創新的制度、科學評價的導向、豐富易得的資源、無后顧之憂的保障,全方位構建讓科研人員舒心的科研生態。不僅吸引科研人才“來”,更要讓科研人員“留”;不僅要留住科研人員的“人”,更要留住科研人員的“心”。讓科研人員無后顧之憂地、充滿希望地、滿懷熱情地、寬松自由地創造。另一方面,在科研成果可以市場化的應用研究領域及部分基礎研究領域,要完善“以市場激勵為導向的高效管理體制機制”。核心在于:進一步依靠市場機制配置科技資源,加快建立主導產業技術創新體制機制。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生產、教育、科研深度整合,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市場化技術創新體系。加快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激發企業技術研發投入的積極性,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使企業通過技術創新獲得合理的市場補償。充分發揮政府搭建平臺、監督管理的作用,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強有力服務。力求通過體制機制創新,破除制約創新驅動發展的體制機制瓶頸,推動數字經濟領域創新不斷取得新突破,發揮出數字經濟的核心引領帶動作用,在更深層次上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
參考文獻
裴長洪、倪江飛、李越,2018,《數字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財貿經濟》,第9期。
鄔賀銓,2016,《數字經濟就是實體經濟》,《南方企業家》,第12期。
張亮亮、劉小鳳、陳志,2018,《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戰略思考》,《現代管理科學》,第5期。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7/t20220708_405627.htm。
《工信部:我國建成全球最大規模光纖和移動通信網絡》,2021,https://www.cnenergynews.cn/dianli/2021/09/14/detail_20210914106487.html。
中華標局,2022,《2021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主要數據》,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Q3NDkzMw==&mid=2247509688&idx=1&sn=3fc4adb4d66e04435db787d4e04cabc5&chksm=ec12fa22db6573340ba4fcf4348912a3a93f4b3e29053bb8227130f6332658e5f514585ee4bb&scene=27。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108/t20210802_381484.htm。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2019, "Digital Trade and U.S. Trade Policy,"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4565.
D. H. Autor; F. Levy and R. Murnane, 2003,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4).
D. H. Autor and D. Dorn, 2013, "The Growth of Low-Skill Service Job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5).
E. Brynjolfsson and B. Kahin, 2000,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Economy: Data, Tools, and Research,"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6(3).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EFF), 2019, "A Cycle of Renewal, Broken: How Big Tech and Big Media Abuse Copyright Law to Slay Competition," https://www.eff.org/deeplinks/2019/08/cycle-renewal-broken-how-big-tech-and-big-media-abuse-copyright-law-slay.
European Commission (EC), 2020, "Shaping Europe's Digital Future: Commission Presents Strategies for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73.
European Commission (EC), 2021, "Humans and Societie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ec.europa.eu/jrc/communities/en/community/digitranscope/news/humans-and-societies-age-artificial-intelligence.
ITU/UNESCO Broadband Commiss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9, "The State of Broadband 2019: Broadband as a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ttps://www.broadbandcommission.org/Documents/StateofBroadband19.pdf.
J. P. Meltzer, 2019,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imer: What is Needed to Maximize AI's Economic, Social, and Trade Opportunities," https://essentials.news/ai/ethics/article/artificial-intelligence-primer-needed-maximize-ais-economic-social-trade-opportunities-1d6c5de6a6.
M. Goos and A. Manning, 2007, "Lousy and Lovely Jobs: the Rising Polarization of Work in Britai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1).
M. Goos; A. Manning and A. Salomons, 2015, "Explaining Job Polarization: Routine-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Offshor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8).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 2019, "Asia-The Future is Here," http://www.199it.com/archives/934270.html.
S. Dutta; G. Grewal and H. Hrishikesh, 2019, "For Many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the Cloud is Ready for Prime Time,"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19/enterprise-applications-cloud-ready-prime-time.aspx.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ACUS), 2021, "The China Plan: a Transatlantic Blueprint for Strategic Competition,"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china-pla-n-transatlantic-blueprin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2019,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19 Value Creation and Captur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https://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aspx?publicationid=2466.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2019, "Innovate Europe: Competing for Global Innovation Leadership,"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innovate-europe-competing-for-global-innovation-leadership.
責 編/桂 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