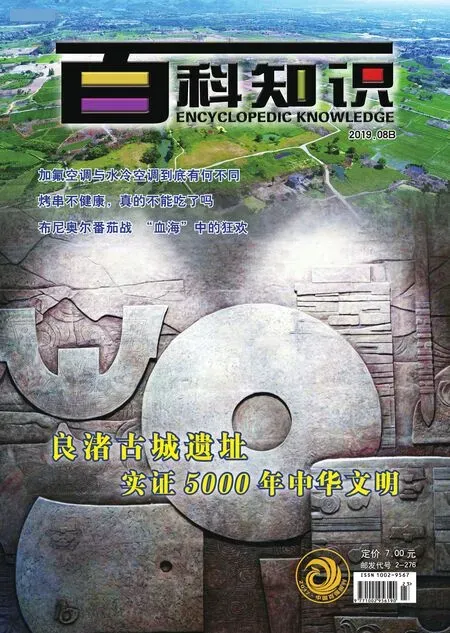植物園的過去和未來
史軍
前不久,國務院批準在廣州設立的華南國家植物園正式揭牌;而在此前的4月18日,國家植物園已在北京揭牌。
對于人們來說,植物園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所在。植物園究竟是怎樣一個地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它可以是長滿漂亮花草的公園,也可以是空氣清新的休閑健身場所,還可以是帶孩子認知植物的科普場地。
以上這些答案,也對,也不對。植物園絕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拍照背景板和休閑健身場所,多姿的花草只是其外表,在其美麗的外表之下包裹著植物科學研究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強大內核,并且這些方面正在越來越多地影響甚至重塑我們的生活。
到底什么是植物園?這要從植物園的起源和歷史說起。
從皇苑到植物園
上林苑是我國秦漢時期的著名皇家園林,從秦朝開始興建,漢武帝則對其進行了擴建。它地跨長安、咸陽、周至、戶縣、藍田五縣境,縱橫300里(約124千米),可以說是一個巨型皇家園囿。在這座皇家園林中,不僅生長著本地植物,而且有從各地移植來的珍奇花木。為了培育那些來自南方的熱帶和亞熱帶植物,上林苑中還修建有名為“扶荔宮”的溫室。如果從收集、保存和培育植物等功能看,上林苑可以稱得上是我國最早的植物園。包括后來出現的很多皇家園林,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兼具此類功能。
在同一時期的歐洲,同樣有很多栽培、收集植物的藥草園,如亞里士多德和泰奧弗拉斯托斯都有自己種植物的藥草園,我們可以將其視為歐洲植物園的雛形。

不過,這些園林顯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植物園,在它們的實際用途中,植物學研究所占比重很低。比如,上林苑兼有軍事訓練基地的功能,其他植物園多數是為了收集藥草和經濟作物,或者容納來自異域的動植物貢品。與古代中國的園林相比,歐洲的藥草園更偏重于藥用植物的分類鑒別、栽培和教學使用。
到了16世紀,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歐洲的船隊出現在世界各處的海洋上,尋找著新的貿易路線和貿易伙伴,以發展新生的資本主義。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植物也隨著各國船隊被帶回歐洲,植物分類學因此有了極大發展,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植物園伴隨植物學的發展出現了:1544年,意大利比薩大學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的植物園,并保存至今。
在出現早期,植物園主要以收集、保存從其他地方引種的植物為主,同時進行馴化和研究。進入20世紀之后,植物園的主要工作是進行植物分類學和相關學科的研究。到20世紀末,諸多植物園的工作重心開始逐步轉移到植物多樣性保護上。
南京中山植物園是我國最早成立的植物園,其前身可追溯至1929年的“中研院自然歷史博物館植物學部”及“孫中山先生紀念植物園”。1926年,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委員會開始營造中山陵。金陵大學樹木學教授陳嶸建議,在陵園內開辟植物園。1929年,植物園開始籌建;到1937年底,該植物園已建成多個展覽區并開展了多項研究。1954年,植物園由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華東工作站接管和重建,并定名為中國科學院南京中山植物園。
到今天,我國已擁有植物園近200個,它們分布于全國各地。
我們為什么需要這么多植物園?現代植物園的功能是什么?

總體而言,植物園在當前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功能,分別是植物遷地保護和種質資源保存、植物資源可持續利用、相關科學研究以及科普教育。
遷地保護入新家
植物遷地保護和種質資源保存是植物園最重要的工作,這些工作恰恰也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核心工作。這兩年,生物多樣性保護已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概念,但很多人未必清楚為什么要保護生物多樣性。
我們用一個例子簡要說明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意義。在南美洲的森林里有一種不起眼的植物,名叫金雞納樹。雖然在很久之前,當地人偶爾也會采集它們的枝葉,但是這種植物并未像其“同鄉”玉米那樣光耀史冊。不過,金雞納樹在醫藥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曾挽救了無數瘧疾患者的生命,其中就包括清朝的康熙皇帝,甚至直到今天,金雞納樹依然發揮著治病救人的重要作用。也正是這種植物的發現,促進了人類對熱帶區域的開發,甚至影響了人類歷史的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歐洲殖民者來到之前,南美洲并沒有瘧疾這種疾病,歐亞大陸和非洲大陸也沒有金雞納樹。所謂毒物和解藥相伴相生的故事,只存在于武俠玄幻小說里。回望歷史,假如金雞納樹在尚未被發現之前就因被破壞殆盡而無法用于瘧疾治療,人類歷史可能要被改寫。這也恰恰是我們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動因,因為生物多樣性是全人類的寶庫,其中包含著一個個生物未解之謎的答案。
事實上,生物多樣性帶來的影響遠不止于此。人類今天面臨食物、疾病、氣候變化等諸多難題,或許這些問題的答案就藏在不起眼的植物體內。不過,如果生物多樣性沒有得到足夠保護,很多問題的解決方案可能會隨著物種的滅絕而消失。2002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六次會議一致通過的《全球植物保護戰略》指出,沒有植物,就沒有生命,地球的運轉和人類的生存都依賴于植物。
目前,我國已發現的高等植物大約有3.6萬種, 其中受威脅的植物(即珍稀瀕危植物)大約有4000種,加上未受評估的種類,全國約有11%~15%的植物為受威脅種類。保護好這些物種,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全人類的發展,都具有重要價值。
對這些物種有幾種保護方法,其中一種是遷地保護。所謂遷地保護,簡單來說,就是把那些生存受威脅的植物搬遷到一個新的合適的環境中保護起來,讓它們能更好地生長繁衍。
植物園是遷地保護的主要形式,也是這些遷地保護植物的新家。1985年,第一次“植物園和世界自然保護戰略”國際會議在西班牙召開,將植物園與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緊密聯系起來,使得遷地保護成為植物園越來越重要的使命。近些年,將就地保護、遷地保護、植物回歸相結合的綜合保護理念,日益受到重視,并被應用到植物多樣性的保護中。
從植物獵人說起
豐富的物種收集是植物園特別是國家植物園的根本特色。無論是植物遷地保護、植物科學研究,還是科學傳播和園林園藝展示,都需要建立在豐富的物種收集基礎上。談到植物物種收集,就不能繞開一群被稱為植物獵人的人。

植物獵人究竟是些什么人?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有人說,他們是冒險家;也有人說,他們是博物學家;還有人說,他們就是赤裸裸的物種強盜。無論如何,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植物獵人是歐美貴族圈里的紅人,因為他們可以從遙遠的異域帶回新奇的植物;更重要的是,將新奇物種帶回國的這種行為,象征了帝國蒸蒸日上的國力和科技的進步。
維多利亞時代是大英帝國最輝煌的“黃金時代”,也是英國植物獵人在全球搜集奇花異草的黃金年代。對當時的歐洲人來說,美洲大陸是一個神奇的地方,那里的植物與舊大陸完全不同。比如,茄科植物在歐亞大陸是毒物的象征,但美洲偏偏有土豆、辣椒、西紅柿等眾多茄科植物;歐亞大陸的豆子等果實都結于藤蔓之上,美洲偏偏有埋在土里的大花生;更不要說木薯、番木瓜這些在舊大陸從未出現過的植物。獨特的生存環境和長時間的地理隔絕,讓美洲大陸擁有與歐亞大陸迥異的物種。王蓮就是其中之一。

王蓮是睡蓮科王蓮屬多年生或一年生大型浮葉草本植物。1837年,英國探險家羅伯特·赫爾曼·尚伯克在英屬圭亞那首次發現亞馬遜王蓮。巨大的王蓮讓探險家大為震驚,在當時的八卦消息中,王蓮是一種花朵周長1英尺(30.48厘米)、葉片每小時可長大1英寸(2.54厘米)的神奇植物。由于圭亞那是英國在南美洲的第一塊殖民地,巨大的花朵、嶄新的殖民地等身份信息交織在一起,王蓮這種植物身上也被賦予了更多深層次的含義,與當時的大英帝國緊緊捆綁在一起。
英國植物學家約翰·林德利(John Lindley)經過鑒定,將王蓮定為睡蓮科下的一個新屬,并以維多利亞女王的名字為其命名,用來祝賀女王登基。至此,亞馬遜王蓮聲名大震。很快,英國園藝學家掀起了一場讓王蓮開花的狂熱競賽,不同的家族為此角力,各路人馬不斷嘗試從亞馬孫流域運回各種王蓮的植物體。1844—1848年,人們的多次努力均以失敗告終。不要說開花,即便在英國本土得到活的王蓮植株都異常困難。直到1849年,園藝學家才發現癥結所在—王蓮的種子不能離開水。一旦離水干燥,種子就會死亡。1849年2月,保存在清水中的王蓮種子順利抵達英國;3月,英國皇家植物園得到6棵王蓮植株;到了夏天,王蓮植株數量增加到15棵;當年11月,亞馬遜王蓮的花朵第一次在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綻放。為了觀看這種特殊植物,邱園游客數量驟增。

盡管植物獵人出于種種目的收集植株的種子,但他們也在無形中對植物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當然,植物獵人的使命并不僅止于收集奇花異草,他們還是推進帝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比如,正是這些植物獵人想盡辦法從中國獲得了茶樹種苗和種植技術,并將其偷偷帶到印度,才使得英國最終擺脫長期以來對于中英茶葉貿易的依賴。在這一過程中,一位名叫羅伯特·福瓊的植物獵人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851年,福瓊為印度帶來了12838棵來自中國的茶樹幼苗以及8名熟練的制茶工人,由此成就了印度的制茶產業。再比如,我國古老的傳統觀賞植物,如菊花、山茶、牡丹、月季等,都是隨著植物獵人遠渡重洋進入歐洲的,并給英國的花卉園林產業帶來了巨變。
時至今日,如同冒險家一般的植物獵人似乎已成為歷史,但不同國家對植物種質資源、遺傳資源的重視程度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對植物資源的探索、整理和研究開發,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和保障,不僅影響著我們的衣食住行、醫藥健康,更關乎全球氣候變化,關乎人類的未來。從某種意義上講,保護好我們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好我們的物種資源,是關乎國家安全的大事。
植物的“諾亞方舟”
種子,是植物遺傳信息的攜帶者和傳遞者,是植物繁衍之源,也是一國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全球環境問題日益凸顯。人類逐漸意識到,一味追求工業發展,已對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造成難以彌補的創傷,世界上的植物正以驚人的速度消失。研究表明,一種植物常與10~30種其他生物共存,一種植物滅絕會導致這些生物的生存危機。
不同種子具有的基因差異也會影響植物物種的未來。對于植物特別是那些人類賴以維生的農作物而言,缺乏遺傳多樣性是一件異常危險的事情。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的香蕉枯萎病(也叫巴拿馬病、香蕉黃葉病,是一種通過土壤傳播的香蕉傳染病,染病植株會逐步枯萎死亡)事件,這種病害幾乎摧毀了全球所有的香蕉種植園,并且讓“大米歇爾”這個近乎完美的香蕉品種徹底消失。雖然科學家最終找到了口味略差但抗病性更強的替代品種“卡文迪許”,但這件事給人們敲響了警鐘,此類災難性事件絕不是孤例,也絕不會僅僅存在于電影和小說當中。
遷地保護不是簡單地把植物挖過來栽在植物園里,而是要建立種質資源庫,保存植物的種子、組織、器官,并深入研究植物的形態學特征、系統和進化關系、生物學規律等,進而推動植物種群的保護與恢復。
因而,保存種質資源對于人類未來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幸好,占全球植物1/3的物種被保存在各國的植物園里,總數約有8萬種,各國的植物園因此成為地球植物的“諾亞方舟”。
在實踐中,無論是收集活植物還是收集種子,都有講究;不管是采集還是保存,各有各的門道。
在種質資源保存中,并不能隨意采集種子和植物體,而是有著嚴格的規范。為了保證這些植物材料具有足夠的遺傳多樣性,需要在不同地點的不同種群中采樣,即便碰到植物異常集中、種子異常豐富的地點,也不能一次性收齊。植株和植株之間至少要間隔20米,種群和種群之間至少要間隔50千米。這樣做就是為了保證采集到的種子擁有遺傳多樣性。

采集到合格的種子只是第一步,要讓這些種子和植物體存活下去,還需要很多后續工作。目前,低溫和干燥是延長植物種子壽命的有效方法。不管是挪威的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還是在我國昆明的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都采用類似的低溫干燥環境保存種子。這些保存起來的種子,必將成為人類未來的希望。將種子保存在種質庫中還不算完,這些種子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抽查一次,以檢驗其發芽率,保證能在關鍵時刻為人所用。
到今天,植物園早已不是一個簡單的識別植物的藥草園,也不是一個僅供大家拍照的美麗花園,更是為了人類未來發展保存希望的方舟。在未來,植物園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成為新的研究場所和人們認知自然的平臺。
百園百態各不同
到目前為止,我國共有近200個植物園。雖然都叫植物園;但不同植物園所處的地區氣候環境各不相同,適宜栽培的植物也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特色。
國家植物園,位于北京,由南園(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和北園(北京市植物園)兩個園區組成,收集植物1.5萬種(含種及以下單元),建有牡丹、睡蓮、野生蕨類植物等6個國家花卉種質資源庫。它以收集華北和東北的植物為主,擁有桃花園、月季園、海棠園、牡丹園、梅園、丁香園、盆景園等14個專類園和中國北方最大的珍稀植物水杉保育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水杉是一種先發現化石、后發現活植株的特殊物種。
除了常規的植物,國家植物園中還包含一座亞洲最大的植物標本館—國家植物標本館。其館藏標本超過600萬份,并且所有館藏標本都有可供查詢的數字化影像,為研究和學習植物學提供了珍貴的基礎材料。豐富的研究材料、深厚的學術技術、強大的科研隊伍結合在一起,讓國家植物園成為我國植物學研究的核心機構。

華南國家植物園,位于廣州。前身為國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由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院士于1929年創建。1954年,成為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1956年,建立華南植物園和我國第一個自然保護區—鼎湖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003年10月,更名為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2022年5月30日,國務院批復同意在廣州市設立華南國家植物園。同年7月11日,華南國家植物園在廣州揭牌成立。該植物園依托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設立,不僅保存有豐富的熱帶和亞熱帶植物,而且在建園過程中,增添和強化了嶺南園林的設計元素,是欣賞自然風光與人文設計完美結合的好場所。
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園,位于武漢,現有物種8000余種。武漢植物園的特色植物是以蓮花為代表的水生植物以及獼猴桃家族。武漢植物園培育出多種特別的蓮花品種,并且對蓮花形態和花色的研究居于世界領先水平。另外,喜歡水果的朋友一定要關注一下武漢植物園的獼猴桃家族,這里有國內最大的獼猴桃種質資源保存基地,而且培育出了諸多色味俱佳的獼猴桃新品種。
值得一提的是,武漢植物園的禁毒主題植物展是非常好的科普教育活動,通過讓公眾認知罌粟等毒品植物及其危害,達到宣傳禁毒知識、樹立禁毒理念的作用。
南京中山植物園,位于南京,是中國最早建立的植物園,又稱江蘇省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這里以收集和研究中、北亞熱帶的植物為核心,能看到華東區域分布的植物,園中的藥用植物及梅花等花卉資源的展示也非常有特色。
上海辰山植物園,位于上海。礦坑花園和特別的展覽溫室(含熱帶花果館、沙生植物館、珍奇植物館)是這里的特色。礦坑花園是在廢棄礦坑的基礎上建設起來的花園,是改造廢棄環境的經典案例。除了代表性景點,這里還有月季園、藥用植物園、城市菜園、春花園和觀賞草園等專類展示園。

中國科學院深圳仙湖植物園,位于深圳。這里不僅收集大量熱帶和亞熱帶植物,還擁有國家蘇鐵種質資源保護中心,在蘇鐵類植物的遷地保護和研究中建樹頗豐。除了蘇鐵,仙湖植物園還有特別的硅化木展區,可以讓參觀者感受到歷史和現實生存智慧碰撞的火花。
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園,位于昆明。云南的生物多樣性水平之高,盡人皆知。昆明植物園收集了大量云南以及云貴高原其他區域的特有植物,尤其是杜鵑花、山茶花、報春花等花卉資源,值得觀賞學習。
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位于云南西雙版納。該園是我國國內目前植物物種最豐富的植物園之一,保存植物物種數量超過1.3萬種。在這里,不僅能見到王蓮、跳舞草等代表性熱帶植物,還能感受保存完整的溝谷雨林。如果你是一個自然愛好者,來西雙版納一定不要錯過這個園子,它是國內唯一被評為5A級景區的植物園,不僅擁有豐富的物種資源,而且擁有高素質的科普導游隊伍,還有夜游等特色科普活動,值得體驗。

為何要設立國家植物園
我國地理跨度極大,地貌和氣候多樣,植被類型豐富,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有高等植物約3.7萬種,還有東喜馬拉雅、中國西南山地、印緬地區和中亞山地等4個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分布在我國境內。
隨著一南一北兩個國家植物園的建立,我國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將繼續得到穩步推進,逐步實現我國85%以上野生本土植物、全部重點保護野生植物種類得到遷地保護的目標。
未來,對于國家植物園而言,將重點收集“三北”地區鄉土植物、北溫帶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區的代表性植物及珍稀瀕危植物,共規劃收集活植物3萬種以上,覆蓋中國植物種類80%的科、50%的屬,占世界植物種類的10%;收藏五大洲代表性植物標本,覆蓋中國100%的科、95%的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