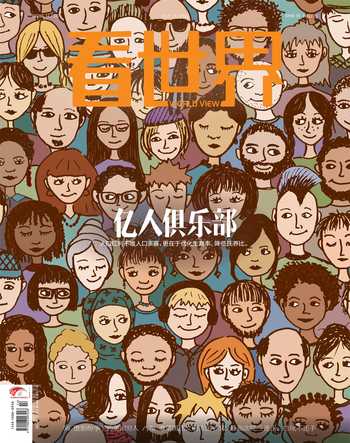“造人”迷途,何以知返?
李亞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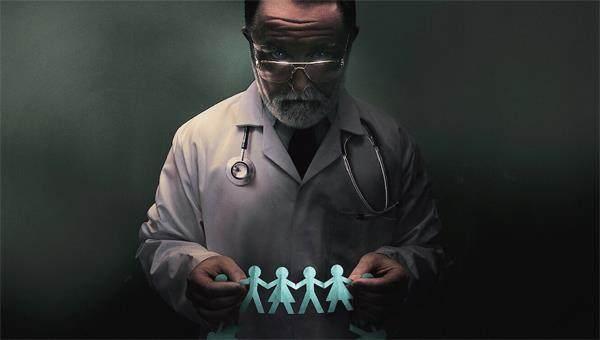
紀錄片《我們的父親》海報,婦產科醫生唐納德·克萊因
近日,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確立女性墮胎權受憲法保護的判例“羅訴韋德案”,一時間在美引起軒然大波。
隨著時代發展,女性對生育權的自主意識逐漸增強,人們對于“生殖”“繁衍”的解讀也日益變化,尤其是在科學技術的加持下,那種“聽天由命”式的自然生殖觀,逐漸顯得落伍,人們想要掌握更大的“造人”主動權。
懷上了但不想要,于是人們研發出人工流產技術,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墮胎”。而當想要但懷不上時,人們又研發出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如人工授精、體外授精、胚胎移植等。那么,諸如此類與“造人”相關的技術,是否將人類從生殖困境中解救了出來?又是否存在更大的隱患呢?
今天我們要聊的不是墮胎權風波,而是另一個因為“人工授精”,在美國引起熱議的社會事件:我們的“父親”。
我們的“父親”
今年5月,Netflix通過一部名叫《我們的父親》(Our Father)的紀錄片,揭露了一樁驚人的“造人”事件。

截至紀錄片制作完成,共有94人通過克萊因人工授精方式出生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一位名叫唐納德·克萊因(Donald Cline)的婦產科醫生在印第安納州名噪一時。他最為人稱道的技術之一,便是“人工授精”,這讓許多不孕家庭都重燃希望。于是,很多人慕名而來。
這些“人工授精”得來的小孩中,有一位名叫雅各巴·巴拉德(Jacoba Ballard)。她從小就發現,金發碧眼的自己,與家人長得很不一樣。于是在35歲的時候,她進行了DNA家譜檢測服務,卻驚訝地發現,資料庫中有7名跟自己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
根據印第安納州當時的法律,一名捐精者最多只能供精給3位女性。而現在有7位,雅各巴意識到事情有些蹊蹺。
于是,她開始展開調查,并在DNA系統中發現了越來越多的“兄弟姐妹”。她開始一一聯系這些人,終于在家族姓史中發現了蛛絲馬跡:他們的父親,很可能就是當年的婦產科醫生克萊因。
據同期診所的醫生和護士回憶,當時掌握人工授精技術的醫生屈指可數,克萊因在進行操作時,往往不讓其他人旁觀協助,只留自己和受孕者在室內。由于進行人工授精的精子樣本溫度非常關鍵,人們推斷,當時他必須在診所另一個房間自慰并射精,再即時把精液帶到診療室,注入患者體內,以提高成功率。
在記者、檢察官等參與調查之下,最終經DNA檢測,克萊因確實為雅各巴等人的父親。截至紀錄片制作完成,共有94名因他秘密捐精而出生的子女。
這個數字是令人震驚的。可怕的是,DNA檢測的資料庫中只存有參與服務的人士資料,這意味著,實際的數量可能更多。大部分通過克萊因這種人工授精方式出生的兄弟姐妹們,甚至都生活在40公里范圍之內。
然而,由于克萊因被起訴時,印第安納州并沒有相關法律支持對其定罪,對于人工授精數量也沒有強制執行的國家限制,于是最后,檢察官只能以制造虛假文書、故意誤導調查妨礙司法公正作出起訴。克萊因最終也只是被罰款500美金、吊銷醫生執照并緩刑1年。懲罰之輕肉眼可見。
更可怕的是,該紀錄片提到,根據DNA檢測系統,像克萊因這樣,用自己的精子進行人工授精的醫生,還有44名。
根據印第安納州當時的法律,一名捐精者最多只能供精給3位女性。
科學“造人”需要更加慎重
事實上,這個紀錄片只揭露了冰山一角。這個世界上因“人工授精”而產生的問題案件,時有發生。
2013年4月,英國一名50歲的神經科學家拉維奇(Gennadij Raivich)因性侵案被捕。他自訴,已經捐精多年,并使49個孩子出生。而在英國,法律規定一位捐精者最多可捐精給10位女性。拉維奇稱,控訴他性侵的女性,只是接受他精子捐贈的受益者。
2020年12月,據澳洲媒體報道,維多利亞州一名40歲的越南裔捐精者范艾倫(Alan Phan),一年之內偷偷向他人提供精子,并生下23個孩子。而根據維多利亞州的相關法律,一位捐精者一生最多可捐精給10位女性。范艾倫稱,當他發現那些女人是多么渴望要一個孩子的時候,他很難拒絕她們,并表示自己曾在一天之內捐精給3名女性。
2020年底,英國《太陽報》也報道了一位居住在美國密歇根州的104歲高齡婦產科醫生菲利普·佩文(Philip Peven),他曾在上世紀50年代的芝加哥地區做研究,并秘密捐精,導致100多名女性懷孕。
還有,2022年2月,據日媒報道,日本一位男子借捐精名義與對方發生性關系,引發雙方配偶互告對方通奸。發生性關系的契機是,捐精中心介紹雙方進行面談,雙方隨后并沒有通過捐精中心繼續,而是發生了實際性行為。日本和美國類似,對于人工授精的數量,還沒有強制執行的國家限制。

當“造人”走入迷途,這個原本被用來幫助許多不孕不育家庭擁有自己孩子的科學途徑,淪為犯罪和道德問題的隱患。不管出于何種動機,生命的出現與誕生,本不該被輕看,和如此隨意。
呼喚法律控制隱患
在人工授精中,這樣的混亂事件會帶來哪些危害呢?
首先涉及倫理問題。試想,前述案件中的雅各巴,她成年之后若在當地遇見一個相愛的人,結果發現DNA檢測出來,他們是近親,要如何面對?若雅各巴成年結婚之后,也有不孕問題,她也來接受人工授精,最后捐精者與當年母親的捐精者是同一人,該如何面對?并且,如果雅各巴的捐精者是她同父異母的兄弟,又要如何面對?
所以,為了避免出現近親倫理問題,以及隨之帶來的生理健康問題,法律應加大監管力度,對人工授精的數量進行嚴格限制。
必須提到的是,前述案件中的克萊因醫生,其實患有一些先天性的免疫性疾病。這也就意味著,從醫學的角度來說,他根本沒有資格捐獻精子。事實也證明,他的這些“兒女”中,許多都出現了相似的疾病情況。
他過多使用自己的精子進行人工授精時,也把一些遺傳病的風險帶給了下一代,而這種情況本可以避免。所以,對精子數量和質量進行嚴格篩查,本應是人工授精技術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
除了子嗣倫理問題,還有許多潛在風險,需要納入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考量,比如性別、智力、種族、外貌等的選擇問題;跨代懷孕的問題;夫妻雙方離婚后胚胎歸屬權問題,以及捐精方式是否涉及性侵問題等。
如果法律不對諸如此類的隱患進行嚴格控制,勢必會有更多匪夷所思的社會事件發生。因為我們很難用人的“理性”來衡量人的“罪性”。
2018年,在雅各巴和兄弟姐妹的合力推動下,印第安納州通過了相關法律條例,防止類似違法人工授精行為再次發生。這似乎是一個好的跡象。
而人類的生殖困境風波,可能并不會輕易結束。
責任編輯吳陽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