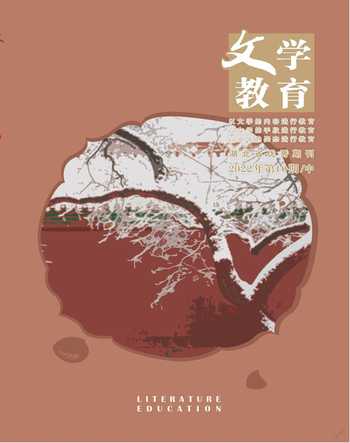同源賓語句法結構中動詞與內論元的關系
佘昱
內容摘要:本文從生成語法的輕動詞理論角度探討同源賓語句法結構中動詞與內論元的關系,并解釋同源賓語現象出現的原因。本文認為同源賓語結構是一個正常的句法結構,其題元結構本質上等于句子“Sb. have/has sth.”的題元結構。同源賓語句的出現是頭韻和內韻語音修辭的結果,是通過添加語音修辭手法來增加其語言表達效果一種語言現象。
關鍵詞:同源賓語 輕動詞 句法結構 語音修辭
同源賓語結構(Cognate Object Constructions,簡稱COC)是英語中一種特殊的語言現象,Quirk et al. (1985:750) 指出:在該構式中謂語動詞本是不及物動詞, 其后卻跟了賓語, 而且在這一類賓語中, 中心名詞在形態上與謂語動詞同形或有關聯, 在語義上重復謂語動詞所表示的動作概念,例如:
(1)Bill died a painful death.
(2)They laugh a hearty laugh.
(3)They dance a merry dance.
像die、laugh、sigh和dance這類的動詞在語義上只要求一個論元,在句子中通常不帶賓語,屬于典型的不及物動詞。但在上述例子中,他們卻能像及物動詞一樣后接賓語,這種特殊的句子結構被稱之為“同源賓語結構”,這些動詞后的名詞詞組被稱為“同源賓語”。
前人關于同源賓語的研究主要從傳統語法、認知語言學和生成語法這三個角度對其進行分析闡釋。
傳統語法主要是對同源賓語的形態、句法和語義特征進行描述。例如,Sweet(1891:99)將同源賓語結構定義為:“有時不及物動詞后面跟有一個具體相同形式的名詞,且這個名詞重復謂語動詞的語義,例如fight a good fight。”他認為同源賓語結構中的賓語名詞是由謂語動詞轉化而來,與謂語動詞在形態上和語義上相關聯,且同源賓語都是抽象名詞。Jesperson(1927)認為同源賓語是一種結果賓語,是謂語動詞行為導致的結果,他還指出同源賓語必須要有一個形容詞修飾。不同的學者對同源賓語的定義各不相同,但他們都支持同源動詞為不及物動詞這一觀點,然而并未解釋不及物動詞為什么能夠帶賓語這一現象。
隨著生成語言學的出現,學者們開始從生成語法角度對同源賓語現象進行分析,但主要集中討論同源賓語的句法地位(Jones 1988; Massam 1990; Macfarland 1995;高華、金蘇揚 2000;Kuno and Takami 2004;劉愛英2012;)關于同源賓語的句法地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Jones (1988)和高華、金蘇揚 (2000)認為同源賓語是附加語,對同源動詞起修飾作用。另一方面,Massam(1990)和Macfarland(1995)則認為同源賓語是論元,可以進行被動化、主題化和wh-位移等操作。此外,Nakajima(2006)和劉愛英(2012)將同源賓語在句法結構上分為兩類:附加同源賓語和論元同源賓語。他們從非作格動詞和非賓格動詞兩方面分析同源賓語,認為非賓格動詞帶附加語同源賓語,非作格動詞既可以帶附加語同源賓語也可以帶論元同源賓語。
此外,也有學者們從認知語言學領域對同源賓語結構進行分析,認知語言學領域又分為兩類:認知語法(Langacker 1991;屈春芳 2005)和構式語法(Kim & Lim 2012;匡芳濤、曹篤鑫 2013)。在認知語法方面,Langacker(1991:363)闡述了同源賓語結構的特點,即賓語的中心語名詞是謂語動詞的名詞化,表明了賓語和謂語動詞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在同源賓語結構中,同源賓語是一個事件賓語。屈春芳(2005)也從認知角度對同源賓語結構進行分析,發現同源賓語有以下幾個認知特征:對主語的歸屬性、依賴性、顯著性和抽象性,他認為這些認知特征能夠有效得區分同源賓語結構與非同源賓語結構。從構式語法的角度進行研究,Kim & Lim (2012)認為同源賓語結構同單賓語結構一樣有兩個論元,但是句法和語義映射之間存在不匹配現象。匡芳濤、曹篤鑫( 2013)則認為同源賓語結構是一種特殊的單賓語結構,表達“致使-存在”意義的單賓語構式對這些不及物的謂語動詞進行構式壓制, 使其獲得額外的“致使-存在”意義, 并具有了攜帶同源賓語的能力。
綜上所述,對于同源賓語結構這一特殊現象,國內外學者主要從傳統語法、認知語言學和生成語法這三個角度對其進行了系統性研究,但都認為同源賓語結構是一種特殊的句法結構。本文認為同源賓語句并非是特殊的句法結構,而是正常的句法結構。本文擬從生成語言學的輕動詞理論出發,對同源賓語結構展開分析討論,重點討論同源賓語句法結構中動詞與內論元的關系,并從語音修辭的角度解釋同源賓語現象的出現。
一.同源賓語句的句法結構
引言中的例句都屬于同源賓語句,但這些句子在選擇賓語是還有不同之處,例(1)和(2)中的動詞die、laugh只能接受同源的名詞作為賓語,除此之外不可以接受其他的名詞作賓語。而例(3)中,動詞dance除了能接同源名詞dance外,還能接其他名詞作賓語,如:
(4)Mary danced the Irish jig.
例句中的Irish jig為名詞dance的下義詞,即動詞dance不僅可以接同源名詞還可以接同源名詞的下義詞。梁錦祥(1999)將這兩種情況分為同源賓語結構和及物化賓語結構,本文中只討論真正的同源賓語結構。
1.同源賓語結構有正常的題元結構
本文認為同源賓語句并非是一種特殊的句法結構,而是與單賓語結構一樣的正常句法結構。同源賓語句的題元結構本質上等于句子“Sb. have/has sth.”的題元結構,例如:
(5)They lived a happy life.
(6)I dream a sweet dream.
如上述例子所示,表層語義上,例(5)表示“他們過著幸福的生活”,但我們可以挖掘出其深層語義為:“他們有著一個幸福的生活”(They had a happy life)。例(6)表層語義上表示“我做了一個甜美的夢”,其深層語義為“我有一個甜美的夢”(I have a sweet dream)。我們可以認為同源賓語句“They lived a happy life”和“I dream a sweet dream”的題元結構本質上等于句子“They had a happy life”和“I have a sweet dream”的結構樹形圖。
2.同源賓語句法結構中輕動詞的引入
丹麥語言學家Jespersen(1949:117)在解釋V+NP結構時提出“輕動詞”(light verb)這一概念,他認為在這一結構中動詞在語義上無法承擔謂語功能,語義內容較少,常見的輕動詞主要有have, do, make, take, get等,這些輕動詞組成的動詞短語是由輕動詞和補充謂語語義不足的名詞所構成,且該結構中的賓語是由原為動詞通過零形式轉化生成的名詞。上文講到同源賓語句的題元結構與單賓語結構一樣是正常的題元結構,其本質上為“Sb. have/has sth.”,根據前人對同源賓語結構的定義可知,同源賓語是由謂語動詞轉化而來,與謂語動詞在形態上和語義上相關聯,這與輕動詞短語結構一樣,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同源賓語句中的“V+NP”與Jespersen(1949)所提出的輕動詞短語結構本質上是一樣的。
在1.部分我們提到的例句“They lived a happy life.”的題元結構本質上為“They had a happy life”,在該句中我們把“had”視為一個正常的實義動詞,能夠給名詞“They”和名詞短語a happy life分配題元角色,給名詞短語“a happy life”授予賓格。但現在實義動詞“had”已經被視為一個輕動詞了,句子結構中也相應增加了vP這一成分,輕動詞“have”占據了v的位置,V的位置也就相應空缺了。
首先,從題元結構來看,該句中有兩個題元角色,即外部論元 “They”和內部論元“a happy life”。Chomsky(1981:40)認為不管是動詞的內部論元還是動詞的外部論元,都是由動詞選擇的,但內部論元可以由動詞直接題元標記(θ-mark),而外部論元則由動詞間接題元標記,外部論元的題元角色要由整個動詞短語指派。然而現在句子“They had a happy life”中的“had”已經被視為一個輕動詞了,題元角色無法獲得。Chomsky(2000:102)后來又指出外部論元由輕動詞選擇,那么現在外部論元“They”的題元角色已經有了,由句子中的輕動詞“have”分配,但內部論元“a happy life”的題元角色卻無法獲得,這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地方。其次,從格的授予來看,Chomsky(1995:111)提出格鑒別式,即每個有語音形式的 NP 都必須有抽象格(abstract Case)。每個名詞短語都必須得到格,句中若有無格名詞,則句子不合法。例句“They had a happy life”中的名詞“They”由T賦予主格,名詞短語“a happy life”的賓格由動詞賦予,而在該句中只有輕動詞“have”,無法給“a happy life”賦予賓格,因此名詞短語“a happy life”無法獲得格。有語音形式的名詞短語“a happy life”,無法獲得格,這不符合格鑒別式的要求,因此句子不合法。為了解決上述的兩個提出的論元問題和格問題,我們可以從名詞“life”復制一個動詞“live”到V位置,這樣名詞短語“a happy life”就有了題元角色和賓格。上文中我們提到在“V + NP”這一結構中賓語是由原為動詞通過零形式轉化生成的名詞,那么可知“They had a happy life”句中的名詞“life”是由其相對應的動詞“live”通過零形式轉化而來,當該句的句法結構V位置缺少動詞時,我們可以從名詞“life”復制一個動詞“live”到V位置。動詞“live”填充了V后,整個句子就有一個正常的題元結構了,題元角色的分配和主格、賓格的授予也能夠正常進行。例句的派生過程如上圖所示,從名詞“life”復制過來的動詞“live”移位到v位置與輕動詞“have”合并,接著再移位到T位置與時態語綴-ed合并得到動詞“lived”;主語“They”從原來的Spec-VP移位至Spec-TP。經過這么一系列句法操作,句子“They had a happy life”變成了“They lived a happy life”,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同源賓語句并非是一種特殊的句法結構,而是與單賓語結構一樣的正常句法結構”想法.
二.同源賓語句:語音修辭的作用
對于英語中同源賓語現象的出現,我們可以從語音修辭的角度對其進行解釋。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是語言存在的外部形式,沒有語音就沒有有聲語言,英語語音諸要素的選擇運用,可以達到言語表達中的不同語用效應,即語音修辭(劉世理 1997)。語音修辭與其他修辭手法的相同之處在于,一樣都是對語言進行提煉,以達到超出語言表層結構的特殊意境,賦予語言更豐富的內涵。不同之處在于,它是利用語言中的發音、音節、語調等自然因素,形成一定的語音修辭格,表現出語言符號的深層語義,即語音修辭意義。常見的語音修辭主要有頭韻、尾韻以及內韻等。頭韻指一組詞、一句話或一行詩中若干詞的詞首重復相同的一個字母或語音, 形成一種詞首的韻律。尾韻指相同詞尾輔音在一組詞、一句話或一行詩中重復出現,具有悅耳的節奏感。內韻指詩行內某個詞同行尾那個詞同韻的現象,最常用于詩歌,內韻還用于英語諺語中,押內韻的諺語具有回環和諧的音樂美, 讀起來瑯瑯上口, 聽起來悅耳, 并且易記易傳。本文討論的同源賓語句也同樣運用了頭韻以及內韻的修辭手法,比如例句(5)“They lived a happy life.”中的謂語動詞“lived”和同源賓語“life”押頭韻。在同源賓語例句(2)“They laugh a hearty laugh.”、例句(6)“I dream a sweet dream.”中,謂語動詞“laugh、dream”分別與同源賓語“laugh、dream”押內韻。
通過上文的分析,同源賓語句的題元結構本質上等于句子“Sb. have/has sth.”的題元結構。同源賓語句與一個正常的句子“Sb. have/has sth.”相比,因為增加了頭韻以及內韻的語音修辭手法,其語言表達更加鮮明且生動有力,語音更整齊和諧,富有節奏感和旋律美。語音是語言的外衣,它賦予意義以感官效果,是意義得以流動的最原始的載體(張娜 2008),語言主要靠語音來實現它的交際功能,因此對語音的修辭及其重要。語音修辭通過語音的和諧以及周期性重復來增加旋律美、音樂性,從而強化表達效果,同源賓語句也是通過添加語音修辭手法來增加語言表達效果的案例之一。
本文從生成語言學的輕動詞理論出發,對同源賓語結構展開分析討論,認為同源賓語結構并非是一種特殊的句法結構,而是與單賓語結構一樣的正常句法結構。同源賓語句的題元結構本質上等于句子“Sb. have/has sth.”的題元結構。本文從題元角色的分配與格的授予兩方面進行分析,由于句子“Sb. have/has sth.”中的“have/has”為輕動詞,占據vP位置,無法分配題元角色和授格,因此需要從同源賓語復制一個動詞過來用以順利進行題元角色的分配和格的授予,在經過一系列的句法操作后,得到句子“Sb. have/has sth.”的S-結構,即同源賓語結構。接著,從語音修辭的頭韻和內韻解釋英語中同源賓語結構現象,同源賓語句是通過添加語音修辭手法來增加其語言表達效果一種語言現象。
參考文獻
[1]Chomsky, N.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M]. The Pisa Lectures. Dordrecht: Foris.
[2]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M]. Cambridge: MIT Press.
[3]Chomsky, N.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A]. In R. Martin et al. (eds.), Step by Step[C].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Cambridge, MA: MIT Press. 89-155.
[4]Jespersen, O. 1927.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5]Jespersen, O. 1949.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Ⅵ, Morphology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6]Jones, M. 1988. Cognate objects and the case-filter[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4 (1): 89-110.
[7]Kim, J & J. Lim. 2012. English Cognate Object Construction: A Usage-based,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J].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18 (3): 31-55.
[8]Langacker, R.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2: Practical Applicatio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9]Massam, D. 1990. Cognate objects as thematic objects[J]. Canad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5 (2): 161-190.
[10]Macfarland, T. 1995. Cognate Objects and the Argument/ Adjunct Distinction in English [D]. Ph. D.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1]Nakajima, Heizo. 2006. Adverbial Cognate Objects. Linguistic Inquiry, 37(4), 674–684.
[12]Quirk, R. S. Greenbaum, G. Leech & J. Svartvik.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London: Longman.
[13]Sweet, H. 1891. A New English Grammar[M]. Oxford: Clarendon.
[14]高華、金蘇揚,2000,無格的同源賓語——最簡方案內特征核查得出的結論[J].《外語與外語教學》 (06):62-66.
[15]匡芳濤、曹篤鑫,2013,同源賓語構式的構式壓制與詞匯壓制闡釋[J].《山東外語教學》34(03):22-28.
[16]劉愛英,2012,論英語同源賓語的句法地位與允準[J].《外語教學與研究》44(02):173-184+318.
[17]梁錦祥,1999,英語的同源賓語結構和及物化賓語結構[J].《外語教學與研究》(04):23-29+78.
[18]劉世理,1997,論英語語音的修辭功能[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01):108-111.
[19]屈春芳,2005,同源賓語結構的認知特征[J].《外國語言文學》(03):162-165+161.
[20]張娜,2008,漢語語音修辭的審美價值[J].《黑龍江科技信息》 (34):204+82.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