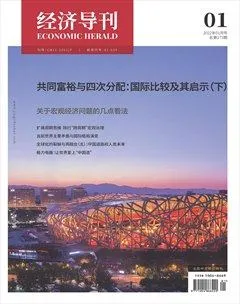日本經濟現狀與中日經貿關系展望
劉軍紅
日本經濟長期低速增長
冷戰結束后30年,日本經濟長期處于停滯狀態,被稱為“失去的30年”。過去30年的每個10年平均增速分別為0.3%、0.3%和0.7%,可謂“貼著地皮增長”,堪稱“零增長”。GDP增長率的低下與物價、利率的長期低下,并稱為日本經濟的“三低”,也構成了“日本化”的三個典型特征。
2016年以后,日本央行將長期低下的利率限定在0%左右(10年期國債收益率鎖定為0%),導致預期投資收益率長期低下。企業不投資,抑制設備投資、抑制研發投入,潛在生產率低下,潛在GDP增長率長期處于1%以下(目前為0.7%),在物價長期低迷背景下,日本經濟呈現“通縮化”現象。
擺脫通縮是日本政府的長期任務。“安倍經濟學”使用了大膽的金融政策,輔之以機動靈活的財政政策,積極擴大國家債務;央行無限購買國債及企業股票基金,導致央行資產膨脹、日元長期貶值。新冠肺炎疫情中,在國際資源能源價格上漲背景下,日元貶值加劇進口物價上升。出口物價則因企業面臨全球競爭難以輕易提升,導致日本交易條件惡化(出口物價高于進口物價)。
鑒于新世紀以來日本企業海外生產比率達30%,日元貶值對于企業出口的刺激效果減弱,良性效果稀薄,呈現更強的負面效果。由此,面對國際物價上升、美歐央行金融政策回歸正常化傾向,日本央行如何調整金融政策關乎其經濟增長。
中日經濟具有穩定深度發展的基礎
從貿易方面看,自2009年中國首次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國以來,至今,日本的最大出口地在中美之間輪動,中美不分伯仲,堪稱日本的兩大出口要地。在進口方面看,自2002年以來,中國持續保持日本最大的進口來源國地位,且從中國的進口規模逐年擴大,在日本總進口中的占比約達23%左右,逐漸與美國拉開距離。這意味著日本對中國制成品的依賴在逐漸增強,對美國制成品的依賴逐漸減弱。
中日產業間始終保持著緊密的相互依賴關系。中國入世之初,日本對華出口的九成為生產設備、核心零部件和中間產品。而今,這種跨國產業鏈關系仍在保持并得到加強。從日本財務省貿易統計數據看,有色金屬、半導體制造裝置、集成電路、電子零部件,及電子計數儀器等對華出口逐年擴大,并構成中國出口產品的核心要素,其比例關系大致為13:100,即每進口13個單位的日本生產要素,可產出100個單位的中國出口產值。
與此同時,中日貿易結構日漸表現水平分工特征,如在一般機械、電氣機械和原料、化工原料等類別中,中日相互占比日趨接近,如“一般機械”,互占23%左右;“電氣機械”接近27%,中國出口占比更多一些。這意味著中日產業內貿易快速發展,形成了彼此不可或缺的緊密產業鏈關系。
這與日本始終保持高水平的對華直接投資有關。中國入世后,日本企業對華投資掀起新的高潮,這個潮流持續到2012年中期,這個過程既體現了對入世后的中國經濟的高度預期,也反映了對北京奧運會及上海世博會的高度期待,同時也與日本“3?11”地震后企業分散投資,轉移產能,規避風險有關。之后,日本企業投資開始向東南亞轉移,在增速上呈現超過對華投資的勢頭。
在中美貿易摩擦和疫情疊加背景下,中日貿易結構并未發生大規模改變,表明日本對華投資,及其在華產業鏈布局也未發生顯著改變。對東南亞的投資增加,可謂仍保持在過去的延長線上。中國市場的投資魅力、投資收益仍可抵消所謂的“經濟安全”考慮。中日產業關系仍具有穩定深化發展的條件。以此為基礎的中日關系也具有保持穩定發展的條件。
(編輯 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