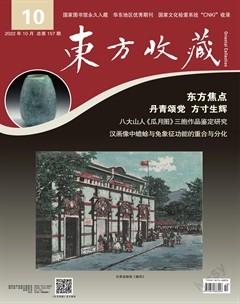凌源市博物館藏三方金代銅印



摘要:金代軍府官印歷史遺存較多,與其臨時設立的軍府機構較多有關。臨時軍府機構的頻繁置廢,增加了對官印管理的難度,也與其對官方印信較為松弛的管理相關。金代官印以九疊篆為內容,以簡潔的銅質為載體,均為典型特征。金代施行的軍府制度,既成就了女真的迅速崛起,也為其敗亡埋下了伏筆。
關鍵詞:凌源市博物館;金代官印;軍府制度
官方印璽的出土和面世,不僅可以補足正史之闕疑,也是古代藝術的展現。現藏于凌源市博物館的三方金代銅印,均為上世紀70年代在凌源市境內出土的,其文字內容“與漢字的文化史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與同步發展的態勢”[1],乃文字傳承的特殊形態。此三方銅印均為軍府官方印璽,《金代官印集》[2]已有收錄,今做簡考。
一、三方金代銅印
金代銅“元帥都監府印”(圖1),1977年出土于凌源市河坎子鄉。印臺(印身)近似正方形,縱長9.7、橫寬9.6、印身厚(印墻高)1.6厘米;印通高4.6厘米,長方形柱狀立鈕(或稱之為板鈕),鈕高3厘米;印面陽刻九疊篆“元帥都監府印”兩行共六字,每行三字;印鈕上部鏨一“上”字,以示印文方向,便于用印端正,印臺上面右側刻“元帥都監府印”邊款,便于識別取用;印為黃銅質地,重1272克。該印不見磕損,鑄造規矩,印面平整,文字刻鑿深入,印文舒朗,邊墻厚重,朱文和留白搭配和諧,風格端莊,具有典型的官印氣息。
金代銅“都統所印”(圖2),1975年出土于凌源市佛爺洞鄉小河西村。印臺正方形,長、寬均為7.3厘米,印墻高1.6厘米;印通高5.2厘米,扁楔形立鈕,鈕高3.6厘米;印面陽刻九疊篆“都統所印”兩行共四字,每行兩字;印鈕上部鏨一“上”字,指示印文方向,便于正確用印;印為黃銅質地,重809克。該印外形方正,陽文筆道粗獷外放,留白較少,文字刻鑿淺顯,配以中等印邊,從而呈現內收的氣勢,收放之間,達到總體的平衡。
金代銅“都軍司印”(圖3),1979年于凌源市萬元店鎮無白丁村出土。印身近似正方形,縱長6.5、橫寬6.4、印墻高1.1厘米;印通高3.2厘米,長方形柱狀立鈕,鈕高2.1厘米;印面陽刻九疊篆“都軍司印”兩行共四字,每行兩字;印鈕上部鏨一“上”字,指示印文方向,便于正確用印;印為黃銅質地,重401克。該印面為窄邊陽文,邊外四周有留白,印文筆道纖細,留白較多,近于鐵線文。
這三方銅印均為金代軍府系統官印,金朝遺留下大量的官方印信,在中國歷史上尤其獨特。一般來說,官方印信歷任傳遞使用,改朝換代或行政區劃變更,皆由朝廷收回熔毀,極少流落民間和隨葬,官方對印信的嚴格管理,體現官方印信的權威性。而有金一朝,僅統治北方一區,歷經百余年的歷史,民間流落有大量官方印信,為歷朝特例。1991年出版的《金代官印集》收錄金代官印554方,《吉林出土古代官印》[3]收錄金代官印53方,2000年出版的《遼海印信圖錄》[4]收錄東北地區存世金代官印132方。隨著新發現的金代官印不斷涌現,2007年景愛先生整理編次《金代官印》[5]收錄金代官印915方,陜西、山東、上海等地文博機構所藏金代官印也得到學者的重視,收錄于相應的著作中,“時至今日(2019年),留存印譜或發現實物的金代官印數量已在900方以上”[6],以現有統計來看,這一數字可能要翻倍才行。
二、金代官印的歷史源流
印信,初為璽印,用以鈐壓封泥,最早可追溯至戰國時期,《左傳》中的“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7]已有用印的記載,是為符契的發展,也是印信的濫觴期。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頒令天下只有帝王、皇后印信可稱為“璽”,百官以下則稱“印”,印信開始兼具身份憑證和權力的象征,兩漢因之。隨著造紙術的完善和紙張質量的提高,公文鈐印成為朝廷公文傳遞的必要步驟。至此,官印成為朝廷權力的象征,是統治力量所能到達轄域的體現。
官印乃朝廷權力的象征,“作為政府機構頒發給官員的一種政治憑證,是對其權力的肯定和認同。”[8]每一個穩定政權對官印鑄造都有特定的規制,印文受秦代璽印的影響,篆文一直流傳于官方印信中,期間雖有諸書體印文的出現,但篆文一直占據正統的位置,尤其是九疊篆成為官印專用體。“九”是古人認為的數理之終極,言筆畫曲折繁復折疊之多,以達到曲折平滿的印面效果。九疊篆用于官印,唐代流行,至宋代達到鼎盛。遼金受宋代文化的影響,既是出于模仿,也是出于防偽,金代官印幾乎全為九疊篆印文,或朱文或白文,前述三方金代軍府銅印即如此。
以女真族為主體,兼統渤海、契丹、漢人,完顏氏建立金朝,完顏旻收國、天輔間金朝初創期,官方印信使用雜亂無章,宋、遼舊印依然通用。《金代官印背后的金末困局》認為“金朝立國之初,各種官制尚未完備,官印制度也比較混亂,甚至還因襲盈歌時期的信牌舊制”,此時期,萬戶授金牌,猛安授銀牌,謀克、蒲輦授木牌,符牌和印信并行,這里的印信包括宋、遼的舊有官印。天輔間,以攻克遼中京(今寧城縣天義鎮西)始至正隆(1156—1161)初年,金代官印頒授和使用逐漸規范。正隆元年(1156)海陵王當政,大力對朝廷體制進行全面改革,“(正隆元年正月乙丑)罷中書門下省設尚書省”[9]。故《金代軍事制度及軍印研究》[10]將金代軍府印信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是妥當的。金代官制等政治治理體制大量吸收宋、遼的成熟做法,沿用宋遼院、臺、府、司、寺、局、所官制等級體系,并御制對應官印品級尺寸,由禮部統一鑄造。初因統一鑄造,無各路官印區劃前綴,以天干嵌入印文以示區別,后隨著金朝疆域不斷南擴,設立南方諸路,天干十字不能滿足制印的需要,始用千字文嵌入印文,使得各路、諸府、諸州官印得以有明晰的區別。
官印發展到金代,質地從歷史上的金、銀、玉、銅,且在玉印占較大比例的情況下,逐漸定位于銅印;外形上在經歷了由簡到繁再由繁到簡的過程,印鈕從圓鈕、橋鈕、瓦鈕、鼻鈕,到諸如龍、天祿、赑屃、虎等神獸,金代官印逐漸統一于板狀、長方形柱狀、楔形、扁楔形,大為簡潔;印鈕穿孔消失,由拴系攜帶變為印盒攜帶。
金代官印常帶邊款、題記。前文元帥都監府印,印鈕右側刻“元帥都監府印”,方便持印者識別不同的印章。許多官印于印側刻鑄造單位、鑄造年代,以說明該印章的來源;印鈕上鏨“上”或“┸”,來指示印文的朝向,以方便用印者能夠正確用印,不至于用印顛倒。
三、金代軍府體制
女真族起于北方,同早之的遼國和晚之的蒙元政權一樣,都是從文明程度較低的游牧階段的奴隸社會開始,在憧憬中原地區高度發達的文明和富庶中覺醒,在充分吸收中原文明成分后,迅速崛起。女真族崛起之前,直到完顏阿骨打時期,政治體制實行的是集體領導的勃極烈制。根據王震中先生的“邦國—王國—帝國”理論[11],此時的女真(氏族),處在介于邦國和王國之間的過渡狀態。自猛安謀克的全民皆兵或說是兵民合一的民族治理體制出發,此時實行集體領導的勃極烈五人共議政事,符合摩爾根描述的“野蠻時代”軍事民主制社會架構,只是在周邊大量高等級文明存在的情況下,中原文明的成分迅速地被吸收、運用。勃極烈制社會體制快速演變為王權國家,此以完顏阿骨打建國為標志,年號收國。
猛安謀克制,是女真崛起的軍事基礎。初期約一百戶為一謀克,謀克相當于百夫長;一千戶為一猛安,猛安相當于千夫長;猛安之上有萬戶。至完顏阿骨打時期(1114年),“初命諸路以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12]此時,雖處立國之前夜,但能夠說明,其統治的人口有大幅度增長。
“收國元年十二月,始置咸州軍帥司,以經略遼地,討高永昌,置南路都統司……每司統五六萬人。又以渤海軍為八猛安。凡猛安之上置軍帥,軍帥之上置萬戶,萬戶之上置都統。”[13]這說明金代軍府制度極具變化,會根據現實需要,臨時設立相應的軍府機構,使得軍府機構的設立具有目的性和靈活性,這大概也是金代早期軍力強盛的原因之一。“(收國)三年,以伐宋更為元帥府,置元帥及左、右副,及左、右監軍,左、右都監”[14],至此,金代元帥府成為最高軍事統領機構,形成或明或暗,與勃極烈五人共議制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傳承性的七人統軍模式,這也許就是清初八旗議政的淵源。應該注意的是這里所說“軍帥”與“元帥”的區別。前文所說“元帥都監府印”,在時間上必然在收國三年之后鑄造,參照其鑄造精良程度,應該在海陵王當政期間鑄造,因銅印所能提供的其他信息較少,其具體為哪路的元帥都監府,還有待進一步考察。對照此前發現的“上京路元帥都監府印”為金熙宗時期鑄造,該印較“上京路元帥都監府印”鑄造更為精良,筆者判斷該印鑄造于海陵王當政期間。
都統始于前秦,《晉書》云:“(太元八年,晉將伐苻堅,苻堅大舉征兵)良家子至者三萬余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建威將軍、少年都統。”[15]此時都統為臨時性軍事統領,這一設置歷經南朝、隋唐、五代皆然。至金代初年,都統仍為非常設性軍事頭目,金代逐漸推行都統官。《金史·卷四十四》載:“(正隆)六年,南伐,立三道都統制府及左右領軍大都督”,都統由此成為常見的軍事機構,但其設立依然是有相對應的特設軍府機構,本文所說的“都統所印”就是此時產物。對比《錦州市博物館收藏的金代銅印及初探》收錄的“都統府印”[16]、《義縣文物保管所收藏一枚金代銅印》介紹的“都統府印”[17]、《遼寧鐵嶺地區發現兩方金代銅印》介紹的“都統之印”[18]、《四方金代銅印見證軍事編制》介紹的“都統所印”[19],都是這一時期的都統印信,但印文不同,說明金代軍府官印的鑄造尚存在較為混亂的情況。
總的來說,都軍司作為金代地方軍事機構,是駐守府鎮地方的常駐軍事力量,側重于維持新征服地區的地方治安,完備的都軍司設指揮使一人,下設軍典二人、公使六人。都軍司指揮使品秩正七品,下轄少量軍兵。
參考文獻:
[1]劉玉玲.金代“窟忒忽達葛謀克印”考辨[J].北方文物,2019(02):78-81.
[2]景愛編.金代官印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3]張英,任萬舉,羅顯清.吉林出土古代官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4]王綿厚,郭守信主編.遼海印信圖錄[M].沈陽:遼海出版社,2000.
[5]景愛,孫文政,王永成編著.金代官印[M].北京:中國書店,2007.
[6]葉帥.金代官印背后的金末困局[J].黑河學院學報,2019,10(10):187-188+190.
[7]左傳[O].閔齊伋明萬歷四十四年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數字圖書,第七冊·襄公下:52.
[8]任永幸.金代官印研究述評[J].理論觀察,2019(09):97-99.
[9][元]脫脫等.金史·卷五[M].北京:中華書局,1975:106.
[10]任永幸.金代軍事制度及軍印研究.[D].吉林師范大學,2020.
[11]王震中.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于王權的形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59—66.
[12][元]脫脫等.金史·卷二[M].北京:中華書局,1975:25.
[13][元]脫脫等.金史·卷四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75:1002.
[14][元]脫脫等.金史·卷四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75:1002.
[15][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一百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75:2916—2917.
[16]劉鱺.錦州市博物館收藏的金代銅印及初探[J].遼金歷史與考古,2009(00):368—369.
[17]劉劍.義縣文物保管所收藏一枚金代銅印[J].北方文物,1999(01):54.
[18]馬洪路.遼寧鐵嶺地區發現兩方金代銅印[J].考古,1983(09):843.
[19]柳燕,衣文聰.四方金代銅印見證軍事編制[J].東方收藏,2016(05):54-55.
作者簡介:
韓波(1973—),女,漢族,遼寧凌源人。大學本科學歷,凌源市博物館中級館員,研究方向:遼金文物藏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