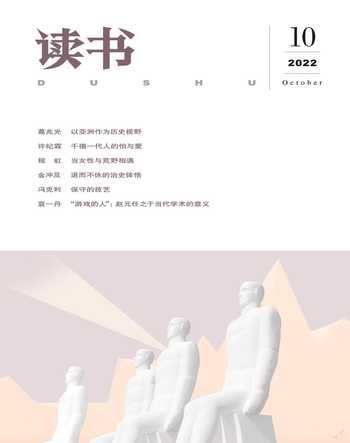天平的兩端
許璐
基督教文化與儒家文化作為東西方文明體系獨立發展出的先進文化,在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碰撞中成為雙方的代表。因長期在各自地區處于領先水平,基督教文明同儒家文明都對自身有著極高的認同感和自信心。
十四世紀末,伴隨著元帝國的覆滅,不僅曾經在“蒙古和平”庇護下暢通無阻的東西方陸路交通中斷,東方新興的明王朝也終結了曾經寬松的宗教政策,西方教士在華的活動受到極大限制。但與此同時,新航路的開辟激發了西方人的冒險精神,于是雖然之前一個世紀的努力徹底荒廢,且傳教已變得愈發艱難,西方傳教士仍然希望尋找到新的方法,深入中國,傳播福音。
十六世紀,為應對宗教改革對天主教會的沖擊,教會內部改革派人士創建了耶穌會。較舊有的天主教修會而言,耶穌會風格更加開放,為重振教會的榮光,他們將希望寄托在對海外全新教區的開拓上,神秘而富庶的遠東地區自然尤為其所關注。從羅耀拉到沙勿略、范禮安、利瑪竇,傳教士們為了實現在華傳教的目的,摸索出了一套以文化適應為核心的在華傳教方針。而在應對外來文化的過程中,中華文明逐漸產生出了數種不同的應對態度。其中全盤接納派與全盤否定派成為天平的兩端,兩廂對立。當然,在兩端之間還有一部分士人,主張“會通”,使西方文明“為我所用”。明末,以徐光啟等為代表的部分士大夫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一方面堅持對中華文明的認同與熱愛,另一方面也對外來文明持開放態度,與秉持著文化適應政策的傳教士相互交流,東西方文明在這一時期和諧互動,達成了平衡狀態(陳曉華:《十八世紀中西互動:學術交流與傳承》)。但遺憾的是,平衡最終沒有能夠維持下去,天平逐漸倒向了持全盤否定態度的一端。
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傳教士湯若望接掌欽天監,成為中國首位洋監正,此時在欽天監中居于要職的教士除湯若望外,還有李祖白等加入了天主教的中國籍教徒。因教會強烈的傳教企圖,由教士們主導的欽天監在常規的功能之外,逐漸成為一個奉教機構,這種情況引發了中國保守士人的強烈不滿,康熙歷獄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爆發的。而引發康熙歷獄的直接原因,是一名叫作楊光先的士人的上疏。
楊光先字長公,生于明萬歷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家族世襲新安衛副千戶這一武職。眾所周知,武職對承職者的文化水平并沒有很高的要求。且根據楊氏家譜和楊光先的自述,他的近三代親長,以及他個人都沒有任何的科舉經歷。可以想見,楊光先并沒有接受較系統、完備的儒學教育,亦即他對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明的理解與認識是比較淺層、初級的。明崇禎年間,本應在戍地任職的楊光先遵照父命,將家族世襲的武職交給弟弟楊光弼后,選擇入京謀生。當時的明王朝外有后金皇太極虎視眈眈,內有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早已風雨飄搖,亂象叢生。楊光先入都后,于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兩度公開上疏,稱溫體仁、陳啟新、劉之鳳等為“奸佞”,痛陳奸邪誤國。他本人還親自到正陽門外,與陳啟新當面辯論對峙。他的諫言并未被接納,還因干政而被判流放,但他以布衣之身,抬棺死劾朝臣的行為,不僅在社會輿論中贏得了廣泛的同情,還為他博得了“敢言”的令名。
清王朝建立后,楊光先再次從家鄉來到京城。在此期間,他眼見湯若望受順治帝恩寵,于是先后寫下《摘謬論》《選擇議》《辟邪論》等文,并多次赴有司控告湯若望等人借歷法行邪教,以左道之學,冀望謀奪中國。但因湯若望圣眷正濃,楊光先的陳詞未被受理。康熙三年(一六六四),以李祖白《天學傳概》的刊行為引,楊光先再次發難,痛斥教士無父無君,實為亂臣賊子,意在暗中竊取中國正朔之權,去尊崇西洋,毀滅中國圣教,而這些事都關系著中國萬古綱常,必須盡快誅滅他們,制止他們的言論,并將所有物證全部交給禮部。康熙歷獄,就此拉開帷幕。經過一年多的審理,湯若望、南懷仁、李祖白等欽天監教士都被論罪。其中南懷仁被流放,李祖白等五人被斬,湯若望雖免死,但最后病亡獄中。此后,楊光先被任命為新任欽天監監正,但楊光先確實沒有管理欽天監、制定歷法的學識與能力,最終淪為新舊勢力權力斗爭的犧牲品,被罷免后死于歸鄉途中。
可以說,無論是明季的上疏,還是清初以“華夷之防”為名的上疏,楊光先都是以大義為綱,卻沒有在具體實踐層面提出建設性意見或是改良辦法。在以“積極入世”為特征的儒家思想體系中,楊光先的做法顯然是不夠通達的,特別是在對傳教士的抨擊中,所謂“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楊光先:《日食天象驗》)更暴露了他思想的局限性。
關于引發楊光先上疏的《天學概論》一書的作者李祖白,他的生平在史籍中記載不多,而從稀缺記載中還原出的歷史真實,仍有一些戲劇性的地方。作為斗爭雙方的楊光先與李祖白,實際上是有一些相似性的,比如他們都是受到了不完全儒學教育的中國人,即他們都對東方文明理解不深,理解的片面讓他們分別選擇了天平的兩側,在應對中西文化交流時走向了兩個極端,這種片面與極端,不僅招致個人命運的悲劇性結局,也為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帶來了陰霾與波折。
李祖白字然真,教名約翰。明末,李祖白已跟隨湯若望在歷局任事,清朝建立后,他繼續在欽天監擔任夏官正一職。李祖白是湯若望的學生,作為傳教士在中國發展的本土教眾,他對西方宗教理論體系完全服膺,其宗教理念較徐光啟等更為激進,譬如同樣是將中國的歷史神話體系與西方宗教體系相結合,利瑪竇、徐光啟等人將宗教中的“神”比附為中國人概念中的“天”,而李祖白則在《天學傳概》中直接翻譯了上帝創世說,將伏羲等中國之祖視為基督耶穌的后人,認為就算最早的耶穌子孫在中國不屬于伏羲部族,也必定比伏羲部族還早。耶穌在中國的子孫是中國最早的人種。很顯然,這種說法極大觸怒了中國士大夫群體。楊光先就尤其視之為妖言,責罵李祖白堂而皇之將中國人視為西人之后,是悖亂人倫、以夷變夏,蘊含顛覆之心。實際上不只當時的楊光先等認為李祖白的論調是惡語,即使到西學東漸思潮高漲的近代,《天學傳概》依然被視為極端,遭到批判。
而從另一角度看,李祖白的“大膽”正說明了他對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明的無知,以及對東西方文化的認識都缺乏理性與深度。李祖白雖是被稱為“生儒”的中國人(徐光啟:《新法算書》),實際既不是“生員”又不是“儒生”,作為湯若望的門人,他的思維體系已經完全天主教化。同楊光先不同,雖然同樣對儒學一知半解,楊光先稱儒學為“圣教”,對儒學持尊崇態度,李祖白則對儒學極為疏離。而對比他對外來宗教的狂熱態度,這種對本民族文化的漠視疏離更加令人側目,并最終為他帶來殺身之禍。
與徐光啟相比,李祖白對東西方文明的認知格局是狹隘的。徐光啟所持的“天儒結合”的理論前提,是堅決地將中華文明作為根基,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吸納外來優秀文化,以西輔中,而非削足適履,鄙棄本民族文化,一味迎合、適應西方文化體系。在他的行為和態度中,既能體現中華民族文化開放包容的自信態度,也展現了儒家文明自我調整、自我更新的能力,這也是中華文明能夠歷經數千年風雨依然生機勃勃的根本原因。
楊光先和李祖白作為同時代的中國人,在應對以基督教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挑戰時,他們的選擇走向了天平的兩端,一方全盤否定,一方全盤接納,從歷史的發展來看,這兩種極端的態度不僅招致了他們個人命運的悲劇性結局,也沒有使中西方文化交流走上正確的道路,最終為禍甚遠。以古鑒今,當今的中國堅持越發展越開放的原則,而在開放之中,不可避免地要應對外來文明持續性的沖擊。為此,必須認識到何為應對外來文明、與外來文明開展交流競爭的正確態度,即不去選擇站在非此即彼的天平的任何一側,而是在對本民族文化深入透徹的理解與認識的基礎上,繼承好、發展好、利用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開放的心態面對外來文化,在吸納的過程中堅持“走出去”戰略,建立起對中華文明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