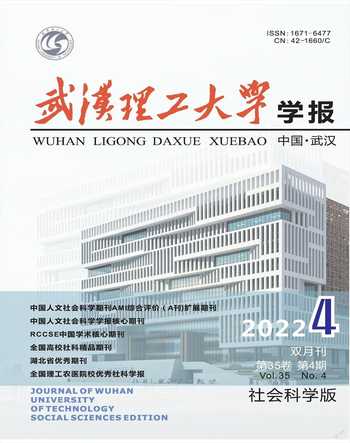瑪姬?吉小說(shuō)《光年》中對(duì)真實(shí)的后現(xiàn)代生態(tài)世界的重構(gòu)
摘 要:瑪姬·吉是當(dāng)代英國(guó)重要的作家之一。在其作品《光年》中,吉反思并批判現(xiàn)代性意識(shí)形態(tài)對(duì)人身心的異化以及對(duì)整個(gè)生物圈和地球共同體的破壞,并且通過(guò)積極建構(gòu)認(rèn)知的身體、有機(jī)的宇宙整體系統(tǒng)以及和諧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地方,來(lái)恢復(fù)身體與心靈、人與宇宙自然、人與地方、人與他人之間的和諧關(guān)系和內(nèi)在聯(lián)結(jié),重構(gòu)真實(shí)的后現(xiàn)代生態(tài)世界。
關(guān)鍵詞:瑪姬·吉;身體;宇宙;地方
中圖分類號(hào):I561.074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22.04.016
生態(tài)后現(xiàn)代主義學(xué)者斯普瑞特奈克在《真實(shí)之復(fù)興》一書中批判現(xiàn)代性意識(shí)形態(tài),倡導(dǎo)徹底的非二元論,積極重構(gòu)一個(gè)真實(shí)的后現(xiàn)代生態(tài)世界。現(xiàn)代性意識(shí)形態(tài)強(qiáng)調(diào)機(jī)械論和還原論,“把身體只看作一架生物機(jī)器,把生物圈和宇宙只看作一套可以預(yù)測(cè)的機(jī)械鐘表裝置,把地方只看作人類活動(dòng)的背景”[1]39。由此導(dǎo)致“人與自然界的斷裂,身體與心靈的斷裂,以及自我與世界中其他存在物的斷裂”[1]78。對(duì)此,斯普瑞特耐克主張“一種生態(tài)學(xué)意義上的徹底的非二元論”[1]譯者序3,一種注重關(guān)系和過(guò)程的有機(jī)整體觀。這一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認(rèn)知的身體(the knowing body)、創(chuàng)造性的宇宙(the creative cosmos)和復(fù)雜的地方觀念(the complex sense of place)三個(gè)方面。認(rèn)知的身體,是一種身心關(guān)系的整體論;創(chuàng)造性的宇宙,是一種宇宙自然的系統(tǒng)論,指出宇宙是一個(gè)活生生的有機(jī)體;復(fù)雜的地方觀念,關(guān)注人與地方自然環(huán)境和文化社會(huì)環(huán)境的密切聯(lián)系。真實(shí),是對(duì)有機(jī)整體性的體認(rèn),對(duì)內(nèi)在相關(guān)性和創(chuàng)生變化的強(qiáng)調(diào)。真實(shí)的后現(xiàn)代生態(tài)世界是一個(gè)萬(wàn)物相互作用相互包含的有機(jī)整體性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在小說(shuō)《光年》(Light Years)中瑪姬·吉反思并批判現(xiàn)代性意識(shí)形態(tài)對(duì)人身心的異化以及對(duì)整個(gè)生物圈和地球共同體的破壞,并且通過(guò)建構(gòu)認(rèn)知的身體、恢復(fù)身心的和諧統(tǒng)一;建構(gòu)有機(jī)的宇宙整體系統(tǒng)、重塑人的背景意識(shí)以及對(duì)宇宙萬(wàn)物的責(zé)任感;建構(gòu)宜居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地方、維護(hù)生態(tài)家園和精神家園這三個(gè)方面來(lái)努力修復(fù)人與自身、與宇宙自然、與地方、與他人的和諧關(guān)系,恢復(fù)并發(fā)展人的感知力、背景意識(shí)、地方意識(shí)和責(zé)任感,樹(shù)立有機(jī)整體觀,重構(gòu)真實(shí)的生態(tài)世界。
一、建構(gòu)認(rèn)知的身體
斯普瑞特奈克主張身體是認(rèn)知的、能動(dòng)的,身心關(guān)系即是身身關(guān)系。作為一個(gè)活的有機(jī)系統(tǒng),身體能夠敏銳感知并積極協(xié)調(diào)自己內(nèi)部以及自身與外界的關(guān)系。認(rèn)知的身體,是嵌入自然的身體,處在與周圍環(huán)境的交感互通之中;認(rèn)知的身體,是具身的身體,身體的感知力是人覺(jué)知自我及認(rèn)識(shí)世界的基礎(chǔ),是智慧的來(lái)源。后工業(yè)社會(huì),在對(duì)功名利祿的追逐中、對(duì)物欲享樂(lè)的沉溺中、對(duì)邏輯推理的崇拜中,人的身體感知本能漸趨麻木鈍化。對(duì)此,斯普瑞特奈克指出:“我們能夠恢復(fù)全部人類感覺(jué)的唯一途徑,就是發(fā)展我們現(xiàn)代減少的意識(shí),并培養(yǎng)對(duì)生活的深刻參與”[1]153。《光年》中,吉刻畫了一個(gè)積極建構(gòu)認(rèn)知的身體的人物——哈羅德。他在對(duì)自然的回歸中、對(duì)周圍環(huán)境的融入中、對(duì)生活的深刻參與中,反抗現(xiàn)代性對(duì)人類身體感知力的壓抑和扭曲,積極恢復(fù)身體感知力,進(jìn)而傾聽(tīng)萬(wàn)物,覺(jué)知當(dāng)下,感受內(nèi)在,重塑整一的身心,找回本真的自我,收獲人生的意義。
吉在小說(shuō)的序言中引用1884年版《世界奇觀》的一段話強(qiáng)調(diào)認(rèn)知的身體的重要性:
智者可能一生之中只會(huì)驚奇一次,但這足使他終生受益;愚者從未對(duì)世界感到驚奇。智者的教育源自對(duì)世界的好奇心,并在對(duì)世界的全身心的崇敬中達(dá)到巔峰……柯勒律治,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宣稱“哲理邏輯始于好奇也終于好奇,而對(duì)世界的崇敬心則一直存在”[2]11。
智者之所以為智,主要原因在于其通過(guò)身體感知力與世界建立了深刻的聯(lián)結(jié)。所謂的“驚奇”、“好奇”、“崇敬”都源自身體的感知力。智者,憑借認(rèn)知的身體,擺脫對(duì)邏輯推理的盲目崇拜,并且深刻地參與生活、聯(lián)結(jié)外界,從而獲得對(duì)世界和自我的真實(shí)的覺(jué)知、收獲真正的智慧。愚者,與真實(shí)的世界分離,導(dǎo)致缺乏對(duì)生命的深刻洞見(jiàn)、對(duì)人生的真實(shí)體驗(yàn),以及對(duì)自我的清醒認(rèn)知。
小說(shuō)中,哈羅德可以稱的上是一位依靠身體感知力收獲智慧并實(shí)現(xiàn)人性升華的“智者”。長(zhǎng)期生活在高樓林立的城市里,遠(yuǎn)離真實(shí)的自然,他的身體感知力變得衰微;同時(shí),對(duì)成功名望的追逐,對(duì)理性知識(shí)的崇拜,也壓抑著他的身體本能。不能敏銳地感知世界,不能真實(shí)地覺(jué)知自我,不能深刻地參與生活,他承受著身體與心靈的斷裂、自身與自然的斷裂,他成為困在玻璃盒子里的人,一個(gè)孤獨(dú)的牛仔,直言自己找不到生活的意義、迷失了前進(jìn)的方向。幸而,在對(duì)自然的回歸和熱愛(ài)中,他擺脫對(duì)書呆子式的邏輯推理的盲目崇拜、擺脫名利物欲的束縛,恢復(fù)并發(fā)展了身體感知力;進(jìn)而,憑借敏銳的感知力去重新感受外界、深刻地參與生活、覺(jué)知當(dāng)下,重構(gòu)健全的和諧的身心以及自然的本真的自我。
認(rèn)知的身體,是嵌入自然的身體,時(shí)時(shí)刻刻處在與周圍環(huán)境的交感互通之中。從與自然分離到回歸自然,“世界的變化影響人的身體性感受,人又因此從身體出發(fā)重新關(guān)照自然”[3]59。一次爭(zhēng)吵之后,哈羅德離家出走,來(lái)到一座海邊小城,重回自然的懷抱。起初,因?yàn)榱?xí)慣了城市的溫室暖房,直面刺骨的海風(fēng)和初升的太陽(yáng)讓他生出強(qiáng)烈的不適感。數(shù)日之后,他的身體已然適應(yīng)了周圍環(huán)境,他靜心感受自然之美,并且與穿破烏云的光線、逆風(fēng)翱翔的海鷗、矗立于峭壁之上的松樹(shù)產(chǎn)生共情,感慨雖然處境艱難仍要保持昂揚(yáng)的斗志。從自然之中獲得心靈的撫慰、汲取精神的力量和實(shí)現(xiàn)感知力的復(fù)原,哈羅德為自然之崇高所折服。他選擇租住在一個(gè)海邊閣樓上,回歸自然,沉入寧?kù)o,簡(jiǎn)樸生活,感知最本真的存在體驗(yàn),修煉平和從容的心境。
身體的感知力是人體驗(yàn)、覺(jué)知以及認(rèn)識(shí)自身和世界的基礎(chǔ),是智慧的來(lái)源,因?yàn)檎J(rèn)知的身體“創(chuàng)造意義”,它“對(duì)于自己內(nèi)部和周圍大范圍的微妙力量十分敏感,從中自行理解、選擇和組織信息,賦予這信息以意義——它自己的意義”[1]23。也正因如此,濟(jì)慈才高呼“我寧愿過(guò)一種感覺(jué)的生活,而不要過(guò)思想的生活!”[4];梅洛龐蒂才不斷強(qiáng)調(diào)身體知覺(jué)的基礎(chǔ)地位——“我們對(duì)物體的了解不可能超出身體所能知覺(jué)的范圍”[5],“肉體而非精神是存在意義之源”[5]。他經(jīng)常靜靜地佇立在陽(yáng)臺(tái)上觀看波浪翻涌、云卷云舒、光影變幻,聆聽(tīng)風(fēng)聲、海浪聲和海鳥(niǎo)的鳴叫。傾聽(tīng)、靜觀、冥想,是他融入自然、與周圍世界交感互通的一種身心修煉方式。哈羅德感慨自己之前悶在房間里研究資料完全是在閉門造車,如今仰望星空、沉思冥想,成為他最愜意的時(shí)光。他調(diào)動(dòng)敏銳的感知力和豐富的想象力,感受與宇宙星辰的能量頻率接軌,想象天地的遼闊廣大和時(shí)間的源遠(yuǎn)流長(zhǎng),體會(huì)天人合一的古樸浪漫和超然物外的閑適淡定,在情景交融中突破小我、實(shí)現(xiàn)人性的升華和智慧的覺(jué)醒。
身體感知力讓人具身感知自我與外界的交感互通的同時(shí),充分覺(jué)知當(dāng)下,體驗(yàn)到大自在和真通達(dá),實(shí)現(xiàn)身心的安定豐盈,洞悉人生的意義。此前,哈羅德奮力追逐名利、追求他人認(rèn)同,壓抑了真實(shí)感受,迷失了真我。現(xiàn)在,他意識(shí)到只有深刻參與生活、敏銳覺(jué)知當(dāng)下,才能逐漸認(rèn)清自我并重構(gòu)真我。恰如其父所言“重要的是做那些事的時(shí)候你開(kāi)心嗎”[2]246;“人不是為了成就而活,是為生活而生活”[2]256。哈羅德學(xué)會(huì)細(xì)心感受當(dāng)下的每一刻,認(rèn)真體味生活中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重新觀察周圍的一草一木,更加熱愛(ài)故鄉(xiāng)、親近自然、感恩生命。當(dāng)他爬上海邊的一處峭壁,四下無(wú)人,只有天空、大海、海風(fēng)、陽(yáng)光、野草和海鳥(niǎo),他趴在地上靜止不動(dòng)。
“就在那一瞬間,他清楚地聽(tīng)到了大海的聲音。他屏氣凝神,靜止不動(dòng)了幾秒。不是怒吼聲,也不是竊竊私語(yǔ)聲,而是幾百萬(wàn)個(gè)貝殼和鵝卵石翻轉(zhuǎn)、打旋、破碎的聲音,是數(shù)百億顆砂礫相互間摩擦、旋轉(zhuǎn)、攪拌的聲音。他無(wú)視船只和海灘小屋,無(wú)視人類制造的臟亂。……這個(gè)聲音已經(jīng)有四百億年之久。無(wú)論人類如何,它都仍將持續(xù)下去。……自己是那個(gè)聲音的一份子,自己是活的,地球也是活的。”[2]300
哈羅德被動(dòng)而又警覺(jué)地感受著周圍的一切,進(jìn)而到達(dá)一種物我兩相忘的境界,只感受到生命能量的原始搏動(dòng);在那一刻,他忘卻俗事紛擾,超越生死焦慮,融入到宇宙洪荒的博大智慧中,融入到生命綿延無(wú)盡的創(chuàng)生進(jìn)程中,體驗(yàn)到與萬(wàn)事萬(wàn)物的合一,享受到永恒當(dāng)下的至樂(lè);對(duì)自然的尊重、對(duì)生命的敬畏,油然而生。
在自然之中察萬(wàn)物,在世界之中看世界,安住當(dāng)下,覺(jué)知自我,哈羅德切身體驗(yàn)了自身與自然的融合、與萬(wàn)物的交互,恢復(fù)并發(fā)展了身體的感性知覺(jué)力,實(shí)現(xiàn)身心合一;與此同時(shí),既聆聽(tīng)自我又傾聽(tīng)自然,既修煉內(nèi)在又溝通外在,達(dá)到天人合一。他掙脫物欲的囚籠、名利的枷鎖和理性的束縛,在融入自然、聯(lián)結(jié)世界、傾聽(tīng)萬(wàn)物、覺(jué)知當(dāng)下中感知最本真的存在體驗(yàn),重構(gòu)自然的生態(tài)的自我,修煉平和從容的心境,收獲真正的智慧和人生的意義、秉持一顆仁愛(ài)之心對(duì)待天地萬(wàn)物。哈羅德對(duì)認(rèn)知的身體的建構(gòu),不僅彌合了身心的斷裂、強(qiáng)調(diào)身心是一個(gè)有機(jī)整體,而且修復(fù)了人與自然的分離,強(qiáng)調(diào)身體與外部世界亦是一個(gè)有機(jī)整體。
二、建構(gòu)有機(jī)的宇宙整體系統(tǒng)
斯普瑞特奈克主張宇宙自然是一個(gè)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有機(jī)整體,宇宙萬(wàn)物內(nèi)在相關(guān)、共處于整個(gè)宇宙創(chuàng)生變化的動(dòng)態(tài)進(jìn)程之中。“不僅所有的存在在結(jié)構(gòu)上通過(guò)宇宙之鏈而聯(lián)系在一起,而且所有的存在內(nèi)在地是由與他人的關(guān)系構(gòu)成的”[6]20。人類活動(dòng)深深嵌入于整個(gè)宇宙的運(yùn)轉(zhuǎn)過(guò)程之中,宇宙是人類生存發(fā)展的根基;人不是唯一的主體,宇宙萬(wàn)物都具有主體地位,是與人類交互共生、合作共事的親屬和伙伴。創(chuàng)造性的宇宙是一種宇宙自然的整體論思想,突出宇宙自然的主體地位,強(qiáng)調(diào)人對(duì)更大的共同體的嵌入性和責(zé)任感。對(duì)這一宇宙自然有機(jī)整體系統(tǒng)的體認(rèn),是吉對(duì)現(xiàn)代性的批判和超越,是拯救異化的關(guān)鍵。在現(xiàn)代性二元對(duì)立思維模式的影響下,人類中心主義大為盛行,宇宙被視為“一套可以預(yù)測(cè)的機(jī)械鐘表裝置”[1]39,自然界被視為“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的外殼”[1]3,導(dǎo)致人與宇宙自然的破壞性斷裂、人對(duì)自然萬(wàn)物責(zé)任感的缺失。
在《光年》中,吉按照月份將小說(shuō)分為十二個(gè)部分對(duì)應(yīng)一年的十二個(gè)月份,并在每一部分的開(kāi)頭和結(jié)尾部分都描繪了星體的狀態(tài)以及動(dòng)植物在不同時(shí)節(jié)的發(fā)展變化;大到太空和行星,小到昆蟲(chóng)和花草,一切都處于有機(jī)的動(dòng)態(tài)關(guān)聯(lián)之中;整部小說(shuō)營(yíng)造了一種宇宙自然的有機(jī)整體氛圍。吉特意將整個(gè)故事安置在宇宙時(shí)空的大背景之中,一方面,點(diǎn)明了宇宙是一個(gè)活的有機(jī)體,人類活動(dòng)深深嵌入于自然、地球、宇宙等更大的神圣整體之中,另一方面,旨在強(qiáng)調(diào)自然萬(wàn)物的主體地位、萬(wàn)物與人之間息息相關(guān)的親屬關(guān)系,點(diǎn)明人類必須尊重自然、保護(hù)動(dòng)植物、守護(hù)地球生命共同體。
人類不是宇宙的主宰,亦不是萬(wàn)物的主人。小說(shuō)中,吉描寫到“光……穿越整個(gè)銀河系需要八萬(wàn)年……整個(gè)宇宙里至少有一千億個(gè)銀河系……對(duì)于我們?nèi)祟悂?lái)說(shuō),一年的時(shí)間對(duì)我們來(lái)說(shuō)已經(jīng)足夠長(zhǎng)了。”[2]13在浩瀚的宇宙里,人類只是天地一蜉蝣,滄海一米粟。地球是一個(gè)生命共同體,“每一個(gè)宇宙生命的形式都是以它自己的方式來(lái)到世上的,然而它們之中沒(méi)有一個(gè)是孤立地到來(lái)的”[1]233,同時(shí),人類的出現(xiàn)只是地球上生命演化進(jìn)行到一定階段的結(jié)果,在人類出現(xiàn)之前已經(jīng)有無(wú)數(shù)的有機(jī)體存在。正如哈羅德所了解到的“35億年前,地球上的第一個(gè)生命開(kāi)始萌發(fā)……六百萬(wàn)前,多細(xì)胞生物開(kāi)始出現(xiàn),并形成一條生命演化鏈條……50萬(wàn)年前人類出現(xiàn)……”[2]261可見(jiàn),“人不是突兀的產(chǎn)物,不是孤獨(dú)的存在”[6]。人類與其他有機(jī)體共同編織了一張歷史悠久的親緣網(wǎng)絡(luò),一個(gè)綿延不絕的生命譜系,共同“見(jiàn)證了生命的恩情”[3]222。地球上的其他有機(jī)體是人類的恩人、親戚、合作伙伴,人類對(duì)它們有看護(hù)、回饋的責(zé)任和義務(wù)。
“不僅地球是有生命的,而且整個(gè)宇宙都是活的有機(jī)體”[7]178,宇宙之鏈中的所有存在相互作用、共處于動(dòng)態(tài)創(chuàng)生進(jìn)程之中。萬(wàn)物內(nèi)在相關(guān)、生生不息、循環(huán)往復(fù)是宇宙規(guī)律和天地法則。后現(xiàn)代物理學(xué)和量子力學(xué)已經(jīng)證實(shí)了這一點(diǎn)。哈羅德了解到,在某個(gè)臨界點(diǎn)上不斷擴(kuò)展的宇宙會(huì)開(kāi)始凝聚,幾十億年后,當(dāng)所有的物質(zhì)會(huì)重新聚集到一起時(shí)宇宙大爆炸會(huì)再次發(fā)生,生命又將重新繁衍。與此同時(shí),哈羅德領(lǐng)悟到,“新出現(xiàn)的生命形式雖然和之前的不同,但卻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guò)以另一種已經(jīng)完全變形的能量體存在。……我們將一直不停運(yùn)動(dòng)下去,不是以我們自身本來(lái)的形式,而是以萬(wàn)物的形式。”[2]283人與其他有機(jī)物無(wú)機(jī)物不是中心和邊緣、主體和客體的二元對(duì)立關(guān)系,而是密切相關(guān)的親屬伙伴關(guān)系。“生物體之間沒(méi)有非此即彼的界限:‘我’是它們,它們是‘我’。這就是愛(ài)的緣由”[3]225在小說(shuō)《光年》序言中,吉引用但丁《神曲·天堂》中的一句話“愛(ài),催動(dòng)日月星辰”,意在強(qiáng)調(diào)萬(wàn)物的內(nèi)在相關(guān)性是宇宙運(yùn)轉(zhuǎn)的動(dòng)力所在。正是因?yàn)槿f(wàn)物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宇宙的創(chuàng)生變化過(guò)程才能生生不息地持續(xù)下去。愛(ài)的真諦正是對(duì)這一關(guān)系和過(guò)程的體認(rèn)。愛(ài),是人對(duì)宇宙的嵌入,是對(duì)萬(wàn)物的責(zé)任和關(guān)愛(ài),是人與人之間真摯的情感。愛(ài)強(qiáng)調(diào)關(guān)聯(lián)互通、消滅中心、顛覆等級(jí)、尊重差異、包容多元。愛(ài)是建構(gòu)宇宙有機(jī)整體、地球生命共同體、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基本動(dòng)力和根本保證。
吉一再?gòu)?qiáng)調(diào)人類與周圍世界息息相關(guān),動(dòng)植物是人類的親屬伙伴,尊重自然、關(guān)愛(ài)萬(wàn)物既是人類的責(zé)任和使命,也是人類的自我救贖。斯普瑞特奈克強(qiáng)調(diào)“重新發(fā)現(xiàn)我們與周圍存在的關(guān)系,首先在于認(rèn)識(shí)到人類周圍并不只是一堆客體,而是一堆主體。”[1]234《光年》中,吉描繪了幾十種動(dòng)植物在不同時(shí)節(jié)的生長(zhǎng)樣態(tài)。作為能動(dòng)的主體,它們不僅對(duì)季節(jié)變化感知敏感,能主動(dòng)適應(yīng)周圍環(huán)境,而且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協(xié)調(diào),組成一個(gè)個(gè)小型生態(tài)圈。同時(shí),吉揭露了人類對(duì)動(dòng)物的種種傷害,并成功塑造了一個(gè)擺脫人類中心主義、學(xué)會(huì)尊重和關(guān)愛(ài)動(dòng)物的人物。一直以來(lái),受到笛卡爾哲學(xué)二分法的影響,人與動(dòng)物主客體二元對(duì)立的思想頗為盛行。人類將動(dòng)物視為工具、商品,凝視的對(duì)象和文化意義的投射物,通過(guò)買賣、馴化動(dòng)物,扭曲其天然本性,只為滿足自己的需求。“人類一方面耿耿于自身的異化,另一方面卻又一直致力于動(dòng)物的異化。”[8]28動(dòng)物走私一直屢禁不止,動(dòng)物“作為稀有產(chǎn)品被出售,構(gòu)成今日世界上位居毒品和武器之后的第三大非法走私貿(mào)易”[9]11。小說(shuō)中,洛蒂為討丈夫歡心買來(lái)珍稀動(dòng)物絹毛猴養(yǎng)在家中,卻因?yàn)檎樟喜恢苤缕渌劳觥T谒磥?lái),絹毛猴與其說(shuō)是一條生命,不如說(shuō)是一個(gè)標(biāo)榜其身份的消費(fèi)符號(hào)。洛蒂已經(jīng)內(nèi)化了人與動(dòng)物二元對(duì)立的思想,堅(jiān)信人與動(dòng)物是絕對(duì)分離的,人是萬(wàn)物的主宰,動(dòng)物是沉默的被動(dòng)客體。所以,她對(duì)動(dòng)物園中眾多動(dòng)物與人類共居于世這個(gè)事實(shí)感到震驚和不適,并且完全從人類的視角出發(fā)去審視、點(diǎn)評(píng)各類動(dòng)物。正如戴維所言,“是不是鳥(niǎo)取決于鳥(niǎo)而不取決與人。因?yàn)槟悴涣私怿B(niǎo),所以你把鳥(niǎo)理解為其他事物”[2]86。尊重動(dòng)物,在于承認(rèn)動(dòng)物的主體地位,直面它們的本來(lái)面目。再次參觀動(dòng)物園,洛蒂拋開(kāi)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在撫摸大象的過(guò)程中直面大象的客觀實(shí)相,靜心感受到大象被訓(xùn)斥時(shí)的恐慌不安,并為人類對(duì)大象的束縛和折磨而倍感恥辱。尊重動(dòng)物,在于切身感受動(dòng)物的喜怒哀樂(lè)。洛蒂通過(guò)觀察母猴對(duì)小猴的關(guān)愛(ài),體會(huì)親情的可貴;看到兩只猩猩昆巴和莎樂(lè)美相互陪伴,以及昆巴離開(kāi)后莎樂(lè)美的悲傷,體會(huì)到友情的重要。與猩猩的共情,讓她意識(shí)到愛(ài)的重要性,人與人、人與動(dòng)物之間都需要愛(ài)來(lái)維持彼此之間的和諧關(guān)系。尊重動(dòng)物,更在于承擔(dān)其保護(hù)動(dòng)物的責(zé)任和義務(wù)。洛蒂主動(dòng)承擔(dān)起關(guān)愛(ài)和保護(hù)動(dòng)物的責(zé)任,在動(dòng)物園認(rèn)領(lǐng)四只絹毛猴,為它們支付口糧。從分離到聯(lián)結(jié),從輕視轉(zhuǎn)向了尊重,從傷害到保護(hù),洛蒂對(duì)待動(dòng)物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變。與此同時(shí),洛蒂感到自己在更多地給予,更多地關(guān)注身邊的人。恰恰因?yàn)樗辉賵?zhí)著于占有反而收獲更多。洛蒂超越人類中心主義和自我主義,跳出物質(zhì)主義和消費(fèi)主義的陷阱,重構(gòu)了與自身、與動(dòng)物、與他人的和諧關(guān)系,超越小我成就生態(tài)大我。
人與其他有機(jī)物無(wú)機(jī)物相互作用、相互生成,共同構(gòu)成整個(gè)宇宙自然的有機(jī)整體系統(tǒng)。同時(shí),人作為有機(jī)物的一種,需要棲居于生物區(qū)域,因此必須保護(hù)地方的自然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積極建構(gòu)提升居民的整體幸福感、實(shí)現(xiàn)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地方。
三、建構(gòu)和諧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地方
斯普瑞特奈克強(qiáng)調(diào)地方“是生物區(qū)域,是社區(qū)和個(gè)人得以舒展的物理場(chǎng)所”[1]5。地球共同體由無(wú)數(shù)個(gè)生物區(qū)域組成,人類的各種活動(dòng)和各種關(guān)系的展開(kāi)都嵌入于生物區(qū)、社區(qū)、家庭之中;“宇宙/地球/大陸/民族/生物圈/社區(qū)/鄰里/家庭/個(gè)人。這些都是自我擴(kuò)展了的界限”[1]85。勞倫斯·布伊爾(Lawrence Buell)指出:“地方概念至少同時(shí)指示三個(gè)方向——環(huán)境的物質(zhì)性、社會(huì)感知或建構(gòu)、個(gè)人影響或約束”[10]63。地方,不僅是人類繁衍生息的物理居所,而且是歷史文化的承載者,是個(gè)體情感、記憶與夢(mèng)想的寄托。
現(xiàn)代性意識(shí)形態(tài)不僅造成了人的身心分離,人與自然的分離,還造成人與地方的分離,從而導(dǎo)致個(gè)體處于無(wú)家可歸的狀態(tài),面臨生態(tài)家園毀滅和精神家園迷失的雙重危機(jī)。追求經(jīng)濟(jì)發(fā)展是現(xiàn)代性進(jìn)步觀的核心要素,不惜以犧牲地方生態(tài)環(huán)境為代價(jià)換取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隨著城市化和商業(yè)化進(jìn)程的不斷推進(jìn),地方同質(zhì)化趨勢(shì)不斷吞噬著地方的獨(dú)特魅力,地方的差異性和多樣性正逐漸消逝;與此同時(shí),消費(fèi)主義的盛行正在不斷消解著地方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深厚底蘊(yùn)和崇高美感、妨礙著居民的精神文化修養(yǎng),景觀化、符號(hào)化的超真實(shí)正逐漸取代嵌入地方的真實(shí)。人類毫不節(jié)制自己的欲望,追求物質(zhì)利益最大化,導(dǎo)致地方的自然根基和文化根基均遭到嚴(yán)重破壞;家庭親密關(guān)系也受到?jīng)_擊,貧富分化、居住分異的現(xiàn)象也日益嚴(yán)重,威脅社區(qū)和諧穩(wěn)定;人的地方依附感日漸淡薄,疏離感和無(wú)根感則日益加重。
生態(tài)后現(xiàn)代主義認(rèn)為亟須修復(fù)人與地方的深刻聯(lián)結(jié),積極建構(gòu)一種以提升居民的整體幸福感和實(shí)現(xiàn)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目標(biāo)的地方發(fā)展模式。科爾帕特里克·塞爾(Kirkpatrick Sale)呼吁在地方中扎根、承擔(dān)對(duì)地方的深層義務(wù)、把地方重新神圣化[11]347。在小說(shuō)《光年》中,吉倡導(dǎo)恢復(fù)人的地方意識(shí)、保護(hù)地方自然環(huán)境、尊重地方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關(guān)愛(ài)家庭、關(guān)注社區(qū),積極重構(gòu)生態(tài)家園和精神家園。哈羅德反思經(jīng)濟(jì)主義、消費(fèi)主義對(duì)地方歷史文化底蘊(yùn)和個(gè)體身心發(fā)展的傷害;洛蒂也從物欲洪流和消費(fèi)主義的符號(hào)世界中脫身,承擔(dān)起關(guān)愛(ài)他人、關(guān)愛(ài)地方的責(zé)任。
不斷復(fù)制的商業(yè)發(fā)展模式,導(dǎo)致地方建設(shè)的同質(zhì)化,抹殺了地方發(fā)展的特色和本真意義。哈羅德前往倫敦最大的模型基地參觀,到達(dá)之后首先映入眼簾的卻是一個(gè)大型游樂(lè)園。游樂(lè)園儼然是一個(gè)仿真世界,里面是各種實(shí)物模型。自迪士尼樂(lè)園在美國(guó)面世以來(lái),這種超真實(shí)的景觀模式在大城市中迅速?gòu)?fù)制開(kāi)來(lái)。大型游樂(lè)園不僅成為城市中最受歡迎的娛樂(lè)場(chǎng)所和標(biāo)志性建筑之一,甚至成為衡量地方城市化水平的標(biāo)準(zhǔn)隱形之一。就像哈羅德所評(píng)價(jià)的,這里“更像美國(guó)式的,不像英國(guó),盡管現(xiàn)在沒(méi)什么區(qū)別”[2]149。
不僅如此,地方傳統(tǒng)歷史文化更是淪為商業(yè)盈利的噱頭。本該彰顯地方歷史文化底蘊(yùn)的“大不列顛模型基地”卻成為一個(gè)被抽空人文價(jià)值和精神內(nèi)涵的景觀符號(hào)。之所以建造該模型基地,只是因?yàn)樯碳铱粗辛说胤綒v史文化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作為現(xiàn)代化成果的展示品,該模型基地非但沒(méi)有彰顯現(xiàn)代性的豐功偉績(jī),反而暴露了現(xiàn)代性的種種弊端。交通、工業(yè)以及科技成果本是現(xiàn)代性進(jìn)步的主要標(biāo)志,在模型中卻呈現(xiàn)出停滯不前的狀態(tài):運(yùn)貨卡車停在路邊、鉆塔功能失效、停車場(chǎng)已然坍圮、飛機(jī)在地面來(lái)回滑行、電動(dòng)火車圍繞四周不停跑動(dòng)。吉在此暗示,對(duì)現(xiàn)代性進(jìn)步觀的盲目崇拜,對(duì)工業(yè)主義、科技主義、經(jīng)濟(jì)主義的狂熱追捧不僅會(huì)導(dǎo)致人身心的異化,還會(huì)引發(fā)嚴(yán)重的生存危機(jī)。模型中最大最搶眼的建筑物竟是一個(gè)核電站附近的人偶臉上呈現(xiàn)出一種死于神秘疾病的驚厥抽搐狀態(tài)。不難猜想,致人死亡的就是核輻射。同時(shí),本該熱鬧的比賽、喜慶的婚禮卻都呈現(xiàn)出一種人與人之間冷漠疏離的景象。放眼整個(gè)模型群,看不到自然風(fēng)光,這也從側(cè)面表明隨著現(xiàn)代化和城市化進(jìn)程的加快,自然被侵占和擠壓得所剩無(wú)幾。可以說(shuō),該模型基地是整個(gè)英國(guó)的縮影,整個(gè)模型呈現(xiàn)出一種頹敗、壓抑的氛圍,暗喻整個(gè)社會(huì)危機(jī)四伏的現(xiàn)狀——工業(yè)發(fā)展的停滯,自然環(huán)境遭到破壞,人的身體被毒物入侵,人與人之間冷漠疏離。正如哈羅德所說(shuō),“大不列顛就是這樣的,一切都不再運(yùn)轉(zhuǎn),百?gòu)U待興,所有的舊儀式都出錯(cuò)了。”[2]151這不禁發(fā)人深思,現(xiàn)代性給人類帶來(lái)的究竟是什么?把經(jīng)濟(jì)發(fā)展放在第一位真的會(huì)讓人幸福嗎?科技進(jìn)步真的增進(jìn)社會(huì)和諧嗎?吉在此表達(dá)了對(duì)現(xiàn)代性意識(shí)形態(tài)的反詰,對(duì)人類命運(yùn)的深切憂慮和對(duì)地方發(fā)展前景的關(guān)照,并警告世人——若再不改變思維模式,模型展的荒原圖景就是人類的未來(lái)。
越多越繁榮,越大越強(qiáng)盛,是這個(gè)時(shí)代的魔咒。哈羅德的家鄉(xiāng),一個(gè)邊陲小城,也已然被魔咒入侵,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型購(gòu)物商場(chǎng)和各種娛樂(lè)場(chǎng)所鱗次櫛比。購(gòu)物娛樂(lè)成為了人們閑暇時(shí)的主要消遣,景觀化、符號(hào)化的超真實(shí)充斥著人們的生活。傳統(tǒng)節(jié)日本是增進(jìn)彼此情感交流、宣傳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日子,如今卻變成了購(gòu)物盛典,淪為一個(gè)被剝離歷史文化底蘊(yùn)的消費(fèi)符號(hào)。哈羅德看到又小又破的商店里滿是低俗的玩具,很顯然這些商品是為了滿足客人的低級(jí)趣味。在消費(fèi)主義打造的超真實(shí)世界里,“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wú)規(guī)則游戲的庸俗文化”,“人們由于享樂(lè)而失去自由”[12]Ⅱ不知不覺(jué)中成為娛樂(lè)的附庸。同時(shí),碼頭附近交通擁擠導(dǎo)致空氣污染嚴(yán)重,同時(shí)各種化工垃圾污染水源,引起中毒和各種慢性疾病。可見(jiàn),經(jīng)濟(jì)主義、消費(fèi)主義的盛行,一方面不斷侵蝕著地方的歷史文化底蘊(yùn),導(dǎo)致人沉迷于物欲享樂(lè)之中精神日漸空虛,人與地方、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lián)結(jié)日益脆弱;另一方面直接破壞地方的生態(tài)平衡,危害人類和其他動(dòng)植物的生存。
吉直擊當(dāng)下城市發(fā)展的弊病,指出地方成為經(jīng)濟(jì)進(jìn)步和消費(fèi)繁榮的背景板,成為缺失文化底蘊(yùn)、缺少人情味的一具空殼;與此同時(shí),在物欲橫流的當(dāng)下,家庭關(guān)系也逐漸走向疏離,貧富分化日益嚴(yán)重,社區(qū)居住分異愈加鮮明化,所有這些都是地方和諧穩(wěn)定發(fā)展的潛在威脅。洛蒂擁有大量財(cái)富,消費(fèi)娛樂(lè)活動(dòng)占據(jù)著她的時(shí)間,景觀化、符號(hào)化的超真實(shí)充斥著她的生活。她離真實(shí)越來(lái)越遠(yuǎn),與家人的交流越來(lái)越稀少,與地方的情感聯(lián)結(jié)越來(lái)越淡薄,對(duì)地方問(wèn)題和他人疾苦充耳不聞、視而不見(jiàn)。為緩和夫妻矛盾,她通過(guò)非法途徑購(gòu)買稀有物種絹毛猴來(lái)取悅丈夫。哈羅德離家之后,為排遣郁悶,她選擇去購(gòu)物天堂巴黎散心,把尚未成年的兒子交給保姆照看。家,不再是溫馨的港灣,而是一個(gè)冷冰冰的空殼。在巴黎盡情享樂(lè),洛蒂感覺(jué)自己內(nèi)心的郁悶一掃而光。但是滿足之后卻是空虛寂寥,她開(kāi)始意識(shí)到家人才是自己的存在之根,物質(zhì)的豐裕不能代替深層的情感聯(lián)結(jié)。所以,當(dāng)接到兒子的求助電話之后,她立即返回倫敦,孤身一人前往貧民區(qū)索回家中被偷的珠寶,展現(xiàn)出對(duì)兒子的關(guān)愛(ài)以及對(duì)家庭的責(zé)任感。
隨著城市化進(jìn)程的不斷加速,居住區(qū)分化日益明顯。小說(shuō)中的貧民區(qū)陳舊臟亂、幽暗壓抑、擁擠不堪,呈現(xiàn)出一種頹廢、暴力的氛圍,與狄更斯筆下的貧民窟頗為相似。這里彷佛上個(gè)世紀(jì)的產(chǎn)物,與城市光鮮亮麗的高樓大廈的整體氛圍格格不入,是一個(gè)被遺忘的世界。洛蒂第一次來(lái)到貧民區(qū),不禁驚訝于繁華都市中貧民區(qū)的存在,更震驚于占地面積如此之大的貧民區(qū)在城市地圖中卻只顯示為一個(gè)小點(diǎn),甚至連名稱都沒(méi)有標(biāo)記。這樣縮小到極致,仿佛就可以把貧窮問(wèn)題掩蓋起來(lái),仿佛就可以把窮人牢牢掌控住,防止他們跨越階層、分割富人的利益。很顯然,這種標(biāo)記方式突出并且強(qiáng)化了窮人的邊緣化地位,是對(duì)窮人的無(wú)形歧視和壓迫。居住分異從側(cè)面證明了貧富懸殊日益嚴(yán)重,也不斷強(qiáng)化著等級(jí)界限。在此之后,洛蒂對(duì)貧窮有了直觀的感受,內(nèi)心大受震撼。此前,她對(duì)貧窮問(wèn)題一無(wú)所知,對(duì)抗議群體漠不關(guān)心。洛蒂掙脫物欲的束縛,敏銳感知周圍環(huán)境,深度考察社會(huì)問(wèn)題,反思消費(fèi)主義,成功修復(fù)與家人的和諧關(guān)系,積極向窮人和抗議群體提供援助,為維護(hù)家庭和諧與社區(qū)穩(wěn)定貢獻(xiàn)一己之力。
四、結(jié) 語(yǔ)
在《光年》中,吉建構(gòu)了一個(gè)真實(shí)的后現(xiàn)代生態(tài)世界。在其中,身體是認(rèn)知的身心、是身心合一的有機(jī)體,同時(shí),恢復(fù)并發(fā)展身體感知力是人融入自然、參與生活、覺(jué)知自我、感受世界的基礎(chǔ),也是拯救異化、收獲智慧和實(shí)現(xiàn)人性升華的基本保證;宇宙是活生生的有機(jī)體,宇宙萬(wàn)物相互作用、相互包含,共處于整個(gè)宇宙自然的創(chuàng)生過(guò)程之中,而人類只是宇宙之鏈、生命之網(wǎng)的一環(huán),重新根植于宇宙之中并且維護(hù)好建設(shè)好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和地球生命共同體,是人類義不容辭的責(zé)任和義務(wù);地方是生物區(qū)域,是人類和其他有機(jī)物生存和發(fā)展的物理場(chǎng)所,也是社區(qū)紐帶、家庭關(guān)系的化身,是歷史傳統(tǒng)、個(gè)人記憶和夢(mèng)想的寄托,同時(shí),反思現(xiàn)代進(jìn)步觀對(duì)地方的危害、改變現(xiàn)代人無(wú)家可歸的狀態(tài)、建構(gòu)和諧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地方刻不容緩。吉的小說(shuō)文本充分體現(xiàn)了生態(tài)后現(xiàn)代主義思想,批判了現(xiàn)代性意識(shí)形態(tài),解構(gòu)中心、顛覆等級(jí)、取消對(duì)立、消弭界限、修復(fù)斷裂、尊重差異、承認(rèn)多元,深刻發(fā)展了人與自身、他人、宇宙自然、地方之間的有機(jī)整體關(guān)系,呼喚人的身體意識(shí)、背景意識(shí)、地方意識(shí)和責(zé)任感,對(duì)實(shí)現(xiàn)人的健康的全面的發(fā)展以及建設(shè)生態(tài)社會(huì)、和諧社會(huì)和地球生命共同體有重大的啟發(fā)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1] 查倫·斯普瑞特奈克.真實(shí)之復(fù)興[M].張妮妮,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2]Gee,Maggie.Light Years[M].London:Saqi Books,1991.
[3]王曉華.身體詩(shī)學(xu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4]濟(jì)慈.濟(jì)慈書信集[M].傅修延,譯.上海:東方出版社,2002:37.
[5]歐陽(yáng)燦燦.身體如何成為存在的根基[J].外國(guó)文學(xué),2018(3):105-114.
[6]Spretnak,Charlene.State of Grace:The Recovery of Meaning in the Postmodern Age[M].San Franciso: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1.
[7]田中裕.懷特海有機(jī)哲學(xué)[M].包國(guó)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8]朱寶榮.20世紀(jì)歐美小說(shuō)動(dòng)物形象新變[J].外國(guó)文學(xué)評(píng)論,2003(4):25-32.
[9]羅西·布拉伊多蒂.后人類[M].宋根成,譯.開(kāi)封: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6:11.
[10]Buell,Laurence.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5:63.
[11]戴維·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xué)[M].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47.
[12]尼爾·波茲曼.娛樂(lè)至死[M].章艷,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Ⅱ.
(責(zé)任編輯 文 格)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al Postmodern Ecological World in Maggie Gee’s Light Years
ZHAO Qian, CHEN Shi-d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Maggie Ge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mporary writers in Britain.In her work Light Years,Gee reflects and criticizes the ideology of modernity by pointing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n the whole ecological circle and the earth life community,reconstructs the real postmodern ecological world and restores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y constructing the knowing body,the organic system of the cosmos,and the harmonious sustainable place.
Key words:Maggie Gee; body; cosmos; 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