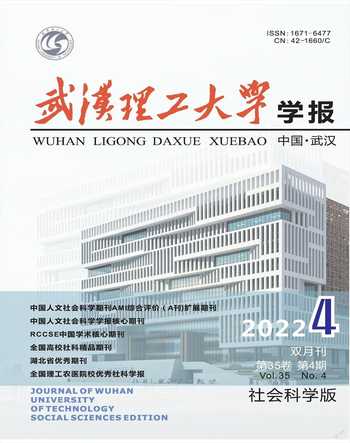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國際刑事規制的強化探析
摘 要: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的國際刑事規制呈強化動向。參與此議題的國際機構越來越多,新的國際文件相繼出臺,所涵括的內容更為明確具體。這一強化動向是基于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后果的嚴重性以及跨國性特點,也得益于“人類共同遺產”理念的推動。我國應據此強化預防措施,加強國際合作,以防范和打擊文化財產的非法販運行為;應根據新的國際規則審視和修訂現行文化財產立法,規制文化財產的非法進口行為,并考慮將其入刑;且應增加條款明確文化財產市場參與者的盡職調查義務及其相應的違法責任。
關鍵詞:文化財產;非法販運;國際刑法;盡職調查
中圖分類號:D997.9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22.04.009
文化財產①是人類的寶貴財富,是不可再生的資源。但是,非法販運文化財產的行為長期存在。這不僅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傷害特定人群的情感,還可能減損文化財產背后的歷史線索和科研價值。20世紀50~60年代,此類行為開始受到關注,1970年國際社會為此出臺了《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以下簡稱《1970年教科文組織公約》)以及1995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以下簡稱《1995年UNIDROIT公約》)。這兩份文件構成規制文化財產非法進出口,以及推動非法文化財產返還的最重要的條約體系,對于打擊文化財產的非法販運行為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刑事規制不是這兩份文件的主要關注點,前者僅部分條款出現制裁字樣或者暗示刑事制裁的可能性②,后者則致力于私法規則的統一,無刑事規制條款。
早期嘗試對文化財產的非法販運行為進行刑事規制的主要文件包括兩份:《防止侵犯各國動產文化遺產犯罪行為的示范條約》(以下簡稱《1990年示范條約》)以及歐洲理事會出臺的《關于文化財產犯罪的歐洲公約》。前者于1990年在聯合國第8次關于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大會上通過,后者于1985年簽訂于特爾斐(以下簡稱《1985年特爾斐公約》)。《1990年示范條約》的條文較為簡單,除前言外,共5條。《1985年特爾斐公約》的條文較多,但沒有引發太多關注。迄今為止僅有6個國家簽字,沒有國家批準,也沒有生效③。隨著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的日益猖獗以及文化遺產保護意識的增強,國際社會強化了對該行為的刑事規制。
一、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國際刑事規制的強化動向
進入21世紀,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的國際刑事規制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切的問題。這不僅體現在更多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大會和安全理事會(以下簡稱安理會)在此議題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且直接以刑事規制為題的國際文件相繼出臺,其所涵括的內容更為全面明晰。大體而言,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國際刑事規制的強化動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參與機構的擴展。
文化財產事項傳統上由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以下簡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負責,《1970年教科文組織公約》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導制定,《1995年UNIDROIT公約》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請求下,由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制定通過。時至今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仍然在文化財產事項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更多的機構參與打擊文化財產的非法販運行為,其中聯合國大會以及安理會的作用非常突出。
聯合國大會多次通過專門決議強調對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的刑事規制,如其在2011年和2013年分別通過了題為“加強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對策以保護文化財產,尤其是防止文化財產被販運”的66/180號決議和68/186號決議。2014年,其不僅通過了69/196號決議,而且將《關于販運文化財產及其他相關犯罪的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對策國際準則》(以下簡稱《2014年國際準則》)作為決議的一部分。
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的國際刑事規制也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經常議題。其在第2199號決議(2015年),第2253號決議(2015年)以及第2322(2016年)號決議中都提及各國應當進行國際合作,防止和打擊恐怖主義分子或者組織非法販運文化財產并促進非法販運文化財產的返還。第2347號決議(2017年)是聯合國安理會出臺的第一份直接以文化財產為議題的決議,不僅重申各國應防止和打擊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并且敦促各國采取諸如完善文化財產清單和數據庫,制定文化財產進出口規章,與世界海關組織以及國際刑警組織進行合作,提升文化財產保護意識等具體措施。
其二,新文件的制定和頒布。
晚近國際社會出臺了兩份重要文件,即《2014年國際準則》和《歐洲理事會關于文化財產犯罪的公約》(以下簡稱《2017年公約》)。前者于2014年公布并被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后者2017年由歐洲理事會通過。這兩份文件直接對文化財產非法販運及其相關行為進行刑事規制。
《2014年國際準則》在性質上與《1990年示范條約》相同,都是軟法性文件,不具有強制性。但是,前者共有48條,包括“預防措施”“刑事司法政策”“國際合作”以及“適用范圍”四大部分,比后者的內容更加豐富。而且不同于《1990年示范條約》,《2014年國際準則》構成聯合國大會決議的一部分。《2017年公約》雖然由歐洲理事會發起,但與《1985年特爾斐公約》不同,其從最初就被設計為開放性的、全球導向的保護人類共同文化遺產的公約,成員資格并不限于歐洲理事會成員。《2017年公約》已有13個簽字國,其中5個國家已經批準,包括非歐洲理事會成員的墨西哥,于2022年4月1日生效④。
《2014年國際準則》與《2017年公約》性質不同,前者是軟法性文件,后者是條約。但是,二者都采用刑事方式規制文化財產的非法販運行為,且前者的出現促進了后者的產生。
其三,具體規則更為全面明晰。
近期文件更多的是從整體上規制文化財產的非法販運行為,強調預防措施和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且對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相關罪名進行了較為明確的規定。預防措施以及國際合作在早期的文件,如《1970年教科文組織公約》以及《1995年UNIDROIT公約》中已被多次強調。《2014年國際準則》和《2017年公約》秉承這一傳統,前者將預防策略置于文件的第1部分,包含12條準則。后者第4章用了兩個條文規定了締約方可以采取的國內、國際預防措施。聯合國安理會第2347號決議也羅列了締約國應當采取的預防措施。同時,由于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大多跨越國境,國際合作也成為晚近文件的重要主題。聯合國大會、安理會的決議,《國際準則》和《2017年公約》都強調調查、扣押、沒收等事項上應進行國際合作。后兩份文件還強調應將文化財產非法販運犯罪視為可引渡犯罪,且在引渡事項上各國應當進行合作。
近期文件還對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相關罪名作了較為明晰的規定。非法販運文化財產行為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前者是指將限制或者禁止進出口的文化財產走私出境或入境的非法行為,后者還包括與非法販運密切相關的上下游行為[1]。在具體罪名的設置上,近期文件都試圖從廣義的角度,對文化財產非法販運的上下游行為進行整體規制。《2014年國際準則》的“刑事司法政策”部分建議各國將“非法販運文化財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盜竊文化財產、盜掠古遺址和文化遺產及(或)進行非法挖掘、圖謀販運文化財產、參加有組織犯罪集團販運文化財產以及相關行為,以文化財產洗錢等行為”規定為嚴重刑事犯罪,將“與販運文化財產相關的其他犯罪,如損毀或破壞文化財產,或者以故意規避法律地位的方式收購被販運的文化財產”規定為犯罪。而《2017年公約》則更為明確,將犯罪分為兩大類:非法販運文化財產相關犯罪以及毀損文化財產罪。公約第3到第9條規定了與非法販運文化財產相關的7種罪名:盜竊罪以及其他形式的非法占有罪;盜掘罪和非法轉移罪;非法進口罪;非法出口罪;明知或應知來源非法而獲取罪;明知或應知來源非法而投放市場罪;偽造文件罪。公約第10條“毀損文化財產罪”規制兩種行為:非法毀損可移動或者不可移動文化財產以及非法從可移動或者不可移動文化財產上轉移其構成部分,用于非法進出口或者投放市場。這些行為僅在行為人主觀上出于故意時才構成犯罪。對于非法進口、非法獲取以及非法投放市場三種行為,公約還要求行為人知悉文化財產的來源為非法才構成犯罪。后兩種行為,如果行為人履行了盡職調查義務,應當知道文化財產的來源是非法的,而行為人沒有盡到此義務,公約要求締約國也應當考慮將其規定為犯罪。
二、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國際刑事規制強化的主要原因
刑法作為最終的救濟手段,應當審慎運用,而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的國際刑事規制呈強化動向,這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的后果極為嚴重
據統計,文化財產非法貿易已成為繼毒品和非法武器貿易之后,最為賺錢的跨國有組織犯罪之一[2]。大量從文化遺產豐富的國家和地區盜掘、盜竊的物品,經過多次國際流轉,最終流入文化遺產需求旺盛的國家和地區的博物館、藝術館或者私人收藏者的保險箱。
文化財產非法販運及伴隨的破壞行為不僅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某些文化財產還是特定人群精神的歸依,其破壞和非法販運會造成劇烈的情感傷害。另外,從考古遺址或者類似地方盜掘文化財產更有可能使其背后的歷史線索及科研價值喪失殆盡。
文化財產非法貿易所獲取的巨大收益也遭到恐怖主義組織的覬覦,近年來,非洲以及中東部分國家動蕩的局勢又為此提供了便利。這些組織不僅破壞文化遺產用以提升自身的影響力,如ISIS(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成員不僅手拿大錘和電鉆瘋狂破壞伊拉克摩蘇爾地區的古文物,而且對敘利亞帕爾米拉古城予以大規模毀損。這些行為被恐怖組織通過推特等社交媒體公之于眾,引發全世界的關注。而且在這些文化遺產被掠被毀行為背后,伴隨著龐大的非法交易市場及巨大的非法收益,而這些收益又被用來支持進一步的暴力行動[3]。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直接威脅著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
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后果的嚴重性使國際社會意識到刑事規制的必要性。相較于《1970年教科文組織公約》以及《1995年UNIDROIT公約》主要強調非法文化財產的返還,刑事規制所獨有的功能和作用,能對行為人產生更強的威懾力,從而避免或者減少非法販運文化財產行為的發生。
(二)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具備跨國性特點
無論合法還是非法的文化財產貿易都具有跨國性的特點。早在1986年,研究國際文化遺產法的重要學者梅里曼教授(John Henry Merryman)將國家分為兩類:文化財產來源國和文化財產市場國[4]。來源國是指在國際市場上,文化財產資源供大于求的國家。這類國家資源豐富但大多比較貧窮,如墨西哥、埃及、印度等。市場國是指在國際市場上,文化財產資源求大于供的國家。這類國家對文化財產的需求旺盛且比較富裕,如美國、瑞士、德國、日本等。市場國對文化財產的渴求推動著國際文化財產貿易的發展,這導致大量從來源國合法或者非法取得的文化財產,經過中間國家或者地區流入市場國。我國宋代章公祖師肉身坐佛像的境遇即是如此:該佛像于1995年12月在福建省三明市大田縣吳山鄉陽春村普照堂被盜,隨后被運至香港,由荷蘭藏家在香港購買并帶往荷蘭,并在1996年由現持有人收購于阿姆斯特丹。多年以后,供奉佛像的鄉民偶然得知佛像信息,雖經多次追索,但仍未返回故土[5]。
文化財產的跨國流動以及各國法律的差異,制造出種種法律漏洞。犯罪分子通過這些漏洞,先將來源不明或者非法的文化財產運抵瑞士或者香港等地的免稅地點,再通過各種機制,制造文化財產的“合法”出口文件或者“合法”來源[6]。之后,這些經過“漂白”的文化財產就可以大大方方出現在市場供各方買家挑選。
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的這一特點使得單個國家的打擊行為不足以對其進行規制。出臺國際文件,促使各國在打擊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方面進行合作,成為國際社會的必然選擇。
(三)“人類共同遺產”理念的推動
人類社會早期已經閃耀著保護文化財產的火花,但主要基于宗教感情、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區分或者對公私物品的籠統保護。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文化財產的破壞和掠奪使整個國際社會震驚,戰爭結束之后,文化財產保護意識逐漸增強,而文化財產是人類的共同遺產,對某國或者某地文化財產的破壞不僅是所在地的損失,也是全人類的損失的理念開始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1954年《關于發生武裝沖突時保護文化財產的公約》(以下簡稱《1954年海牙公約》)首次在條約中確認這一理念,其前言部分強調“深信屬于任何人民的文化財產如遭受到損失,也就是全人類文化遺產所遭受的損失,因為每國人民對世界文化做出其自己的貢獻”。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前言重申了這一點,強調“保護不論屬于哪國人民的這類罕見且無法替代的財產,對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某些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而需作為全人類世界遺產的一部分加以保存”。2001年《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的前言部分亦再次強調這一理念。
除此之外,針對阿富汗塔利班摧毀被授予世界遺產稱號的巴米揚大佛事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臺了《關于蓄意破壞文化遺產問題的宣言》,再次強調文化遺產屬于“人類共同遺產”。同時,該宣言還將文化財產的保護與人的尊嚴和人權相連,要求銘記“文化遺產是社會、群體和個人的文化特性和社會凝聚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蓄意破壞文化遺產會對人的尊嚴和人權造成不利影響。”2020年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因那卡地區歸屬問題發生沖突造成大量文化財產被毀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此作出聲明,再次重申文化遺產的國際屬性,以及作為歷史見證和民族特征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7]。
總之,文化財產是人類共同遺產,與個人、民族的尊嚴和人權緊密相連的理念在國際社會已達成共識。文化財產應當受到國際性的保護,對文化財產的非法販運與破壞應當得到國際刑法的規制。
三、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國際刑事規制的強化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一直重視對文化財產的保護,已經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70年教科文組織公約》《1995年UNIDROIT公約》,以及《1954年海牙公約》及其議定書。我國也已經與一些國家,如瑞士、美國、秘魯、印度、意大利、菲律賓、希臘、智利、塞浦路斯以及委內瑞拉等簽訂了雙邊文化財產保護協議。我國還曾派遣代表團參加在維也納召開的第三次“保護文物免遭販運問題政府間專家組會議”,促成了《2014年國際準則》的出臺。
文化財產的國內刑事規制主要見于《文物保護法》和《刑法》。根據這兩部法律,構成犯罪的行為包括: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故意或者過失損毀國家保護的珍貴文物的;擅自將國有館藏文物出售或者私自送給非國有單位或者個人的;將國家禁止出境的珍貴文物私自出售或者送給外國人的;以牟利為目的倒賣國家禁止經營的文物的;走私文物的;盜竊、哄搶、私分或者非法侵占國有文物的;失職造成珍貴文物損毀、流失的。除此之外,《刑法》中的有些條款雖然沒有出現“文物”字樣,但是對于打擊文物犯罪也具有重要意義,如其對洗錢罪,盜竊罪⑤,“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及對“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盜竊、搶奪、毀滅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偽造、變造、買賣身份證件罪”的規定。
從現實來看,我國的歷史悠久,文化財產豐富,但其毀損、流失也極為嚴重,盜掘古墓葬、古文化遺址并非法出口,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且仍在持續。隨著藝術市場在我國的火爆,也存在非法文化財產入境的可能性。因此,我國有必要關注和研究國際社會強化刑法規制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的新動向,并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
第一,我國應當樹立從整體上規制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的理念。
如前所述,晚近的國際文件都強調對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進行整體規制。強化預防措施,重視司法審判,且強調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司法審判和預防措施并重是現代刑事司法政策的發展趨勢之一。刑事責任是最后的救濟,如果能夠采取預防措施,將文化財產犯罪扼殺于搖籃之中,則不失為更明智的選擇。不僅如此,文化財產保護規則及其懲罰措施能否發揮實際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是否構筑了有效的預防措施。因此,我國應當重視預防措施,加強對文化財產的清查工作,完善文化財產清單和數據庫。同時培養更多的文化財產方面的人才,提升文化財產的數字化保護和安全防范水平。另外,跨國性特點也使得國際合作成為打擊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的重要措施。我國應當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打擊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我國不僅應重視研究《2014年國際準則》及其《操作指南》,尋求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如國際刑警組織、國際被盜文化財產和藝術品相關的數據庫的合作。我國也應當時刻關注《2017年公約》的發展,考慮加入的可能性。同時,我國還應當積極尋求與其他國家,特別是文化財產市場國進行雙邊和多邊合作,以有效預防和打擊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
第二,我國應當借鑒國際文件中的具體規定,審視和修訂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犯罪的立法。
一是應考慮將非法進口文化財產行為入刑。“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受到《1990年示范條約》、《2014年國際準則》以及《2017年公約》的規制。我國《刑法》第151條第2款規定了走私文物罪,其措辭是“走私國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這表明我國走私文物罪的行為對象是國家禁止出口的文物。二者的實質區別在于非法進口行為是否構成犯罪。
《1970年教科文組織公約》是現行的主要規制文化財產非法進出口及促進其返還的公約,第8條將制裁規定為:“本公約締約國承擔對觸犯上述第6條(2)和第7條(2)所列的禁止規定負有責任者予以懲處或行政制裁”,而這兩款就是分別針對文化財產的非法出口行為和非法進口行為。因此,非法進口行為受到該公約的明確禁止。實踐中,一些國家規定了進口限制,但其方式有區別。如美國和瑞士選擇采用雙邊協議來補充《1970年教科文組織公約》,從而執行進口限制。加拿大自1985年,德國自2016年規定了普遍的進口限制規則[8]。澳大利亞⑥以及英國⑦也有類似規定。
因此,文化財產的非法進口行為應受到規制已經為《1970年教科文組織公約》所明確,考慮到該公約締約國已經超過140個,該理念毫無疑義已成為國際共識。我國于1989年加入《1970年教科文組織公約》,是其成員國之一,而條約必須信守是條約法的基本準則。而且,文化財產的非法進口行為是導致文化財產流失和毀損的重要環節。因此,從履行條約義務以及更好地打擊文化財產非法販運和毀損兩個方面看,我國應當采取措施規制文化財產的非法進口行為,且應當考慮在將來的刑事立法中增加非法進口文物罪。
二是應吸收“明知或應知非法文化財產而獲取或者投放市場罪”的合理因素,增加“應知”這一主觀要件,且明確規定“盡職調查義務”條款⑨。
《2017年公約》第7條“明知或應知非法文化財產而獲取罪”以及第8條“明知或應知非法文化財產而投放市場罪”,其相應規定為我國《刑法》第312條“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關于辦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進一步將其闡釋為“明知是盜竊文物、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等犯罪所獲取的三級以上文物,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加工、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依照刑法第312條的規定,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責任。實施前款規定的行為,事先通謀的,以共同犯罪論處。”二者規制的行為類似,但存在區別。
《2017年公約》的主觀要件包括“明知或應知”,而我國僅規定“明知”。也即依據公約,如果行為人履行了盡職調查義務,應當知道文化財產的來源是非法的,而行為人沒有履行該義務構成犯罪。文化財產市場有漠視來源的傳統,且常有精英人士參與,合法和非法貿易交織在一起,如果不對市場參與者施加應有的盡職調查義務,促使其盡量調查文化財產的來源,就會大大增加來源不明文化財產在市場流通的機會。反之,要求參與者,如博物館、藝術館以及私人收藏者在將文化財產投放市場或者獲取文化財產時,對其進行溯源則能減少來源不明文化財產在市場的流動。盡職調查義務在國際文件中已得到廣泛確認。《1970年教科文組織公約》第10條第1款提及盡職調查義務并規定對其不履行可能導致刑事或者行政制裁⑧。《1995年UNIDROIT公約》不僅強調行為人的盡職調查義務,且明確是否履行該義務影響補償,其第4條第1款規定“占有人只有不知道也理應不知道該物品是被盜的,并且能證明自己在獲取該物品時是慎重的,則在返還文物時有權得到公正合理的補償”。第4款進一步闡明了“何為慎重”:“確定占有人是否慎重時,應注意到獲得物品的情況,包括當事各方的性質、支付的價格、占有人是否向通常可以接觸到的被盜文物的登記機關進行咨詢,他通常可以獲得的其他有關信息和文件、占有人是否向可以接觸到的機關進行咨詢。或者采取一個正常人在此情況下應當采取的其他措施。”除此之外,國際博物館協會的《博物館道德守則》對博物館的盡職調查義務作了較為嚴格的規定,規定博物館“在確定以購買、贈送、借用、遺贈或交換的方式征集物品和標本之前,必須以各種方式保證其不是從其原物主國或任何該物品可能會被合法擁有(包括博物館所在國)的中間國非法取得或非法進口的。基于上述原因,考證工作應準確了解該物品從發現或制作完成后的全部歷史。”因此,盡職調查義務條款已經被各種國際文件廣泛采納,在此基礎上,《2017年公約》進一步規定未履行該義務可能入刑。
反觀我國,《文物保護法》第37條規定博物館、圖書館和其他文物收藏單位可以通過購買、接受捐贈、依法交換、指定保管或者調撥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方式獲得文物,但這主要闡明專業機構獲取文物的方式,而對于獲取文物時是否應履行“盡職調查義務”,沒有作出明確規定。2016年實施的《藝術品經營管理辦法》第10條規定了盡職調查義務,但該辦法不適用于文物。2021年出臺的《國有博物館藏品征集規程》第5條提及盡職調查義務,規定博物館購買藏品時應對“擬征集物的真實性、來源合法性、是否符合征集方向進行初審”。但這一規定僅針對國有博物館,且效力層級較低。
如前所述,對文化財產來源的有意或者無意的漠視,是對文化財產非法貿易的縱容。因此,為了增加文化財產市場的透明度,更好地打擊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我國應當在將來的立法中納入“盡職調查義務”,明確規定文化財產市場參與人,尤其是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士應該對文化財產的來源進行必要的調查。且在將來的刑事立法中,考慮增加“應知”這一主觀要件,如果行為人不履行或者沒有充分履行盡職調查義務,不僅要承擔民事上的不利后果,而且其行為可能入刑。
文化財產作為人類共同遺產的組成部分以及民族文化和特征的獨特的重要證據具有重要意義,對文物的保護“功在當代,利在千秋”[9]。隨著文化遺產保護意識的增強,我國加入了主要的文化遺產公約,國內法律逐步完善。但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有待于進一步提升,對利益的追逐使得破壞和非法販運文化財產的行為亦大量存在。因此,我國應當關注國際社會強化刑事規制文化財產非法販運行為的新動向。雖然討論我國應否加入相關條約在現階段為時尚早,但不能否認相關國際文件對我國文化財產立法的積極意義。我國應當研究這些文件及其發展,并就此審視和完善我國文化財產犯罪的相關立法。
注釋:
① 文化財產也稱文化遺產或者文物,雖對其內涵和外延有不同的理解,但本文在互換的意義上使用三者。且本文僅討論“物質性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在討論之列。
② 參見《1970年教科文組織公約》第8條、第10條第1款以及第13條。
③ 參見歐洲理事會網站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119/signatures?p_auth=G1TEcytV,最后訪問日期:2021年12月27日。
④ 這13個簽字國是:亞美尼亞、塞浦路斯、希臘、意大利、拉脫維那、黑山共和國、葡萄牙、俄羅斯、圣馬力諾、斯洛文尼亞、烏克蘭、墨西哥和匈牙利。5個批準國是塞浦路斯、墨西哥、希臘、拉脫維亞以及匈牙利。其中,墨西哥是非歐洲理事會成員國。參見歐洲理事會網站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221/signatures?p_auth=2L13Nhen,最后訪問日期:2021年12月27日。
⑤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盜竊一般文物、三級文物、二級以上文物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盜竊文物,無法確定文物等級,或者按照文物等級定罪量刑明顯過輕或者過重的,按照盜竊的文物價值定罪量刑。
⑥ See Protection of Movable Cultural Heritage Act,1986,Section 14.
⑦ See Dealing in Cultural Objects (offences) Act 2003.
⑧ 該條款的具體內容如下:“本公約締約國承擔:通過教育、情報和防范手段,限制非法從本公約締約國運出的文化財產的移動,并視各國情況,責成古董商保持一份記錄,載明每項文化財產的來源、提供者的姓名與住址以及每項售出的物品的名稱與價格,并須把此類財產可能禁止出口的情況告知該項文化財產的購買人,違者須受刑事或行政制裁。”
⑨ 盡職調查義務在不同的文件中措辭不完全相同。如《2017年公約》采用“due care and attention”,《1995年UNIDROIT公約》和《博物館道德守則》采用“due diligence”,《1995年UNIDROIT公約》對應的中文文本為“慎重”,我國《藝術品經營管理辦法》采用“盡職調查”。這些表述的內涵和外延細究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本文在互換的意義上使用。
[參考文獻]
[1] 周曉永,黃風.跨國非法販運文化財產犯罪界定與國際刑事合作[J].人民檢察,2014(13):18.
[2]Sandro Calvani.Frequency and Figures of Organized Crime in Art and Antiquities[M]//Stefano Manacorda.Organised Crime in Art and Antiquities World.Milano:ISPAC,2009:30.
[3]Jamie Brown.The 2017 Blood Antiquities Convention:Protecting Cultural Property through Criminal Law[EB/OL].(2017-07-04)[2021-12-27].https://grojil.org/?s=+Jamie+Brown.
[4]John Henry Merryman.Two Ways of Thinking about Cultural Property[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86,80(4):831-853.
[5]霍政欣,陳銳達.跨國文物追索:國際私法的挑戰及回應:從“章公祖師肉身坐佛案”展開[J].國際法研究,2021(3):106-128.
[6]Duncan Chappell,Kenneth Polk.Unraveling the “Cordata”:Just How Organized Is the 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Cultural Objects?[M]//Stefano Manacorda.Organised Crime in Art and Antiquities World.Milano:ISPAC,2009:105.
[7]UNESCO.Nagorno-Karabakh:Reaffirming the Obligation to Protect Cultural Goods,UNESCO Proposes Sending a Mission to the Field to All Parties[EB/OL].(2020-11-20)[2021-12-27].https://en.unesco.org/news/nagorno-karabakh-reaffirming-obligation-protect-cultural-goods-unesco-proposes-sending-mission.
[8]Robert Peters.Preventing Trafficking in Cultural Property:Import and Export Provisions as style: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J].Santander Art and Culture Law Review,2019(2):99-100.
[9]內蒙古自治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習近平:保護文物功在當代利在千秋[EB/OL].(2016-07-26)[2021-12-27].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608/c40531-29327553.html.
(責任編輯 文 格)
Analysis on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riminal Regulations on Illicit Trafficking of Cultural Property
HU Xiu-juan
(School of Law,Humanities and Sociology,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Hubei,China)
Abstract:In the international panorama,there has recently been a trend towards favoring a greater us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gainst “illicit trafficking in cultural property”.This trend is reflected in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this issue and the issuance of new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with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pecific contents.The trend towards criminalization is based on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the act of illicit trafficking and its transnational characteristic,also on the concept of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Under this trend,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strengthen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ombating against illegal trafficking of cultural property.China should also review and revise its cultural property legislation in terms of new international rules.Therefore we should regulate the import of cultural property,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criminal punishment,and add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and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ies of participants in the cultural property market.
Key words:cultural property; illicit trafficking;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due dili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