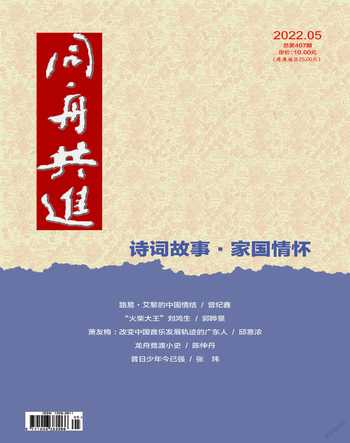孫犁創作《鐵木前傳》前后
劉運峰


在學術界,人們往往認為孫犁前期的創作可以用自然、清新、質樸來概括,后期的創作可以用雋永、深沉、老到來形容,兩者之間固然存在著一定的承接性,卻又有著明顯的不同。
如果說,孫犁前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什么,最為經典的作品是什么,能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定分量的作品是什么,可以毫不猶豫地回答:是他的中篇小說——《鐵木前傳》。
《鐵木前傳》是孫犁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小說。他平生唯一一部長篇小說、也是部頭最大的作品《風云初記》,從動筆到基本完成,用了將近4年時間,篇幅為27萬字;而《鐵木前傳》只有4.5萬字,寫作時長卻超過3年。
全副身心釀佳作
1949年1月15日,天津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孫犁隨著解放大軍來到《天津日報》,成為了那里的一名編輯,從此沒有離開過。城市生活對于孫犁來說是陌生的,他有許多不適應。尤其是進城之后的“人和人的關系,因為地位,或因為別的,發生了在艱難環境中意想不到的變化”。孫犁很為這種變化而苦惱,他需要暫時離開這個環境,需要在熟悉的生活中得到慰藉,尋找答案。
孫犁想起了過去的朋友,想到了童年時期的經歷。晚年的孫犁曾在一首《題照》詩中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和處境:“曾隨家鄉水,九曲入津門。海河風浪險,幾度夢驚魂。故鄉月皓朗,天津日昏沉。烏鵲避地走,不聞故鄉音。”他創作的源泉在農村,他擅長的是農村題材的小說和散文。“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于是,1952年初冬,他向報社請了長假,來到了河北省安國縣的農村。
安國,古稱祁州,為藥材集散之地,是北方有名的“藥都”,也是孫犁的第二故鄉。在他11歲的時候,孫犁就隨父親來到安國縣城,考入高級小學,度過了兩年時光。那里的風土人情給孫犁留下了深刻印象。
孫犁到安國的第一站是縣城北部50里的于村,之后又到了縣城南部12里的長仕村。在這兩個村莊,孫犁遇到了他童年時期熟悉的老一代人,結識了正在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年輕人。大約半年后,孫犁回到天津,他除了寫作《風云初記》第三集外,還根據下鄉的所見所聞寫了《楊國元》《訪舊》《婚俗》《家庭》《齊滿花》等散文,以“農村人物速寫”為題,陸續發表在《天津日報》上,這可以說是孫犁為寫作《鐵木前傳》所做的前期準備。
1953年夏天,孫犁開始了《鐵木前傳》的寫作。小說從童年時期對鐵匠和木匠的印象寫起,逐漸深入到社會生活變遷所引起的人際關系變化,以及年輕一代在面對新社會、新生活時所做出的選擇。盡管孫犁在創作上已趨于成熟,而且《村歌》《風云初記》的發表給孫犁帶來了很高的聲譽,他的寫作條件也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這部小說卻寫得異常艱難,幾乎傾注了他的全部身心。
關于《鐵木前傳》的創作,孫犁在1979年致評論家閻綱的信中說:“這本書,從表面看,是我1953年下鄉的產物。其實不然,它是我有關童年的回憶,也是我當時思想感情的體現。”正因為傾注了自己的全部身心,小說中的每個字、每句話,都是用“紙的砧,心的錘”反復打造出來的。孫犁自己曾說,這部小說他是可以通篇背誦下來的。1956年3月29日,因過于勞累,孫犁在午休后去衛生間時突然暈倒,將左腮磕破。妻子、孩子聞聲趕來,趕緊把滿臉是血的他送去醫院,臉頰縫合了數針,所幸沒有大礙。但從此之后,孫犁不得不暫時放下手中的筆,以至于“十年廢于疾病”。
盡管孫犁為寫作《鐵木前傳》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發表卻并不順利。由于《風云初記》第三集的大部分發表于《新港》雜志,因此孫犁首先想到把這部新作交給《新港》。遺憾的是,對于孫犁的這部嘔心瀝血之作,負責編輯部日常工作的兩位年輕人不僅不說它的好處,反而說這個不好,那個不行,發表出去對孫犁名聲不利,竟然做了退稿處理。
隨后,孫犁將《鐵木前傳》轉給《人民文學》。擔任《人民文學》主編的秦兆陽一口氣讀完,擊節贊賞,對孫犁作品的知音、作家康濯說,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小滿兒寫得比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中的路希卡還要美,果斷決定在1956年第12期作為頭條發表。作家方紀閱讀之后,也認為這是孫犁創作的最高峰。
《鐵木前傳》的發表標志著孫犁創作風格的成熟,這部小說受到了文壇的矚目和評論家的關注。小說并沒有涉及轟轟烈烈的大事件,也沒有描寫叱咤風云的大人物,而是寫冀中農村的凡人瑣事,正是通過這些有血有肉的小人物,折射出了新舊交替的社會大背景。孫犁筆下的這些人物,有的倔強如鐵匠傅老剛,有的精明如木匠黎老東,有的勤勞如九兒,有的懶散如六兒,有的張揚如小滿兒,有的本分如四兒,但是,孫犁并沒有給這些人物貼上標簽,而是按照事物自然發展的脈絡來塑造人物形象,這些人就如同在我們身邊,真實而親切。可以說,孫犁是對魯迅先生所倡導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繼承。
這部《鐵木前傳》給孫犁帶來了聲譽,也帶來了艱困。為了寫作,他的身體每況愈下。1975年4月12日,孫犁在《鐵木前傳》的書衣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此四萬五千字小書,余既以寫至末章,得大病。后十年,又以此書,幾至喪生。則此書于余,不祥之甚矣。然近年又以此書不存,頗思得之。春節時,見到林吶同志,囑其于出版社書庫中,代為尋覓。昨日,林以此本交人帶來,附函喻之以久別之游子云:‘當他突然返回家鄉時,雖屬滿面灰塵,周身瘡痍,也不會遭遇嫌棄的吧?……嗚呼,書耳,雖屬上層建筑,實無知之物,遭際于彼,并無喜怒。但能反射影響于作者,而作者非謂無知無情。世代多士,戀戀于斯,亦可哀矣。”可見,孫犁對這部作品的復雜感情。
經典插圖永流傳
《鐵木前傳》的單行本于1957年1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收入了四幅線描插圖,可惜的是,這些插圖沒有注明作者。小說首印16130冊,很快銷售一空。
1959年7月,剛剛從天津人民出版社獨立出來的百花文藝出版社推出了《鐵木前傳》的新版本。這一版本與初版最明顯的不同,是以四幅水粉畫代替了原來的線描插圖,其作者是張德育。

張德育(1931—2010),河南南陽人,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5年入中央美術學院學習,1958年畢業后分配到百花文藝出版社擔任美術編輯。張德育受過正規的專業訓練,以人物畫見長,此前,他已經為馮德英的長篇小說《苦菜花》畫過插圖,深受好評。
張德育剛到出版社,便翻看了出版社的樣書,當讀到《鐵木前傳》的時候,立即被吸引住。他一口氣讀完,覺得這樣的好書一定要有好的插圖,于是找到社長林吶,建議重新出版《鐵木前傳》,并主動請纓,要求下農村體驗生活、收集形象,為小說畫插圖。出版社經過研究,同意了他的想法。張德育在冀中農村經過一個月的生活體驗后,回到單位專心致志地進行插圖的繪制,盡管只有四幅,卻用去了兩個月的時間。
插圖完成后,很快通過,于是,百花文藝出版社在1959年7月推出了新版的《鐵木前傳》,印數達19100冊。之后又多次重印,依然保留了這四幅插圖。
對于張德育的插圖,孫犁非常滿意。多年后,張德育對孫犁的小女兒孫曉玲講述了當時隨林吶拜訪孫犁的情景:
在多倫道大院那個帶陽臺的屋子里,我第一次見到自己崇敬的作家,他不像想象中的作家那樣威嚴,倒像是個農村的老師。他說話不像他用文字表達情感那樣自如,但平易近人。孫犁先生見到我,便招呼老伴:“德育來了,畫《鐵木前傳》的,你來看看。”你母親從廚房走出來,笑著對我說:“你見過小滿兒吧!”她是個很樸實的農村婦女,可說話挺有意思。我對她說:“大娘,您沒想到吧?!我這個歲數不可能見過小滿兒。我畫的只是我心里的一種感情表達。”你母親認定我見過原型,這也從一方面說明我畫的的確像小滿兒。我對你母親說,不是我畫得好,而是孫犁先生對現實生活挖掘得深刻,寫得生動,文字表達又是那么優秀……我被感動了,被他帶進了那個環境,與他筆下人物的情感融為了一體。

《鐵木前傳》的插圖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家鐵凝在《懷念插圖》一文中寫道:“我第一次讀孫犁先生的中篇小說《鐵木前傳》是在二十歲以前……當時除了被孫犁先生的敘述所打動,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畫家張德育為《鐵木前傳》所作的幾幅插圖。其中那幅小滿兒坐在炕上,一手托碗喝水的插圖,尤其讓我難忘。”“畫中的小滿兒,在深夜來到住在她家的干部屋里,倚坐在炕上毫不扭捏地讓干部給她倒一碗水。深夜的男女單獨相處,村人對她的種種傳聞,使干部對她心生警惕。然而她落落大方地與干部閑聊,探討怎樣才能了解人的內心。這時她的眼光甚至是純凈的,沒有挑逗的意味,雖然在這個晚上她美艷無比,頭上那方印著牡丹花的手巾,那朵恰巧對在額前的牡丹花給整個的她籠罩上一層神秘而又孤傲的色彩,使人想到,在輕佻和隨便的背后,這女人情感深處也有著諸多的艱難和痛苦。”
鐵凝認為,“這幅插圖的藝術價值并不亞于孫犁先生這部小說本身”。“張德育先生的插圖,用著看似簡單的中國筆墨,準確、傳神地表現出一個文學人物的血肉和她洋溢著別樣魅力的復雜性格,實在讓人敬佩。中國至今無人超越張德育這幾幀國畫插圖的高度,他自己也未能再作超越”。
的確,后來由于紛繁復雜的行政工作,張德育未能盡展其才,實現藝術上的突破。但是,無論當時,無論現在,無論將來,張德育為《鐵木前傳》繪制的這四幅插圖都無愧為經典之作。
(作者系南開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