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塑三代
常懷穎
中國有梳理學(xué)術(shù)史的傳統(tǒng)。與傳統(tǒng)學(xué)問不強(qiáng)調(diào)分科一樣,中國學(xué)術(shù)史的研究向來有較大的彈性,既可以是《國故論衡》《中國近三百年學(xué)術(shù)史》《國朝漢學(xué)師承記》這樣的長時(shí)段的觀察,也可以是小切口、專題的個(gè)案分析。無論是大是小,都是看某一類問題的發(fā)展方向,是當(dāng)下對既往的疏通和總結(jié)。說得宏大些,學(xué)術(shù)史是厘清“道統(tǒng)”的路向;說小些,學(xué)術(shù)史讓學(xué)科和問題的勾連與糾纏得以條分縷析,對后來學(xué)子了解學(xué)科、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脈絡(luò)、走向與得失,培養(yǎng)問題意識,都大有裨益。
學(xué)術(shù)史往往也是為未來保存過去的一種手段。由于學(xué)科范式、問題取向和學(xué)者地位會各領(lǐng)風(fēng)騷數(shù)十年,往往會有學(xué)者和學(xué)說因地位、范式的變化,而成為學(xué)科發(fā)展史上的“失蹤者”。因之,學(xué)術(shù)史有不斷“重寫”的必要。換言之,這種“重寫”是以對價(jià)值的“重估”為背景的,它表達(dá)的不但是這一代學(xué)人的“認(rèn)識”,也更是在追溯歷史本來的面目。
考古學(xué)是個(gè)小眾學(xué)科,誕生至今也不過二百年左右,在中國更是不過區(qū)區(qū)百年。對考古學(xué)史的梳理,相較于歷史積淀更久的學(xué)科而言,看似有些“操之過急”。但實(shí)際上,考古學(xué)史的作用,除了回顧學(xué)科發(fā)展歷程、提醒被忽略的材料、設(shè)法讓考古學(xué)研究更加客觀少走彎路、紀(jì)念重要的考古學(xué)家這些常見目標(biāo)之外,往往還有紀(jì)念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為某些研究結(jié)論、體系和研究者本人正名,厘清文物或遺存發(fā)掘、收藏和傳承過程的作用。更現(xiàn)實(shí)的問題是,雖然僅過了百年,但與最初的樣態(tài)相比,中國考古學(xué)的發(fā)展變化顯然超出了學(xué)科出現(xiàn)時(shí)的預(yù)設(shè),其發(fā)展也遠(yuǎn)非線性,甚至已經(jīng)出現(xiàn)研究者隱去、研究分歧淵源模糊的情況。
也正因如此,從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開始,中國考古學(xué)學(xué)術(shù)史寫作漸多。但較顯見的現(xiàn)狀是,相關(guān)研究集中于一九四九年以前,而罕見當(dāng)代的學(xué)術(shù)史梳理;對機(jī)構(gòu)、人員分析多,對學(xué)術(shù)問題清通少;考古學(xué)者分析整理多,非考古學(xué)專業(yè)出身的學(xué)者極少參與。除陳星燦對一九四九年以前史前考古的學(xué)術(shù)史研究外,對中國各時(shí)段考古學(xué)史梳理中,對學(xué)術(shù)問題流變、學(xué)術(shù)取向轉(zhuǎn)換的研究極少,這種現(xiàn)象與研究者是否能準(zhǔn)確把握學(xué)科發(fā)展動態(tài)、學(xué)力的深淺息息相關(guān)。這些現(xiàn)狀固然與考古學(xué)自身的話語體系相對獨(dú)立、研究對象多為物質(zhì)遺存,令未受專業(yè)訓(xùn)練的其他學(xué)科研究者對具體學(xué)術(shù)問題難以評判、分辨有關(guān)系。但也毋庸諱言,上述現(xiàn)象與考古學(xué)行業(yè)小,從業(yè)人員多有師承友朋關(guān)系,難免產(chǎn)生“為尊者諱”的心態(tài),不便分析較近的時(shí)代、較具體的研究問題直接相關(guān)。這種環(huán)境下,對夏商周考古學(xué)史的研究就更顯珍貴。
夏商周時(shí)代考古重要,一方面,是因它與中國考古學(xué)同時(shí)起步,在很長的一段時(shí)間內(nèi)甚至密不可分,往往以三代考古可見中國考古學(xué)之一斑。一九四九年以前,“古史辨”思潮影響中國古代史研究,焦點(diǎn)集中在三代考古遺存之上。因?yàn)榭谷諔?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當(dāng)時(shí)實(shí)際的有效工作時(shí)間不多,針對三代以外的田野考古工作并不系統(tǒng),研究不得已集中在夏商周考古上。無論是研究團(tuán)隊(duì)的組建與培訓(xùn)、田野操作和研究方法的規(guī)范化、學(xué)術(shù)問題和視角的選擇等方面,中國考古學(xué)都打上了夏商周考古的烙印。另一方面,近年來對三代考古學(xué)與傳世、出土文獻(xiàn)間的關(guān)系,學(xué)術(shù)界反思甚多,甚至由此生發(fā)出關(guān)于考古學(xué)研究“純潔性”“獨(dú)立性”乃至文獻(xiàn)記載是不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問題。這些反思,連帶產(chǎn)生對考古學(xué)研究邊界、考古學(xué)復(fù)原古代歷史和史料獲取的功能與目的的質(zhì)疑,甚至上升到對考古學(xué)歷史屬性的懷疑。由此產(chǎn)生的邏輯悖論,已延展到類似“史前”時(shí)期是否是“史”的問題。此種背景之下,孫慶偉所著《追跡三代》頗顯異類,但反而彌足珍貴。

《追跡三代》由十篇文章組成,前兩篇圍繞顧頡剛展開,討論“古史辨”思想的形成和顧本人的夏史態(tài)度;第三篇論李濟(jì)汾河調(diào)查的過程和目的;第四至第七篇集中梳理考古學(xué)界對夏文化、夏商關(guān)系的探索歷程;第八篇比較李濟(jì)與鄒衡的殷墟研究;第九、第十篇討論先周文化研究的分歧形成過程和困境。可以說,除了頭兩篇之外,其余八篇以學(xué)術(shù)史方式梳理了中國三代考古最核心學(xué)術(shù)問題的發(fā)展歷程。
夏商周考古研究歷經(jīng)近百年,斐然成果的背后是幾乎所有重大學(xué)術(shù)問題都曾有激烈分歧與論辯,甚至可以說,若干核心問題至今仍未達(dá)成共識。不但非夏商周考古學(xué)領(lǐng)域的考古學(xué)家只知大概,很多剛剛?cè)腴T的夏商周方向研究生也分辨不明微妙細(xì)節(jié)。以夏文化探索為例,僅是梳理清楚新、舊西亳說和鄭亳說之間的學(xué)術(shù)主張,把握夏商分界焦點(diǎn)問題的變遷,分析各學(xué)說代表學(xué)者觀念的轉(zhuǎn)變歷程與動機(jī),就是十分困難的任務(wù)。不但需要宏觀綜合能力,駕馭五十余年來的發(fā)掘資料,以及由此而來的數(shù)十位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區(qū)分其間細(xì)微差別,還需要清晰地描述出來。否則,沒有專門研究經(jīng)歷的讀者,必然墜入五里霧中,不得其要。
從最終成品來看,孫慶偉達(dá)成了學(xué)術(shù)史重溯的目的。不但有“順著看”發(fā)現(xiàn)與研究的縱向動態(tài)學(xué)術(shù)史觀察,也以“橫通”視野觀察“材料”如何成為學(xué)術(shù)問題,以及身處其間的學(xué)者在用什么方法解決這些問題。
學(xué)科范式的轉(zhuǎn)變有因緣,也有導(dǎo)火索。新材料的突然出現(xiàn),學(xué)者一時(shí)間未必能預(yù)料到后果。在考古研究中,材料需要轉(zhuǎn)化為知識,知識進(jìn)而又會影響思想與研究理路。對這一過程的盤點(diǎn),往往需要長時(shí)段的歷史眼光。在學(xué)科發(fā)展的長程上考察這些問題,就需要避免枝節(jié),單刀直入。這對觀察人的素養(yǎng)有很高的要求,回溯的眼光尤其需要知識的先期儲備。
從這個(gè)角度來說,學(xué)術(shù)史梳理為孫慶偉本人提供了相關(guān)核心問題研究入門的幫助。可以說,《追跡三代》首先是孫慶偉本人熟悉并進(jìn)入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自我訓(xùn)練和資料準(zhǔn)備過程,是他熟悉該領(lǐng)域研究現(xiàn)狀,發(fā)現(xiàn)存在問題的自我訓(xùn)練,其次才是作為研究目的的學(xué)術(shù)史探索。
但孫慶偉寫作的預(yù)設(shè)顯然不止于此,弄清核心問題的來龍去脈、糾葛細(xì)節(jié),只是起跑線,他的終極目標(biāo)是要發(fā)現(xiàn)核心話題的瓶頸是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核心話題之弊”。這既是孫慶偉的目的,更是他的抱負(fù)與情懷。6973D88E-F154-4958-A2A9-D419F8A76385

與其他學(xué)術(shù)史的重建工作不同,《追跡三代》對于學(xué)術(shù)問題生發(fā)的語境(context)非常在意,對提出和解決學(xué)術(shù)問題的學(xué)者本人異常關(guān)注。在孫慶偉的回溯過程中,學(xué)術(shù)研究與學(xué)人思想、經(jīng)歷之勾連,使學(xué)術(shù)史探索已非純知識性的考察和梳理,甚至于對類似韓維周這樣學(xué)術(shù)史上的“失蹤者”,都給予了充分關(guān)注。實(shí)際上,了解三代考古研究者在專業(yè)程式化研究背后的個(gè)人經(jīng)歷、學(xué)術(shù)“野心”和歷史情懷,是打開學(xué)術(shù)問題嬗變道路的一把鑰匙。
中國考古學(xué)百年發(fā)展史中,操作和研究的規(guī)范化,是一條明線。但在“專業(yè)化”和職業(yè)化的趨勢下,一線考古工作者因制度、因工作安排,終生負(fù)責(zé)某一遺址專攻某一領(lǐng)域的工作模式越來越普遍。作為研究機(jī)構(gòu)齒輪上的一顆螺絲釘,興趣廣泛學(xué)者的學(xué)術(shù)空間逐漸變窄,想要旁及其他運(yùn)轉(zhuǎn)結(jié)構(gòu),有難度。同時(shí),日趨規(guī)范也更加程式化的專業(yè)研究和知識生產(chǎn)模式,對從民國而來缺乏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訓(xùn)練、憑舊學(xué)、憑經(jīng)驗(yàn)甚至靈感進(jìn)行研究的學(xué)者,是嚴(yán)峻的挑戰(zhàn)。可以明顯地看到,在學(xué)科初建階段,學(xué)者本人的直覺、能力和問題意識會直接影響學(xué)術(shù)導(dǎo)向和方法論體系框架的構(gòu)建。在發(fā)掘與研究專業(yè)化水平提高的同時(shí),一大批曾經(jīng)站在問題前沿的學(xué)者,逐漸退隱到幕后。學(xué)術(shù)發(fā)展會在材料的積淀中,以既有的導(dǎo)向和方法論形成自身內(nèi)在理路。不同時(shí)期研究路向、風(fēng)行思潮的出現(xiàn),都可以在學(xué)術(shù)內(nèi)在理路中找到答案。但考古研究成果是不是全都得自基于實(shí)證的邏輯推理或檢測分析?有沒有考古學(xué)家直覺和經(jīng)驗(yàn)的成分?這是可以作為歷史認(rèn)識論研究的課題,也可以學(xué)術(shù)史的發(fā)展進(jìn)行回溯。
實(shí)際上,任何一個(gè)身處其間的夏商周考古研究者,在對自身學(xué)術(shù)道路和研究領(lǐng)域進(jìn)行抉擇時(shí),當(dāng)然會因機(jī)構(gòu)、制度和偶然的機(jī)緣產(chǎn)生研究的“主戰(zhàn)場”,但在精耕自己“一畝三分地”的研究時(shí),也必然會自然與不自然地代入自己的學(xué)術(shù)興趣,甚至?xí)幸驅(qū)W術(shù)“血脈”傳承的影響。《追跡三代》可看到一代代學(xué)者傳承、習(xí)得的知識與技能,也能看出不同問題的生發(fā)、尋找過程,以及解決問題的學(xué)術(shù)路徑淵源。孫慶偉試圖讓讀者回到研究的現(xiàn)場,以“了解之同情”的方式體察夏商周考古在發(fā)現(xiàn)與研究的發(fā)明之間如何展開,將問題與研究者的互動細(xì)細(xì)展開,全書也因此顯出了關(guān)懷與溫情。

李濟(jì)(1896-1979)
對考古研究來說,發(fā)現(xiàn)與研究之間的節(jié)奏往往并不匹配,對各類遺存的認(rèn)識和理解往往滯后于發(fā)現(xiàn),而理論的凝練與提升更肯定在若干認(rèn)識和理解的沉潛之后方能產(chǎn)生。因此,對于當(dāng)下三代考古研究范式路徑、討論問題的選擇,都必須基于當(dāng)時(shí)事件發(fā)生的背景來理解,不應(yīng)該以當(dāng)前的理念衡量。三代考古研究范圍擴(kuò)大,根源于“材料”的擴(kuò)充。所謂新材料,并不一定是剛剛被發(fā)現(xiàn)的材料,也包括過去曾被發(fā)掘而不被認(rèn)為是“材料”的材料。而什么才能被認(rèn)作為“材料”,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學(xué)者的眼光和研究的范式,而非依賴于研究對象。正如孫慶偉注意到李濟(jì)與鄒衡對殷墟研究視角的差異,“著史”還是“分期”,是兩種不同的理念,更是兩種學(xué)術(shù)研究范式的路徑差別(當(dāng)然,如果《追跡三代》中能將考古所安陽工作隊(duì)的分期抉擇納入討論,則這一問題的分析將更加豐滿)。雖然同樣將考古遺存作為史料,李濟(jì)和鄒衡的處理卻完全不同。這種差異的根源,源自學(xué)者本人在身處不同社會境地,根源于學(xué)者經(jīng)歷和思想底色的差異,也根源于對三代考古學(xué)術(shù)目的的預(yù)設(shè)。
蒙文通說,要考察一種思想,就要考察它的“得勢”與否及其原因何在。孫慶偉對于學(xué)人背景、經(jīng)歷與學(xué)術(shù)問題導(dǎo)向的梳理,顯然注意到了在中立的學(xué)術(shù)態(tài)度和客觀的歷史解釋之外,學(xué)者本人的“倫理價(jià)值”和“興趣”影響,注意到了在中國近代社會迅速轉(zhuǎn)變過程中,學(xué)者自身的人文色彩和性格所帶來的研究差異。當(dāng)然,《追跡三代》在這一梳理過程中,也有缺憾,對于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研究體制以及宏觀史學(xué)研究范式背景對三代考古學(xué)的影響如何,被他隱去了。而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機(jī)制的一大問題,就在于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學(xué)者代際傳承和師承關(guān)系,以及研究體制甚至條文規(guī)定限制,會對學(xué)術(shù)研究產(chǎn)生持久且嚴(yán)重的影響。
以《追跡三代》的梳理,我們大體可以看出七十多年來,夏商周考古核心學(xué)術(shù)問題的糾纏、觀點(diǎn)和理路的分歧,僅是表象。深層次的問題,在于研究與立說重心的轉(zhuǎn)變,在于歷史研究面貌和取向的變化,在于舊有學(xué)術(shù)邏輯框架、學(xué)說體系的延續(xù)與舊有學(xué)說結(jié)論的調(diào)整、修正甚至倒置之間所形成的鮮明對比。
相對于當(dāng)前如火如荼的各類“新史學(xué)”,尤其是“新文化史”影響下的研究話題,傳統(tǒng)夏商周考古研究視角顯得不大“新潮”。《追跡三代》所認(rèn)定的核心學(xué)術(shù)問題,更多是近來被批評為缺乏“純潔性”且?guī)в小熬幠晔穬A向”的議題。但孫慶偉是一個(gè)有著明確理論自覺的學(xué)者。在梳理學(xué)科發(fā)展史中具體問題發(fā)展脈絡(luò)的同時(shí),他十分關(guān)心這些具體問題提出的因由和解決的方法。在對先周文化探索學(xué)術(shù)史的分析中,他分析了徐旭生、蘇秉琦和石璋如的視角差異;也用細(xì)致描述,分析“追溯法”和“都邑法”的缺陷;甚至梳理了同輩兼同門雷興山“考古背景”分析法產(chǎn)生的學(xué)術(shù)背景。這種學(xué)術(shù)史的梳理,顯然沒有“托諸空言”,也沒有“因人廢言”,而是將理論發(fā)展及理論缺陷的思考,放置在具體問題中進(jìn)行回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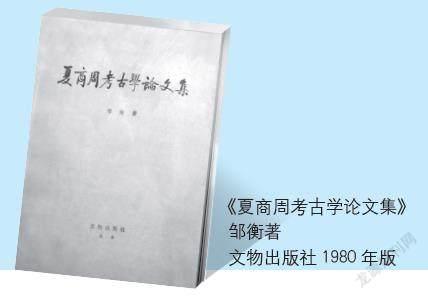
但孫慶偉的回溯無法解決的是,如何回應(yīng)對夏商周考古學(xué)史學(xué)取向的質(zhì)疑,以及有效力的解決辦法。實(shí)際上,任何學(xué)術(shù)問題不僅來自學(xué)術(shù)研究,而且來自當(dāng)下社會不斷變化的需求和視角,甚至來自看待自身歷史的不同方式。對三代考古史學(xué)取向質(zhì)疑的背后隱含著的,是部分當(dāng)代研究者對于與西方學(xué)術(shù)界接軌,甚至得到西方學(xué)術(shù)界認(rèn)可的希望。6973D88E-F154-4958-A2A9-D419F8A76385
二十世紀(jì)以來,西方史學(xué)理論更新的速率增快,一個(gè)比較重要的特征是立說重心總體上不再關(guān)注精英,討論焦點(diǎn)由中心轉(zhuǎn)向邊緣、由權(quán)威轉(zhuǎn)向群眾。這些變化也影響了中國歷史研究的面貌,但在很長一段時(shí)間內(nèi),對上古、先秦史并未形成沖擊。一方面固然因?yàn)樯瞎攀妨线^簡,理論轉(zhuǎn)換帶來的新史學(xué)變革和問題傾向,在上古研究領(lǐng)域無法同樣展開。另一方面,中國上古史重建研究的重任離開考古資料幾乎無法有新突破,而物質(zhì)文化資料如何直接成為新史學(xué)的史料,在方法論上尚待探索。
但歷史學(xué)界整體變化,或多或少仍會影響夏商周考古學(xué)焦點(diǎn)的變換,其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近年來對于文獻(xiàn)記載的三代歷史與考古學(xué)文化遺存關(guān)系的討論,以及對三代考古研究史學(xué)傾向的檢討而形成的“古史辨”思潮的回歸。《追跡三代》之所以將回溯的起點(diǎn)放在顧頡剛古史辨思想的形成,也當(dāng)是因這樣的現(xiàn)實(shí)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而起的。

實(shí)際上,從民國時(shí)期殷墟的發(fā)掘開始,地下材料始終是在強(qiáng)化學(xué)者對古史的信任,肯定了正史敘事體系框架的可靠性。傅斯年本人由疑古轉(zhuǎn)向重建古史,就是古史辨派對矯枉過正極端方式的反思。然而,整體的疑古傾向畢竟存在,以至于連徐旭生在提倡“改走信古的路”時(shí),也只敢把最終的目標(biāo)設(shè)定為在“傳說”中“尋求古代略近的真實(shí)”。
對夏商周考古學(xué)家來說,對文獻(xiàn)史料可信度立場的轉(zhuǎn)換雖是警醒,卻要避免極端。如果秉持全面批評的態(tài)度,在對既有舊研究范式與結(jié)構(gòu)倒置的同時(shí),卻無法以考古資料重建上古史框架,則“破而不立”的狀況只會傷害到學(xué)科的構(gòu)建與演進(jìn)。另一個(gè)悖論是,即便將考古學(xué)置于非史學(xué)的語境下,破碎的考古遺存會讓研究問題更為碎片化。無論是不是“作為人類學(xué)的考古學(xué)”,考古遺存的史料意義與價(jià)值,永遠(yuǎn)無法回避。如果沒有整體的關(guān)照,物質(zhì)文化資料也就只能是片段個(gè)案,而無作為社會組成部分的意義。在這一前提下,“陳腐”且有邏輯缺陷的史學(xué)研究范式,反比刻意回避史學(xué)目的甚至“編年史傾向”的新說,更具啟發(fā)力和建設(shè)意義。
《追跡三代》的敘述式梳理中,始終隱含著這一思路,討論了三代考古學(xué)“史學(xué)取向”的合理性。九十余年的三代考古研究歷程回溯,清晰地說明,任何學(xué)者都不能斷然無視長期且有傳承的三代文獻(xiàn)記載。三代考古的發(fā)現(xiàn),與文獻(xiàn)記載契合的情況多,于史無征的反而是少數(shù)。這反映出傳統(tǒng)文獻(xiàn)記載似乎都有史影或者來由,并不都是神話傳說。與以否定“編年史傾向”為出發(fā)點(diǎn),走向否定考古學(xué)物質(zhì)遺存的史料性質(zhì)方向,令史前社會非“史”的學(xué)術(shù)取向相較,孰是理性?孰是極端?恐怕圓鑿方枘,一目了然。當(dāng)然,上古社會是不是“歷史”這個(gè)問題十分復(fù)雜,甚至可能需要對史學(xué)本身的價(jià)值和性質(zhì)做出重新評估,界定“歷史”的邊界范圍。但對于當(dāng)下的歷史研究者而言,如傅斯年在二戰(zhàn)后論學(xué)術(shù)客觀性時(shí)所強(qiáng)調(diào)的那樣,若推到極端,不論社會科學(xué)還是自然科學(xué),研究都只有“理想的境界”。
當(dāng)然,夏商周考古學(xué)家也必然需要警惕文獻(xiàn)的陷阱,不能將文獻(xiàn)記載全部認(rèn)作事實(shí)。考古學(xué)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物質(zhì)遺存而非語言文字,可用以觀測和解釋的信息交流也非語言、文字。這正是考古學(xué)的強(qiáng)項(xiàng)。未來的工作難點(diǎn),是需要以更多的經(jīng)驗(yàn)性實(shí)例,凝練可以重復(fù)檢驗(yàn)的,從物質(zhì)到人群、到族屬的研究方法論。這個(gè)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然會有漸進(jìn)的成就。《追跡三代》的回溯中,讀者能夠體察數(shù)代考古學(xué)家的孜孜以求歷程,孫慶偉回望的這個(gè)探索過程,可能是接近歷史真相(如果確實(shí)存在的話)的唯一路徑。6973D88E-F154-4958-A2A9-D419F8A763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