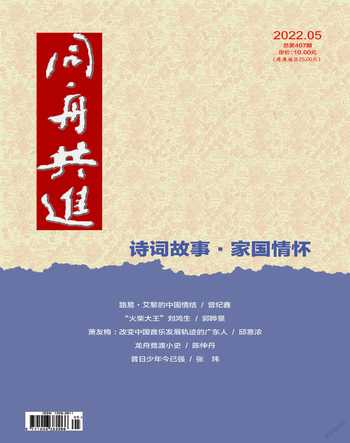聊聊杭幫菜
沈嘉祿
杭幫菜,也就是杭州菜,與紹興菜、寧波菜、溫州菜一樣屬于“小幫菜”。小幫菜,格局不大,弄來弄去也就這么幾道菜,西湖醋魚、東坡肉、炸響鈴、松鼠鱖魚、鞭尖老鴨湯、砂鍋魚頭豆腐、叫化童雞、清湯魚圓、龍井蝦仁、荷葉粉蒸肉……多乎哉,不多也。若要較真起來,有幾道菜還是從別人那里“偷”來的。
不過也要看到,杭州菜頗有點來歷,是老資格。有一首詩,一直令人心馳神往:“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這是南宋一位名叫林升的文人在酒后信手寫下的,流傳了800多年,為后人留下了當時的社會場景的寫照。
【人間天堂】
紹興十一年(1141),南宋與金簽訂紹興和議,結束了長達十余年的戰爭狀態,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南宋政權由此得到了喘息機會。
臨安作為都城的經濟優勢與地理條件主要有幾個方面:一、憑長江天然之險,不像建康那樣瀕臨長江,易受攻擊。二、地處太湖流域與寧紹平原兩大魚米之鄉的交匯處,物產豐饒。三、大運河與浙東運河在此交匯,明州作為外貿港也近在咫尺,漕運、海運都很方便。四、經唐、五代與北宋的長期建設,杭州已躍升為東南最繁華的都會。到了南宋末年,人口達124萬,城區面積十倍于汴京。蘇東坡和白居易曾先后在杭州擔任官職。
戰爭給江南帶來了巨大的創傷,但對杭州而言卻是一次機會。在政治經濟重心南移的同時,北方的文化與技術也一并南下,為生產力發展和商業繁榮創造了條件。杭州的城市格局從唐朝的封閉型轉變為宋代的開放型,百業興旺,經濟繁榮,不僅超越了前代,而且居世界前列。
山清水秀的景色令人陶醉,五方雜處、萬商云集也為臨安的飲食構成創造了條件。相當數量的廚師、點心師與茶藝師隨著逃亡大軍過江南下,驚魂甫定,重操舊業,而本地食客也從北方肴點中品出了別樣滋味,很快便接納了他們。
更重要的是,從大環境方面說,進入南宋,中國的飲食原料豐富了許多,如絲瓜、黃瓜、胡蘿卜等菜蔬都從域外引進種植成功;動物蛋白的來源也以豬、羊、牛、雞、鴨、鵝、魚、蝦、蟹為主。而游牧業、狩獵業時代常食或祭祖的野味退居次要地位,甚至連花卉也能做成一道道珍饈佳點、泡成一壺壺雅香襲人的花茶。
人間煙火最盛時,杭州城內就有17個副食品交易市場,要做一桌家宴,差仆人去辦,輕而易舉就能完成。皇宮里還設立了四司六局,專門管理皇上的膳食及筵席諸事。吳自牧在《夢梁錄》里說過:“杭城食店,多是效學京師人,開張亦效御廚體式,貴官家品件。”他還在書中收錄了臨安各大飯店的菜單,菜式共有335種,比如繡吹羊、野味假炙、清攛鹿肉、煎黃雀等,大致保留了北方口味;而更多的菜點,如波絲姜豉、淡菜膾、蝦色兒、酒潑蟹、梅干兒等,則從原料、烹飪方法及菜名上反映了北方文化對杭州食事的影響。
在周密的《武林舊事》中還記錄了當時的名酒50多種,街巷挑擔叫賣的風味小吃70多種,餐飲市場的烈火烹油、燈紅酒綠是不難想象的。書中還有“高宗幸張府節次略”一節,說的是紹興二十一年(1151)十月,清河郡王張俊宴請皇上,前前后后上了102款菜肴,外加120碟點心、水果、香藥和看果等,數百人從早上一直吃喝到晚上,曲終人散之際,張俊還向皇上進奉了各種寶器、古物、名畫,若論數量和質量,堪當一座博物館。可見臨安當時飲食選擇之豐富、文化繁榮之程度。
【南北“雜交”】
在張俊請皇上吃飯的菜單里仍然可以看到不少北方美食,比如花炊鵪子、豬肚假江鰩、羊舌簽、五珍膾、炒白腰子、水母膾、七寶膾等,但也能見到南方風味的蛛絲馬跡。
當然,食材與口味肯定會影響外來風味的本土化進程,杭州作為旅游城市,已經有不少文人墨客將閑情逸致融入到這座城市的氣質之中,使得本土化的過程變得水到渠成。今天假如對杭州菜稍作研究,便會發現有些菜肴從外省一路南下的草蛇灰線。比如西湖醋魚,不就是黃河鯉魚的變體嗎?叫化童雞,這不是常熟王四酒家的看家菜嗎?荷葉粉蒸肉,但凡荷葉田田處大抵都會有,四川、江西、湖南、重慶都有,荷香與肉香則一樣的古雅馥郁。
至于響當當的東坡肉,傳說是蘇東坡在杭州當太守時發明的,其實誰都知道,他對紅燒肉的定型是在黃州(今湖北黃岡)。今天不僅杭州有東坡肉,四川、徐州等地都有東坡肉,而且都說自己是“首發地”,但如果要說味道及入口即化的效果,當然還是杭州廚師拿捏得最到位。

再說到清湯魚圓。這道菜我有發言權,因為我母親做得最好,她是紹興人,她的手藝是從娘家帶到上海來的。清湯魚圓看似素面朝天,其實制作起來頗費工夫,以前我家常做。母親一早去菜市場拎一條3斤以上的花鰱魚,剝皮、去骨、剔肉,在木砧板上剁成魚泥(木砧板上的木紋可以夾住肉眼難以看清的小魚刺),再叫我用一把毛竹筷子以順時針方向使勁攪拌。母親每過一段時間來加半碗水,大約是一斤魚肉加一斤水,一直拌到筷子插進魚肉里能站起來不倒,才算大功告成。然后輪到母親下料,唯有鹽、料酒和味精三樣,不必加淀粉和蛋清。坐鍋燒水,她一邊從虎口擠出魚圓,一邊用湯匙一刮,投入正翻著蝦眼的沸水里,等魚圓浮起后馬上撈起。魚圓撈盡后,再往鍋內投入豆苗略氽一下,再投入適量的魚圓加熱,淋上幾滴油就可上桌了。這樣一碗清湯魚圓,白是白,綠是綠,湯色清澈,魚圓滑嫩,入口就化,口味鮮美。
那么,宋嫂魚羹呢?這應該是板上釘釘的杭州菜了吧?這就要說到宋嫂魚羹的由來。話說一日春光正好,宋高宗帶著近臣坐畫舫游宴于西湖,突然一葉扁舟乘風而來,船頭立一婦人,曼聲叫賣魚羹。高宗一聽是豫中口音,思鄉之情油然而生,遂差人買來一嘗——東京老味道啊!忙把婦人叫上船來親切問候,這才知道那位半老徐娘是隨他一起逃難南下的宋嫂。高宗在“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西湖吃到宋嫂魚羹,大發“不知今夕何夕”之嘆。這位宋嫂只知其姓,不知其名,但不影響她成為中國烹飪界的“魚羹之母”,宋嫂魚羹也理所當然成了杭州菜的招牌。E22EA842-731F-4442-AED4-DF6D3F0BF07A
就是這樣,古代杭州菜與北方風味的“雜交”,杭州人對美食的理解,以及江南地區從庶民階層到知識階層對杭州這座城市的預期與要求,定義了南宋以后的杭幫菜。
【進入近代】
美食作家二毛在《民國吃家》一書中的《且介亭與上海菜》一文里,梳理了魯迅與杭州菜的緣分:“知味觀杭菜館是魯迅在上海期間去得最多的地方。它于1930年開業,原設于芝罘路西藏路口,后遷至福建路南京路口……拿手菜有西湖醋魚、東坡肉、叫化雞、西湖莼菜湯等。”“知味觀”是不是魯迅去得最多的菜館,還不能輕易斷定,但從《魯迅日記》里可以知道,在1932年7月至1935年10月,他曾五次光顧知味觀,包括數次設宴招待朋友。
對于一些隆重的宴請,魯迅還會事先去店里預訂好餐位。1933年秋,魯迅就在知味觀宴請日本福民醫院院長和內山君等好友,以東道主身份點了叫化雞、西湖莼菜湯等名菜。席間他還向客人介紹了叫化雞的來歷和做法。
有時候魯迅也會請知味觀的廚師到家里來做菜。1934年3月25日的魯迅日記中有這樣一筆:“夜招知味觀來寓治饌,為伊君夫婦餞行,同席共十人。”伊君是曾任職《大美晚報》的美國記者伊羅生,與魯迅一起加入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將一個外國人請到家中吃飯,可見魯迅與伊君的關系非同一般。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滬漂”的浙江籍文人為數不少,可以想象一下,他們都有機會去知味觀吃過叫化雞、西湖醋魚、神仙鴨子、蝦子面。但也應該看到,彼時的上海,寧波館子的數量與興盛程度肯定在杭菜館之上。我不敢說上海人對杭州菜有所排斥,但至少在本幫菜的成長過程中,幾乎看不到對杭州菜的借鑒。而寧波菜里的家常元素,倒是長驅直入地滲透到石庫門的生活日常中,直到今天,嗆蟹、醉蝦、搖蚶、墨魚大烤、咸菜大湯黃魚、冰糖甲魚等,仍然是上海人的最愛。
新中國成立后,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初,將近半個世紀里,杭州菜在上海只是作為一種風味被保存著,稍為群眾所知的也就兩家,一家是福建中路的知味觀,就是魯迅吃過的那家,門口寫有“知味停車,聞香下馬”八個字。還有一家是開在四川北路橫浜橋堍的西湖飯店。這兩家都是老字號,一本菜單可以用上幾十年。
誰也想不到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杭幫菜忽如一夜春風來,上海灘突然雨后春筍般出現了好多家杭幫菜酒家,知名度比較高的有紅泥、張生記、謝小義、江南春、新開元、蘇浙匯、萬家燈火等。后來連老資格的樓外樓也繃不住了,搶灘虹橋開發區開了一家。
在環境布置上,這些酒家一般以民族風來拉近與食客之間的距離,供應的菜肴大都是流行于民間的家常菜,選料比較粗放,成本可控,“貼水面飛行”,不至于虧本。但也因為家常,對出菜的要求就不能過高,以叫化雞、東坡肉、宋嫂魚羹等幾道老菜裝裝門面,其它的就“海派”了。比如油條入肴,油條在杭州叫做“油炸檜”,是老百姓因痛恨秦檜而發明的,現在做成絲瓜炒油條、白米蝦炒油條,也可以接受,很有老百姓過小日子的機巧。至于八寶辣醬、剁椒魚頭、五彩魚柳、紅燒河鰻、麻香辣子雞等,都是敲上杭州菜印章的外幫菜。
【“新杭幫菜”】
進入新世紀后,上海餐飲市場的競爭日益白熱化,更多外省風味涌入。
近十年,杭幫菜打出“新杭幫菜”的旗號,龍井蝦仁、西湖醋魚、蝦爆鱔、東坡肉、桂花鮮栗羹、筍干老鴨煲、乾隆砂鍋魚頭、童子雞炒毛豆等屬于“傳統節目”,鄭重保留,此外還引入了江蘇菜和本幫菜的一些元素,有些居然還摘了米其林星級,光芒四射。
重新登場后,這些杭幫菜餐廳的業態、時態、心態都有了變化,不再一味地貪大,經營上也相當慎重,不事聲張,對品牌的培育與維護也比較用心。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業主都是從別的行業轉入餐飲界的,算是“入侵者”。
所幸,新杭幫菜餐廳一家接一家地開張了,在江浙菜與本幫菜之間游走,路子越走越寬,都贏得了良好的聲譽。這一態勢證明,上海市場是高度開放的,餐廳只要能做到尊重傳統,勇于創新,融合度高,就能滿足多層次消費者的需求。
昔時,浙江杭嘉湖地區出過不少懂吃能寫的文人,他們為中國的飲食史留下了許多美食寶典,如林洪的《山家清供》、浦江吳氏的《中饋錄》、韓奕的《易牙遺意》、曹庭棟和黃云鵠的《粥譜》、高濂的《遵生八箋》和《居家必備》、謝墉的《食味雜詠》、朱彝尊的《食憲鴻秘》、李漁的《閑情偶寄》、袁枚的《隨園食單》、顧仲的《養小錄》……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杭幫菜的形成與發展,所以,杭幫菜一定會有更加精彩的呈現。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E22EA842-731F-4442-AED4-DF6D3F0BF0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