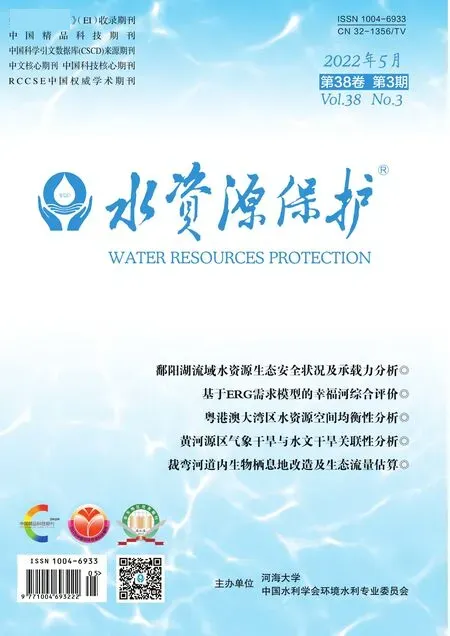黑河和白河流域濕地變化及其歸因分析
呂佳南,李常斌,武 磊,謝旭紅,周 璇,魏健美
(1.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2.蘭州大學西部環境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甘肅 蘭州 730000)
1 研究區概況
濕地是由水陸交互作用所形成的自然綜合體[1],具有獨特的生態水文環境條件[2],在調節氣候、涵蓄水源和維持區域生態平衡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3-4]。早期關于濕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受人類活動影響較大的平原和沿海地區[5-9],研究內容多見濕地水力傳輸機制、水量平衡和景觀格局變化等[10]。由于氣候變化與濕地演化關系密切,濕地生態系統對氣候變化的響應也逐漸成為研究熱點[11-13],特別是隨著全球變暖進程加劇,高海拔生態敏感區濕地景觀動態研究成為該領域前沿焦點[14-15]。Niu等[16]通過研究中國濕地變化趨勢,認為1978—2008年中國濕地減少主要由土地復墾所致;李娜娜等[17]對四川省濕地類型變化的驅動力進行了分析,認為四川省濕地類型的變化是社會經濟因素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國內生產總值為主導因素,氣溫變化對其有一定影響;李志威等[18]研究了若爾蓋沼澤濕地的萎縮機制,認為氣溫升高對若爾蓋沼澤的萎縮影響較小,人工開挖溝渠疏干沼澤積水是沼澤濕地萎縮的重要誘因;邢偉等[19]分析了全新世以來東北地區沼澤濕地發育的動態變化過程,認為氣溫和降水是影響沼澤濕地發育的最重要因素。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濕地變化與氣候和人類活動均有關聯,由于上述過程發生效用的時間尺度并不一致,較高時間分辨率的濕地動態診斷就顯得尤為關鍵,該方面的研究目前還較少見諸報道。
若爾蓋濕地位于青藏高原東北部,是黃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養功能區[20-22],對黑河、白河流域河川徑流具有明顯調節效應。1970年以來,黑河、白河流域濕地變化顯著,已出現水位下降、濕地萎縮、沼澤土壤硬化、濕地植被退化、濕地沙化和濕地生物多樣性減少等諸多問題[23-25]。明確黑河、白河流域濕地變化及其對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響應,有利于厘清濕地生態水文系統與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因果關系,屬河源區濕地生態系統水源涵養量化評估的基礎性內容,可為高寒濕地景觀保護和濕地水文人工調節等提供科學數據支撐。
黑河和白河同屬黃河上游一級支流,發源于四川省紅原縣若爾蓋高原東部,位于102°00′E~103°25′E、32°00′N~34°10′N(圖1)。黑河發源于紅原縣東北部哲波波亞山,自南向北流經若爾蓋,于瑪曲和若爾蓋縣界處匯入黃河,干流全長261 km,流域面積7 427 km2,海拔在3 273~4 451 m之間;白河發源于紅原縣南部嘎哇達則,自南向北流經紅原縣,于若爾蓋縣西南部唐克鎮匯入黃河,干流全長187 km,流域面積5 488 km2,海拔在3 369~4 809 m之間。 兩河流域內高寒草甸、濕地廣布,是黃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養生態功能區[26]。該區高寒濕地是由青藏高原新、舊構造運動沉降和上升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沼澤區,地貌類型主要有低山、丘陵和河谷階地[26]。氣候屬于大陸性高原寒溫帶濕潤氣候,高寒大陸性氣候特征明顯。域內氣溫具有南低北高、東低西高的空間分布特征;降水總體表現為南多北少,多集中在5—9月。

圖1 黑河和白河流域地理位置及水文地貌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hydrologicalgeomorphology of Heihe River and BaiheRiver basins
2 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采用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發布的MOD13Q1數據(http://reverb.echo.nasa.gov),該數據由EOS/Terra衛星上搭載的中分辨率光譜儀獲取處理合成,空間分辨率為250 m。DEM及SLOPE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地理空間數據云平臺(http://www.gscloud.cn),分辨率為90 m。本文以DEM、 SLOPE和從MOD13Q1提取的歸一化植被指數(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增強植被指數(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 EVI)等數據為基礎,通過構建決策樹模型的方法提取黑河、白河兩河流域濕地。降水及氣溫數據選用由青藏高原數據中心(https://data.tpdc.ac.cn/)提供的中國區域高時空分辨率地面氣象要素驅動數據集(The China Meteorological Forcing Dataset),空間分辨率為0.1°,時間分辨率為3 h。若爾蓋縣、紅原縣2000—2018年總人口、鄉村人口、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口、國民生產總值、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肉類總產量和油料產量等統計數據來源于兩縣統計年鑒。
2.2 研究方法
2.2.1決策樹模型
決策樹的數學內涵由閾值判定。基于閾值將影像分割為相對同質的像元子集,各子集對應某一個待定的類。決策樹模型支持像元解譯的過程追蹤和結果對比,有利于地類變化及不同地類之間的關系解釋[27],符合濕地變化研究所需。
基于樣本訓練構建決策樹模型,TNDVI、TEVI、TDEM和TSLOPE分別為NDVI、EVI、高程和坡度的分類閾值要素值。訓練過程中發現,NDVI、EVI數據能夠較好區分水體(包括具有一定明水顯示的沼澤濕地)和草地,高程和坡度有利于區分川原和山區,而濕地通常位于開闊平緩的平原川區。上述指標中,高程和坡度屬相對靜態,年代際濕地面積萎縮或擴張主要依據TNDVI和TEVI的變化而定。訓練、分類結果與TM影像解譯成果及野外調查記錄進行對比,不斷調整分類閾值,最終確定兩河流域主要覆被類型決策樹模型分類閾值要素值(表1)。

表1 決策樹模型分類閾值要素
2.2.2濕地動態分析
采用景觀格局動態分析方法量化濕地動態。景觀格局分析指標體系大致對應斑塊、類型和景觀3個尺度水平。濕地在空間具有斑塊分布特點,在決策樹模型進行分類的基礎上,選取以下斑塊水平指標進行濕地動態綜合分析:斑塊面積百分比IPLAND表征某一類型斑塊總面積占全域面積的百分比,其值越接近0,則該斑塊類型越稀少,反之越大;最大斑塊指數ILPI為某一斑塊類中最大斑塊面積占全域面積的比例,其值越小說明斑塊連片的面積就越小,反之越大;斑塊密度IPD表征某一類型斑塊在全域的密度,其值越小則該斑塊類型破碎度越低,反之越高。
3 結果與分析
3.1 兩河流域濕地景觀動態
3.1.1決策樹模型精度驗證結果
分類精度驗證基于TM影像數據及野外調查結果進行。選取116個興趣區(region of interest,ROI)進行驗證,見圖1。分別在2017年10月、2018年5月及7月、2019年7月、2020年7—8月前往兩河流域進行野外綜合科考,考察區域涉及兩河流域沿河灘涂、沼澤、湖泊等,對草甸和濕地進行了地形、地類等描述和記錄,樣區分布如圖1所示。2000—2018年分類精度驗證結果見表2,分類平均精度為95.14%,Kappa系數為0.910 0,表明所構建分類決策樹在兩河流域的適用性較好。

表2 決策樹分類精度驗證
3.1.2濕地景觀提取結果
基于所構建決策樹模型提取兩河流域2000—2018年濕地景觀,得到沼澤濕地、沼澤化草甸濕地和湖泊等主要濕地類型的空間分布。2000年和2010年分別對應兩種不同的濕地景觀格局,以這兩年為例進行展示如圖2所示。由圖2可見,黑河、白河流域濕地主要分布于兩河干流兩側,北部黑河流域濕地面積分布比白河流域廣,特別是中、下游地帶多見沼澤濕地分布。兩河流域濕地動態顯著,特別是沼澤濕地,與2000年相比,2010年該類濕地顯著減少。
根據分類結果進行空間統計,兩河流域草甸濕地、沼澤濕地和湖泊面積的逐年變化如圖3所示。由圖3可見,兩河流域以草甸濕地面積為最大,黑河流域3種主要類型濕地面積均大于白河流域。黑河流域草甸濕地面積在2000—2010年明顯增加,2010年面積最大(3 167.37 km2),之后發生減少,2014年面積最小(2 680.70 km2),隨后再度增加;白河流域草甸濕地面積在2000—2012年上下波動,無明顯增減趨勢,2012年開始出現減少,2014年出現最小值(738.51 km2),隨后增加;黑河流域沼澤濕地面積在2010年之前、白河流域在2009年之前均呈減少趨勢,之后開始增加,在2014年達到最大值,隨后又逐漸減少;兩河流域湖泊面積相對穩定,研究期間略有增加。
由上述分析可知,統計時段內兩河流域濕地面積迥異,但變化具有一定趨同性,均以2009年、2010年、2014年為變化特征值年份。草甸濕地在2010年達到最大值,在2014年達到最小值;沼澤濕地在2009年、2010年面積較小,在2014年達到最大值。兩河流域沼澤濕地和草甸濕地面積變化存在此消彼長的總體特征。2000—2018年,黑河、白河流域草甸濕地面積的變化率分別為14.147 km2/a和-0.111 km2/a;沼澤濕地面積的變化率分別為-7.780 km2/a和0.776 km2/a;湖泊面積均有增加,變化率分別為0.349 km2/a和0.068 km2/a;濕地總面積變化率分別為5.486 km2/a和0.837 km2/a。總體來看,黑河流域以草甸濕地和湖泊增加、沼澤濕地減少為主要變化特征;白河流域以草甸濕地減少、沼澤濕地和湖泊增加為主要變化特征;2000—2018年,兩河流域濕地總面積呈增加態勢。

(a) 2000年

(b) 2010年


(a)黑河流域

(b)白河流域
3.2 濕地景觀動態變化結果
基于決策樹模型分類結果,由Fragstats4.2景觀格局指標分析軟件計算斑塊面積百分比IPLAND、最大斑塊指數ILPI和斑塊密度IPD等3個指標,黑河、白河流域主要濕地類型的3個指標變化如圖4所示。由圖4(a)可見,黑河流域草甸濕地面積占比大于白河流域,統計期間呈增長趨勢,白河流域則呈微弱減少趨勢;兩河流域沼澤濕地面積占比均較小,變化趨勢與草甸濕地相反,特別是黑河流域沼澤濕地的減少較明顯。由圖4(b)可見,兩河流域草甸濕地的ILPI與IPLAND在數值和趨勢上都相近,表明草甸濕地在該區的完整性較好;沼澤濕地的ILPI值小于IPLAND值,表明沼澤濕地的破碎化程度高。由圖4(c)可見,兩河流域草甸濕地的IPD值均發生下降,意味著該類濕地斑塊密度變小,景觀連通性提升;沼澤濕地的IPD值上升,表明該類濕地斑塊數量增加,破碎度進一步加劇。兩河流域湖泊呈零星分布,3個指標值在個別年份出現變動,與湖泊面積增加相對應。濕地景觀及其動態分析表明,2000—2018年,兩河流域草甸濕地景觀的連通性進一步增強,這一過程伴隨著沼澤濕地景觀的破碎化程度提升。


(a) IPLAND

(b) ILPI

(c) IPD
表3為2000—2018年兩河流域景觀斑塊指標年際變幅,可見,黑河流域草甸濕地的IPLAND增幅小于ILPI,對應的IPD減小,表明草甸濕地連片程度提升;從絕對變化量來看,黑河流域草甸濕地IPLAND增幅大于沼澤濕地減幅,表明黑河流域草甸濕地的增加,并不完全對應沼澤濕地的退減,水文條件變好情形下,周邊草甸也可轉變為草甸濕地。上述情形在年代際尺度呈波動態勢,總體來看,黑河流域草甸濕地面積整體呈擴大態勢,破碎化程度降低;沼澤濕地整體呈減少態勢,但存在局部發生連片的情形,對應斑塊密度的降低,表明該區沼澤濕地變化的地域分異顯著。白河流域情形相反,草甸濕地IPLAND減幅小于ILPI,對應的IPD增加,表明白河流域草甸濕地減少,破碎化程度提升;草甸濕地IPLAND減幅小于沼澤濕地IPLAND增幅,表明該區沼澤濕地的增加非完全來自草甸濕地,適宜地形和水文條件下,周邊草甸也可轉為沼澤濕地。兩河流域湖泊各項指標變幅均為正值,表明2000—2018年,兩河流域湖泊無論面積還是數量都呈增加趨勢。

表3 2000—2018年兩河流域景觀斑塊指標年際變幅
3.3 濕地變化的驅動因素
3.3.1變化趨勢
兩河流域濕地景觀變化復雜。一方面,人類活動(如放牧,疏干等)導致沼澤濕地退演為草甸濕地;另一方面,豐水年降水量增加可導致部分草甸濕地轉為沼澤濕地或致使湖泊面積、數量增加;此外,氣候變暖的背景下,區域AET耗散增加,影響到濕地水文過程,也是各類濕地面積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天然狀態下,草甸濕地、沼澤濕地存續主要受地形和水文條件控制,因地形在較長時段內保持相對靜態,因此,濕地景觀動態受氣溫、降水等關鍵氣候因子影響更為顯著。以流域為單元進行空間統計,黑河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小于白河流域,氣溫則正好相反。2000—2018年,黑河流域最小降水量發生于2008年(498.31 mm),最大降水量發生在2018年(831.88 mm);最低氣溫出現在2000年(1.13 ℃),最高氣溫出現在2010年(2.67 ℃);濕地總面積在2001年最小(3 021.20 km2),2010年最大(3 263.67 km2)。白河流域最小降水量發生在2002年(531.54 mm),最大降水量發生在2018年(964.06 mm);最低氣溫發生在2000年(0.66 ℃),最高氣溫出現在2017年(2.40 ℃);濕地總面積在2003年最小(799.66 km2),2012年最大(890.26 km2)。由圖5、6可見,2000—2018年,兩河流域氣溫、降水量和各類濕地總面積呈趨同增長(圖中趨勢線上數字表示年際變幅),但從各因子極值發生年份來看,氣溫、降水量和濕地面積變化并不嚴格對應,如2018年兩河流域降水量均達到最高值,但濕地面積并未出現最大值。初步理解,更小時間尺度(如次、旬、月、季等)的氣候因子動態以及人類活動對濕地水文過程的影響等起著重要調節作用,本研究暫不涉及。

(a)黑河流域

(b)白河流域
3.3.2驅動因素分析
氣溫、降水量是影響黑河、白河流域濕地動態的主要氣候因素。以總人口、國民生產總值、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肉類總產量等作為社會經濟因素,對上述各類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進行主成分分析,結果見表4。黑河流域的3個主成分,其序列計算特征值分別為6.765、1.194和0.922,主成分累計貢獻率為89%;白河流域的3個主成分,其序列計算特征值分別為7.042、0.983和0.882,主成分累計貢獻率為89%。由表4可見,荷載系數越大,驅動因素對該類主成分的影響越大,進而對該類主成分所驅動濕地變化的貢獻越大。黑河流域濕地變化的驅動力因素的主成分1由總人口、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口、生產總值和第一產業增加值為主的社會經濟因子構成;主成分2由肉類總產量和鄉村人口等農牧業因子構成;主成分3主要是以降水量為主的氣象因子構成。白河流域濕地變化的驅動力因素的主成分1由生產總值、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為主的社會經濟因子構成;主成分2是以油料產量為主的農牧因子構成;主成分3是由降水量為主的氣象因子構成。黑河與白河流域濕地變化驅動因子的主成分1均是由生產總值和第一產業增加值等社會經濟因子為主,表明當地社會、經濟和農業的發展總體上影響和控制著兩河流域濕地變化的方向。

圖6 2000—2018年兩河流域濕地總面積變化趨勢

表4 主成分分析結果
4 討 論
黑河、白河流域地處若爾蓋高原,是以藏族為主的少數民族聚集區,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氣候條件和水文、生態特性決定了當地的支柱產業為畜牧業。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過牧等因素導致草甸、濕地生態系統退化;此外,兩河流域濕地內分布著數量眾多的與天然水系連通的人工開挖渠道,濕地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補、徑、排條件發生改變,區域輸水能力和溝渠沖刷增強,引起地下水位下降、沼澤土質硬化、濕地植被退化等不良后果。兩河流域是黃河上游重要的生態屏障區和水源涵養區,有必要加大濕地區水文生態保護力度,將人類活動對濕地生態系統的影響控制在合理范圍,通過地方社會經濟發展與濕地生態系統健康之間平衡體系的構建,實現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已有研究表明,濕地變化是社會經濟因素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影響因子包括國內生產總值、總人口、政策因素、城市擴張、降水量和溫度等[28-31],兩河流域濕地變化的驅動機制具有“社會經濟+農牧業因素+氣候變化”交互作用的特征。李娜娜等[17]對四川省濕地類型變化驅動力進行了分析,李志威等[18]若爾蓋沼澤濕地萎縮機制進行了研究,何菊紅[32]對若爾蓋濕地與氣候變化及人類活動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中得到的結論與本研究基本一致。
黑河、白河流域相對豐沛的降水和山間寬闊平緩谷地共同促成濕地發育,流域降水是該區濕地形成發育的水文基礎[33];社會經濟發展因素,如開溝排水、泥炭開采、旅游業和畜牧業發展等導致濕地和河網溝渠間水力傳輸條件發生改變,重塑了濕地面域-線狀連通貫穿格局,極大地改變了濕地匯、蓄、排泄過程,濕地地表-地下系統的水分補給、徑流和排泄過程變異,濕地景觀形塑格局由此奠定并長期受到影響;農牧業因素,如草場分布、飼草種植、圍欄放牧等會影響區域蒸散發和地表產匯流過程,也對濕地變化產生影響。黑河流域濕地面積占比大,降水相對較少,沼澤濕地分布相對分散;研究期間,草甸濕地增加、沼澤濕地減少,或與社會經濟及農牧業因素促發沼澤濕地疏干進程加劇(并演化為草甸濕地)有關。白河流域變化趨勢相反,該區降水較豐沛,流域面積、沼澤濕地面積、最大斑塊指數和密度值與黑河流域相比較小,社會經濟因素驅動下,溝渠系統向沼澤濕地輸水,或使其外圍及地勢低洼處明水面積增加,沼澤濕地面積增加,相應地,草甸濕地面積減少。兩河流域湖泊呈增加趨勢,與當地湖庫保護及建設有一定關系[34]。需要說明的是,主成分分析結果表明2000—2018年兩河流域濕地變化具有“社會經濟+農牧業因素+氣候變化”交互作用的特征,并不意味著氣候要素效應,如升溫促增蒸散發、降水的濕地水分供應等不重要,只是說明高寒地區氣溫和降水變化對濕地的影響,比之人口和經濟體量增加的區域環境效用,其顯示度較低。
兩河流域濕地變化的時空異質性很強,不同時空尺度主要影響因素及驅動機制也有所不同,研究時段、因子選取以及分析方法顯得尤為關鍵[35-38]。2000—2018年,兩河流域濕地變化系由社會經濟驅動因素主導,但氣候變化的影響仍不容忽視。有研究發現,除了國內生產總值等社會經濟因素為高寒區濕地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外,增溫背景下沼澤濕地轉化為草甸濕地或非濕地的可能性也較為顯著[39-44]。后續研究將在本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完善氣溫、本地降水、上游來水和濕地出水等與濕地面積之間的多元回歸統計關系,進一步分析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對濕地變化的影響,厘清濕地變化與氣候環境、社會經濟各因子之間的數量關系。
5 結 論
a.2000—2018年,黑河流域草甸濕地面積增加,沼澤濕地面積減少,白河流域濕地變化呈相反態勢;兩河流域草甸濕地和沼澤濕地存在此消彼長的特征,濕地總面積增加。
b.景觀指數分析表明,黑河流域草甸濕地和沼澤濕地的破碎化程度均有所降低,白河流域則相反;研究期間兩河流域的湖泊面積和數量均增加。
c.兩河流域濕地變化具有“社會經濟+農牧業因素+氣候變化”交互作用的特點,年代際尺度社會經濟和農牧業因素對高寒草甸及沼澤濕地變化的影響更具顯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