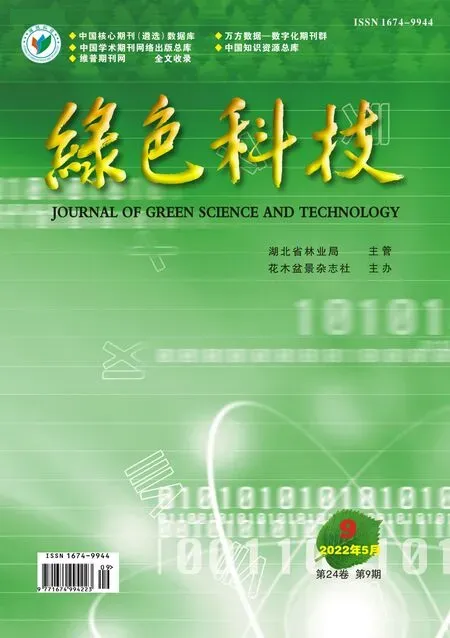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動力學研究
戴劍勇,范夢鴿
(南華大學 經濟管理與法學學院,湖南 衡陽 421001)
1 引言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貿易網絡化信息化程度加深,農產品從生產到銷售各環節行為的復雜性提高,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為農產品的生產與流通帶來信息平臺、射頻識別、冷鏈物流等先進技術的同時,也使農產品供應鏈復雜性日趨突顯。當供應鏈中某一節點爆發風險,若未能及時發現并控制,則會沿著供應鏈以一定概率向相關聯節點企業傳播,最終可能將負面影響擴散至整個供應鏈。加強農產品供應鏈安全管理,提升其風險防控能力對推進農業發展,助力鄉村振興具有積極現實意義,而這就需要對風險在農產品供應鏈中傳染的過程及特點進行研究。
在農產品供應鏈風險研究方面,部分學者側重于風險識別與防控,Ruud等[1]概述了農業風險來源并對荷蘭畜牧業農戶實地調研,將動物傳染病作為其主要風險,認為購買保險是減小風險影響的重要策略。Diabat等[2]基于ISM模型構建食品供應鏈的風險模型,并將風險劃分為宏觀風險、需求管理風險、供應管理風險等5類。Nyamah等[3]以加納農產品供應鏈為研究樣本,對風險進行識別發現其類型與影響力存在地域性,面對不同風險時農業供應鏈各參與者風險管控能力不同。朱晶等[4]研究新發展格局下糧食安全內外部風險點,提出糧食安全風險防范的5個著力點。劉暢[5]對黑龍江、河南、河北等等省進行問卷調研獲取數據,將家庭農場經營過程各類風險劃分為自然風險、政策風險等六類,研究發現市場風險占主要地位。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在農產品風險預警模型、風險評價體系[6]、風險評估[7]、溯源追蹤[8]及應急響應[9]等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豐碩成果。
隨著風險傳染的概念逐步得到認可[10,11],眾多學者將討論的焦點轉向農產品供應鏈風險傳染。雷勛平[12]在剖析農產品質量風險形成機制基礎上對風險傳導的關鍵因素進行識別,著重探討了供應鏈中責任主體能力差異與信息不對稱兩方面風險的傳導機制。王杏[13]選取農戶、收購商、批發商、零售商為節點,結合局域世界理論分析農產品供應鏈結構,并根據風險與邊權重間關系將其歸納為兩類,分別借鑒疾病傳播與級聯失效理論探析其在農產品供應鏈中的傳染機制。喬良[14]梳理了有機農產品供應鏈風險產生的深層原因,分析風險傳導五環節并基于動態關系與靜態關系提出4種控制模式。付焯等[15]定義生鮮農產品供應鏈物流風險傳染中傳染源、傳播載體及受染者,識別物流風險五要素并對風險值進行測算,研究發現對單一方向鏈式供應鏈中高重要度節點的風險系數優化可以阻礙風險的傳染。常冬雨[16]將農產品流通供應鏈風險分為兩大類并分別建立了SIR傳播模型和負荷—容量級聯失效傳播模型分析了農產品流通網絡的風險傳導過程。Deng等[17]以酸奶供應鏈為研究對象,利用Tropos目標風險框架,提出三級易腐品供應鏈風險傳染模型,從供應鏈屬性及供應鏈重構兩方面提出解決策略。張闡軍[18]收集湖北省243家大型超市生鮮農產品供應鏈重構數據,構建風險傳導SIR模型,分析有效管控狀態下風險演化趨勢。呂波等[19]將供應鏈抽象為小世界網絡,基于SIR模型探討新技術革命時期供應鏈風險傳導新特點及影響因素,認為風險傳導呈“倒W”狀。
農產品供應鏈網絡中存在核心企業,該類企業可能為鏈條中具有較大規模和影響力的農產品龍頭企業或其他具有獨特競爭優勢的企業,網絡中核心企業數量少但其合作者眾多,具有較高的度值,而占據大多數的零散的小企業和農戶等節點度值均較小,呈現出明顯的無標度特性,趙鋼等[20]對江蘇省農產品實地調研數據擬合結果也表明農產品供應鏈網絡度分布服從冪律分布。鑒于農產品供應鏈網絡的無標度特性,本文擬基于BA無標度網絡,建立風險傳染SIR模型對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機理進行探討,以期為農產品供應鏈風險防控提供參考。
2 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SIR模型分析
2.1 模型假設
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與疾病傳播的過程存在諸多相似點,當農產品供應鏈體系中單個企業爆發網絡風險,相關聯企業由于緊密的業務往來成為風險波及者,但各企業自身抵御風險能力存在差異并非所有關聯企業都會轉化為下一個感染者,部分感染網絡風險的企業通過自身調整可以逐漸從風險中脫離,當一次網絡風險過后,企業及整個行業會加強風險監管,完善網絡風險的預警體系及應急程序,對同類風險形成一定的免疫力。現將SIR模型中的概念與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中的概念一一對應,見表1。

表1 SIR模型和農產品網絡風險傳染對應概念
為便于分析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機制,進行了如下假設:
假設1:農產品供應鏈網絡節點數目有限且相對固定,網絡中主體包括供應商、收購商、批發商、配送中心、零售商等企業,各成員被抽象成網絡中的節點,節點間的連邊代表成員間的業務往來,網絡各節點都是風險的載體,節點間連邊為風險傳染的路徑,在網絡風險傳染整個周期中無新的企業進入與退出。
假設2:供應鏈中企業均具有3種狀態,分別為易感狀態,即潛在的隨時可能爆發網絡風險的企業,其在t時刻數量記為S(t);感染狀態,即已經被網絡風險感染且有可能將該風險沿供應鏈向外擴散的企業,其在t時刻數量記為I(t);免疫狀態,即感染過網絡風險但通過自身經營管理與外界幫助從風險中恢復的企業,其在t時刻的數量記為R(t)。
假設3: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率μ除受到企業間緊密程度的影響外,還與預期懲罰力度γ有關。懲罰機制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搭便車”行為[21],對以質量風險為代表的這類個體非安全行為導致的供應鏈網絡風險而言,懲罰策略是影響風險傳染概率的重要因素。本文所提及的預期懲罰力度指當農產品供應鏈中企業產生風險行為時,其可能面臨的經濟與聲譽方面的損失與處罰,該值較大表明企業感染風險成本較高,企業會加強對各風險因子的防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網絡風險在鏈條中傳播,即預期懲罰力度為網絡風險傳染的抑制因素,受Xiao等[22]研究啟發,將有效傳染率記為,其中為可調節參數。
假設4:已經爆發網絡風險的企業經歷一段時間的感染期后會以概率從風險狀態中脫離,這是人力物力財力與企業管理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消費需求多元化,內外環境復雜多變等多種因素催生了一系列以制造商、流通企業等為核心的供應鏈網絡聯盟,網絡聯盟實現節點企業內部化,聯盟內企業一定程度上成為收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益共同體,該模式為企業快速脫離風險提供了新思路,在此定義外界助力為企業在網絡風險感染期內受到的來自其所在聯盟內其他企業的幫助,記為,一般來說,外界助力程度越大,企業從風險中恢復的速度越快,隨著感染進程的推進,聯盟內被感染企業數量增加,能提供助力的健康節點減少,外界助力值逐漸變小。
基于上述假設,歸一化處理后可構建農產品供應鏈上的網絡風險傳染模型:
(1)
式(1)中所涉及的符號及含義如表2所示。

表2 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動力學符號含義描述

(2)
2.2 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閾值分析
本文所提及基本再生數R0是指在農產品供應鏈中一個爆發了網絡風險的Ⅰ類企業在一個周期內能夠將該風險擴散給關聯的S類企業的數量,求解過程如下:
設初始狀態網絡中只存在易感企業,即I(0)≈0,R(0)=0,S(0)≈1,對方程組(1)中的式一兩邊分別取0到t的積分,可得未感染節點的密度函數如下:
(3)
其中輔助函數為:

(4)
則對(4)式求導可得:


(5)
將式(3)代入上式可得:
(6)

(7)
顯然式(7)存在一個平凡解Φ(∞)=0,則該式有正解的充要條件是
(8)
對式(8)求解得:
(9)
因此可以得到農產品供應鏈中網絡風險傳染的基本再生數為:
(10)
R0即為判斷網絡風險能否在農產品供應鏈中網絡中傳染的重要指標,當R0>1時,風險可以沿農產品供應鏈在整個網絡中傳染,當R0<1時,該風險無法在網絡中傳染。
3 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仿真分析
考慮農產品供應鏈網絡無標度特性,基于前文假設,在對模型參數進行假定的基礎上風險傳染過程仿真模擬,仿真實驗一如下:農產品供應鏈網絡中包含200個節點企業,據調查我國平均每個企業有4~5個合作者[23],綜合考慮實際情況將網絡平均度值設為4,初始狀態有一個企業已經處于風險中并向關聯企業傳播,為簡化計算將參數設為1,假設預期懲罰力度γ=0.1,感染概率μ=0.4,外界助力h=0.2,恢復概率λ=0.5,此時由式(10)可得R0=2.93>1,風險可以在網絡中擴散,初始狀態下三類企業數量隨時間變化情況如圖1所示。
圖1中結果顯示隨著風險在供應鏈網絡中逐步傳染蔓延,易感態企業數量隨時間推移呈遞減趨勢并最終趨于穩定;感染態企業數量在風險傳染初期急劇增加,到達峰值后緩步下降至趨近于零,在整個風險傳染周期內存在快速擴散的階段;從風險中恢復的企業隨時間推移逐漸增多,風險傳染初期緩步增長隨后增速變快,隨時間推移其增速再次變緩,最終趨于平穩。

圖1 各狀態企業數量變化曲線
為分析預期懲罰力度對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的影響,進行仿真實驗二,參數設置如下:預期懲罰力度取值分別為0.1、0.9,即預期懲罰力度提高,保持其余各參數數值與實驗一相同,此時風險有效傳染率降低,經計算分別為2.93、1.70,均大于1,仿真結果見圖2。

圖2 預期懲罰力度不同時節點變化曲線
可以看出隨著取值增大,圖2中3條曲線均向右偏移,即整個系統到達穩態的時間延后,此外感染態企業數量變化曲線峰值降低但其轉化為免疫態企業速度變慢,穩態時被風險感染企業與從風險中恢復企業數量都有一定幅度的減小,在整個感染周期內未爆發風險企業數量有所增加。說明預期懲罰力度這一因子更傾向于在風險的預防階段發揮作用,該值增加可以降低風險傳播規模,但與此相對應的是企業從風險中恢復的速度會受到一定影響,可能的原因是企業集中各類資源抵御風險的同時還需將其中一部分用于“繳納懲罰金”。
為分析外界助力程度對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的影響,進行如下仿真實驗三:外界助力程度的取值分別為0.2、0.8,其余各參數均保持與實驗一相同,此時值不變,仿真結果見圖3。

圖3 外界助力程度不同時節點變化曲線
從圖3中可以看出:當值增加為0.8時3條曲線都明顯向左偏移,系統以更快的速度到達穩定狀態,感染態企業數量變化曲線峰值降低近1/2,免疫態企業數量變化曲線變陡,即企業從風險中恢復速度變快,穩態時網絡中易感企業數量更多。說明來自網絡聯盟等組織的助力在有效降低風險傳染規模的同時提高了企業從風險中恢復的速度,外界助力不僅在風險恢復階段扮演重要角色,同時也是企業提升自身防御力的重要因素。
4 實例分析
4.1 M公司農產品供應鏈網絡特性參數分析
本研究選取湖北省M糧油公司為樣本,湖北省作為我國13個糧食主產區之一,其糧油產業規模在全國居領先地位,在我國糧油生產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M公司由湖北省內主要流通企業及19家糧油加工龍頭企業共同出資組建,截至目前,該公司在湖北省主要城市已建成15家區域分公司,77家糧油配送中心以及1540家糧油連鎖零售店,基本實現全省覆蓋,其旗下糧油公共品牌在全國也具有一定影響力,曾榮獲“中國十佳糧油(食品)影響力品牌”“年度新銳品牌”等稱號,M公司供應鏈網絡拓撲結構如圖4。

圖4 M公司農產品供應鏈網絡拓撲結構
利用Pajek軟件對該網絡的參數指標進行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整個網絡平均度值較小,計算過程中發現網絡中度值較大的點多集中于節點36到節點112之間,即供應鏈網絡中的配送中心節點,這與現實情況一致,在M公司的供應鏈體系中,配送中心與公司所轄連鎖店相銜接,主要職責范圍涵蓋糧油運輸與配送、糧油質量監管、商鋪經營與標準化管理、產品促銷等方面,在整個鏈條中占據重要地位,是關乎網絡流通性的重要節點。網絡的平均最短路徑長度為5.6144,糧油商品從供應商到消費者手中要經歷5到6個采購及運輸節點,供應鏈條較長,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M公司從采購到銷售整個環節扁平化程度不夠,網絡中最短路徑的最大值出現于節點113到節點852,這2個節點分別為利川市配送中心及黃梅縣配送中心轄區內的2個連鎖零售店,這一方面由于兩地在地理位置上空間跨度很大,另一方面也受到整個糧油物流配送的區域性集中程度的影響,零售店主要的進貨渠道為相應區域內的配送中心,而各縣/市尤其是相距很遠的縣/市的配送中心間交叉點很少,整個網絡體現出很明顯的區域性,跨區域間的物流配送并不成熟,也由此導致當風險發生時區域間的協調效率可能較低。整個網絡的平均聚集系數較小,表明網絡中的三元組結構較少,從區域分公司到配送中心再到零售店更傾向于鏈條式展開,節點間的緊密性不足,同時網絡的介數中心性較強,網絡中充當“橋梁”的節點占比很大,一旦該類節點被風險波及,嚴重時可能對網絡的連通性產生較大影響。

表3 M公司網絡特征參數
4.2 M公司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動力學分析
據前文模型假設,基于M公司農產品供應鏈樣本數據,對其風險傳染過程模擬仿真。仿真實驗四如下:M公司農產品供應鏈網絡中包含1653個節點企業,初始狀態有一個企業已經處于風險中并向關聯企業傳播,為簡化計算將參數θ設為1,假設預期懲罰力度γ=0.1,感染概率μ=0.4,外界助力H=0.2,恢復概率λ=0.5,此時由式(10)可得R0=6.42>1,風險可以在網絡中擴散,處于3種狀態下企業數量隨時間變化情況如圖5所示。

圖5 M公司各狀態企業數量變化曲線
觀察該仿真結果圖不難發現3條曲線整體變化趨勢與實驗一結果一致,但圖5中易感態企業數量變化曲線位于感染態企業數量變化曲線上方,二者不存在交叉點,系統到達動態穩定時未受風險感染的企業數量在580家左右,其占比遠高于實驗一中穩態時易感態節點數量與網絡總體節點數量之比。說明M公司自身存在一定程度抵御風險的能力,當系統到達動態穩定時處于各狀態企業數量與實驗一結果有所不同,但其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過程與前文所得結果基本一致。
4.3 M公司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過程影響因素分析
4.3.1 預期懲罰力度對風險傳染的影響
令預期懲罰力度取值分別為0.1、0.5、0.9,即預期懲罰力度提高,保持其余各參數不變,進行仿真實驗五,此時風險有效傳染率降低,經計算分別為6.42、4.82、3.75,均大于1,仿真結果如圖6所示。可以看出隨著值由0.1增加至0.9,系統到達動態穩定時處于易感態的企業數量增加,免疫態企業數量減少,感染節點數量曲線峰值降低,整個系統趨于動態穩定時間向后推移,與實驗二結論一致。

圖6 預期懲罰力度不同時三類企業數量變化曲線
4.3.2 外界助力程度對風險傳染的影響
調整外界助力程度的大小,設定的取值分別為0.2、0.4、0.8,即依次增加外界助力程度,其余各參數均保持不變,計算可得值均大于1,對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模型仿真,結果見圖7。在從0.2增加到0.8的過程中,易感企業數量曲線向左上方移動,感染企業數量和免疫企業數量曲線向左下方移動,系統到達動態穩定時間提前,圖7(c)中曲線斜率變陡,與實驗三結論一致。

圖7 外界助力程度不同時三類企業數量變化曲線
5 結論
本文基于風險傳播動力學SIR模型,探討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特點及影響因素,改進節點感染概率和節點恢復概率,對風險傳染過程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1)企業出現風險行為時面臨的懲罰力度是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風險傳染阻礙因子,會影響網絡風險在農產品供應鏈中的有效傳染率,加重企業風險行為面臨的預期懲罰可以有效降低風險傳染規模,但同時也拖慢了企業從風險中恢復的速度。
(2)供應鏈網絡聯盟和行業協會等組織的存在為企業抵御網絡風險提供了新思路,這些來自外界的助力能有效提高感染企業恢復能力,進而加快企業風險恢復進程,降低網絡風險在農產品供應鏈中擴散規模,網絡聯盟將各零散企業聚集成利益共同體,號召各企業共同抵御風險,有效縮短了風險從爆發到湮滅整個過程的耗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