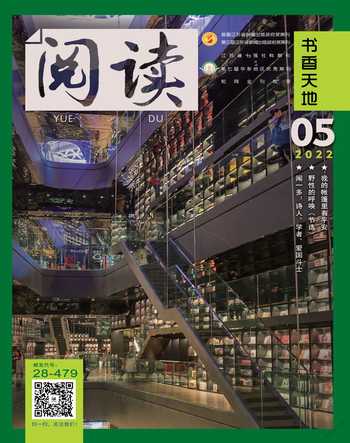顧篤璜:“過云樓畔飄來水磨腔”
姚澤民

蘇州闊家頭巷26號,緊鄰網師園,這是一座修復的明代建筑,被乾隆譽為“江南老名士”的沈德潛舊居,如今是蘇州昆劇傳習所所在地,常常能聽到昆曲余音繞梁。
每逢周二、周六上午9點半左右——準確地說是“九點十五分”,顧篤璜先生必來“沈德潛故居”——昆劇傳習所雅集拍曲。生于1928年的顧先生,雖已年逾耄耋之年,今年九十有四,即便步履蹣跚,但在昆曲這件事上,顧先生一點也不打馬虎眼,時不時也去園林里雅集,這兩年他還熱心排練昆曲《紅樓夢》。
顧篤璜先生出身于蘇州望族,是怡園后人,他的一生,都與園林和昆曲糾纏在一起。130年前,顧家先祖顧文彬萌生了退隱之心,在老家蘇州建造一座園林以安度晚年,園林的名字叫“怡園”。顧篤璜,是顧家的第五代,常常也被稱為“江南最后一個名士”。
蘇州的園林中唯有怡園是最近市中心的,城市是在欲望和塵世中生存,山林卻是逃避和回歸。顧篤璜說,很多園林造在離住宅很遠的地方,因為要逃避繁華,文人想到山林里去,卻又舍不得出來,于是就把山林搬到城市里來,在鬧市中尋山林之趣。要說山林之趣,哪一座園林沒有呢?怡園最脫穎之處在于它不僅是是蘇式園林中的精品,也是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更是昆曲人士清唱雅集的場所。
顧家除了怡園,還有個大名鼎鼎的“過云樓”,由顧氏先祖創立。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過云樓收藏甲江南”之稱,經過六代人150余年的傳承,其藏書集宋元古槧、精寫舊抄、明清佳刻、碑帖印譜800余種之巨。據說上海博物館的青銅器和書畫、南京圖書館的古籍善本、蘇州博物館的昆曲資料等等,都有顧氏家族的捐贈。
曾經的過往已經浸潤到了骨子里,顧篤璜后來的人生陰差陽錯結緣了昆曲,并癡守昆曲幾十年不曾停歇。1946年,第一志愿填報了美術的顧篤璜,卻被錄取進第二志愿戲劇,后來得知因為戲劇專業報考者太少,顧篤璜被調劑了過去。
解放以后,顧篤璜從事蘇州宣傳文化工作,從1951年開始,一直分管蘇州昆劇團工作,并著手復興蘇州昆曲。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顧篤璜不僅親自參加培養了“繼、承、弘”三輩演員,還曾對許多昆曲傳統劇目進行過劇本整理和導演加工,對老一輩昆劇藝人的口述及影像資料的搶救更不遺余力,搶救那些至今還沒有失傳的昆劇傳統劇目(舞臺表演)。顧篤璜先生還與幾位助手認真整理、校勘、打印那些稿本,他們從徐凌云先生的《慕煙曲譜》、李翥岡先生的《同詠霓裳曲譜》《猶古軒曲譜》以及蘇州顧氏過云樓舊藏曲本中,選錄出一千四百多折,編成十六函一百六十冊,幾乎把能夠搜集到的明清以來的劇本和曲譜都聚攏了,可謂國內最全的選本。
那些年,他還面向全國辦過11期昆劇傳承學習班,搶救瀕臨失傳的昆劇;1989年,蘇州昆劇傳習所與蘇州大學中文系合作,創辦漢語言文學專業昆劇藝術本科班;他還主持編選了《韻學驪珠新編》《昆劇選淺注》《昆劇穿戴》《昆劇傳世演出珍本全編》等等;2004年,他還導演了轟動兩岸三地的蘇昆大戲《長生殿》 ……
生在現代的蘇州,心在傳統的姑蘇。出生名門的顧篤璜,堅守“傳統”,他認為傳統劇目保存得愈好,昆劇愈是不會消亡,保存好昆劇傳統劇目是昆劇能立于不敗之地,具有永恒價值的根基。
顧篤璜對昆劇的迷戀始于兒時。在他記憶里,解放前,蘇州人吟唱昆劇是件普遍的雅事。拍板、唱曲、走臺步,顧篤璜在濃郁的昆劇氛圍中耳濡目染。在上海讀中學時,他發起組織“鳴社”票社,被推舉為社長。1942年,他跳級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1946年,又考入蘇州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戲劇專業。他自1951年任蘇州市文聯戲曲改進部部長,便一直從事戲曲工作。1955年,蘇州市文化局成立,他被任命為副局長。但是,未及兩年,他就辭去副局長職務,參與籌建蘇州市戲曲研究室,任副主任,兼管江蘇省蘇昆劇團藝術工作。
2001年5月,昆曲申遺成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口頭遺產和非物質遺產”。也是從這個時候起,全國各地昆曲表演和組織開始層出不窮,各種昆曲創新、改良不斷,昆曲似乎一片繁榮。但是顧篤璜也開始擔心,是不是這樣就意味著原汁原味的昆曲就更少了?改良真的是改“良”嗎?忽視傳統文化和背景的昆曲,會不會反而讓整個昆曲走向錯誤的方向呢?
2004年,著名作家白先勇主持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首演,利用現代劇場的種種概念,給予舞臺以全新的視覺體驗。自2004年4月在臺灣首演至2005年4月內地八大名校巡演,青春版《牡丹亭》一石激起千層浪,各路媒體紛紛報道,許多年輕人甚至認為這才是昆曲應有的面貌。
而談到這版《牡丹亭》,顧先生說:“在青春版中杜麗娘竟然能夠公然坐在柳夢梅的大腿上!古代女子是什么樣的?女子碰到男子說話的時候,一定是先用衣袖擋住自己的臉,含羞帶怯的。”說到興起,他還表演了女子遮羞的動作,他對于一些革新的昆劇篡改了古代傳統文化風俗感到十分氣憤。顧篤璜認為,這些傳統的舞臺和動作細節,是反應古代生活的,不從傳統出發如何能看到真正的古代生活和文化?
“知道昆劇的,都知道那并不是昆劇。”對于這種錯誤的改編,顧篤璜有些無奈。即便是青春版《牡丹亭》10年內演了近200場,但是藝術沒有上去,甚至有些昆劇演員連音也沒有唱準,如何算得上昆曲、昆劇的振興呢?但是在目前改革、創新為主要勢頭的情況下,顧篤璜甚至被扣上了“保守派”的帽子。但他一心只是在搶救昆曲,專心做這一件事。
顧篤璜期望有一批人能把昆曲事業繼承下去。他對前景仍然充滿希望,“社會向前發展了,肯定會尊重傳統,最難的就是這個階段。例如臺灣,這個階段過去了,有無數人癡迷昆劇,我們要渡過這個難關。如果因為我不盡力,給昆劇造成損失,我會責備自己。”
臺灣方面有朋友誠摯邀請顧篤璜再次組團前往演出,但是他手頭沒有拿得出手的成熟演員,也許還要等上一段時間才能成行。他說,自己此生最后一個心愿是讓蘇州教育學院昆劇班畢業生自主創業,辦成一個民辦昆劇團。“這個昆劇團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傳統的,讓觀眾欣賞到純正的昆劇。”他現在仍為保護、搶救昆劇文化遺產缺乏資金而困窘,對此,他坦言,“我對名利無所求,所以能夠愉快,我所追求的是我認為應該做的事情。”
從始至終,顧篤璜牢記恩師趙越教授的教誨,“不管做什么工作,先要弄清楚它的歷史,才能減少盲目性。”正是秉承這樣的歷史責任感,他忠貞不渝地甘當昆劇文化遺產的守護者,無怨無悔。
(摘自《發現非遺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