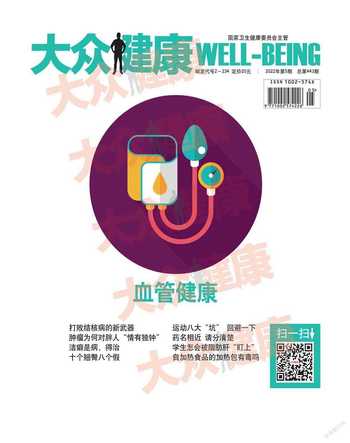劉方軍“腦血管微雕手藝人”
王玉萌
劉方軍,主任醫師,神經外科博士,首都醫科大學三博腦科醫院神經外科三病區主任。擅長腦血管病、顱腦腫瘤等神經外科疾病的治療。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腦血管病專業委員會青年委員,中國醫師協會腦膠質瘤專業委員會委員。
印象中,醫院的神經外科主任都是嚴肅的。但首都醫科大學三博腦科醫院神經外科三病區主任劉方軍臉上,總是洋溢著笑容。在神經外科的從醫路上行走了24年,46歲的劉方軍已經完成復雜神經外科手術2000余例。他認為,神經外科大夫不應止步于“開刀匠”,而應該站在患者的角度,下硬功夫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劉方軍每天都要面對與腦血管疾病的生死博弈,他時而化身“血流導航員”,時而成為“拆彈專家”。對他來說,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看到經他治療的患者回歸正常生活。
12歲男孩佳佳的腦子里長了一個腫瘤,一開始在醫院被當成病毒性腦炎進行治療,腫瘤體積在3個月內瘋長了3倍,手術風險太大了,醫生建議轉院。佳佳父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找到劉方軍的。仔細查看影像資料后,劉方軍發現佳佳患的是長在小腦上的實質性血管母細胞瘤。這種腫瘤看上去就像是雜亂的血管團,血供豐富,又長在小腦上,手術風險確實很大,一丁點失誤就會導致顱內大出血。這就好比拆彈時碰錯了一根引線,隨時可能導致炸彈爆炸。但如果腫瘤沒有全切掉,以后還會復發導致出血。
怎么辦?劉方軍一句鏗鏘有力的“可以手術治療”,給了佳佳一家人希望。可如何能讓腫瘤實現全切,又保證孩子術后的生活質量呢?劉方軍帶領團隊為佳佳制定了完備的“拆彈”手術策略,并組織全科對圍手術期的注意事項進行了詳細的討論。術中,劉方軍在高倍顯微鏡下完整切除了腫瘤,且未損傷周圍重要神經和血管。經醫護人員悉心照料,術后不到一周,佳佳就能下地鍛煉,很快康復出院了。
不斷攀登,攻克難題,讓腦部疾病患者得到更到位的治療,這是劉方軍給自己和團隊定下的規矩。他帶領團隊率先采用頜內動脈搭橋術治療缺血性腦血管病,被《歐洲神經外科雜志》評價為治療缺血性腦血管病方面“切實有用的聰明創新方法”,“巧妙的顱內外血流搭橋,解決了臨床的關鍵問題”。
2008年,從首都醫科大學北京市神經外科研究所博士畢業后,劉方軍到首都醫科大學三博腦科醫院工作,成為國內頂級神經外科專家石祥恩教授的學生。
“石祥恩教授常教導我,手術時,一定要重視每一針、每一線。怎么縫?縫的位置在哪兒?都必須嚴謹。一針縫不好,就可能造成災難性后果。”這顆嚴謹的種子,就這樣埋在了劉方軍心中。每臺手術,無論大小,無論難易,他都嚴陣以待。術前評估、全科討論、手術時間安排、器材準備、患者身體和心理的調整……劉方軍及其團隊一絲不茍的態度,帶給患者的是安心,更是希望。
提到劉方軍,64歲的周大爺感激地說:“劉主任真是難得遇到的好醫生。”周大爺先前是個“固執”的退休大爺,確診為雙側頸內動脈狹窄8年多,由于諱疾忌醫,選擇動態觀察,不愿意到醫院治療。2020年6月起,周大爺經常有頭暈的癥狀,還發生了言語不清、四肢無力,被確診為急性腦梗死。這可把周大爺的家人嚇壞了,他們堅持把周大爺送到了三博腦科醫院。檢查發現,周大爺的左側頸內動脈頸端閉塞,右側頸內動脈近段偏心性重度狹窄,雙側頸動脈分叉及頸內動脈近段管壁增厚伴多發斑塊形成。這樣的情況必須立即治療,不然斑塊脫落還會堵塞大腦血管造成腦梗死。
“我很排斥進醫院,看見醫生就害怕。”周大爺說,但他在門診第一次看到劉方軍,心里就產生了信任感。劉方軍結合影像資料,通俗易懂地介紹了這種疾病的危險程度,讓固執的周大爺決定接受手術。最終,周大爺接受了轉流管保護下的頸動脈內膜剝脫手術,僅通過一個小切口,就將堆積在血管里的“斑塊垃圾”清理干凈了。
“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劉方軍說,臨床的嚴謹源于扎實的醫學根底,手術臺上的從容源于平時的反復訓練。他的辦公室里擺著各種手術練習器械,忙完了手頭的事,他總要抽點時間練練手。
無數次的訓練,造就了劉方軍的手上功夫。“血管搭橋手術要在直徑1毫米左右的血管上進行,用比新生兒胎毛還要細的、直徑約0.01毫米的縫合線,縫9到11針,把兩根血管縫起來。手稍微動一下,就有可能引起血管爆裂。”劉方軍自信地解釋說,“這就相當于在小米粒上進行微雕藝術。”
真正的微雕,可以“慢工出細活”,但手術對時間是有嚴格要求的。在顯微鏡下進行血管搭橋,太慢,血液循環供應不上;太快,血管承受不住巨大的壓力,容易爆裂。劉方軍不僅對搭橋血管的縫合角度把握得不差分毫,而且能在有限的時間里完成“微雕”,讓同行們為之嘆服。
這么多年的臨床手術經歷,也讓劉方軍有了新的思考:手術不能解決所有患者的問題,如何才能讓更多人擁有腦健康意識,預防腦部疾病的發生呢?現在,結束一天繁忙的臨床工作,劉方軍有了一個“副業”,那就是參加網絡直播,呼吁更多人關注腦健康。在他的帶動下,團隊也開始從事大眾科普宣教,把深奧難懂的醫學術語、神秘的腦科知識,轉換成大眾聽得懂的語言。
現在,劉方軍已擁有12萬粉絲,回復粉絲們的提問成為他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不管是多小的問題,他都會詳細地回復。在他眼里,患者的事都不是小事。“我能體會咨詢者的那種焦急,所以不管多忙,我都要抽空回復。有時候下手術很晚了,第二天就會一早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