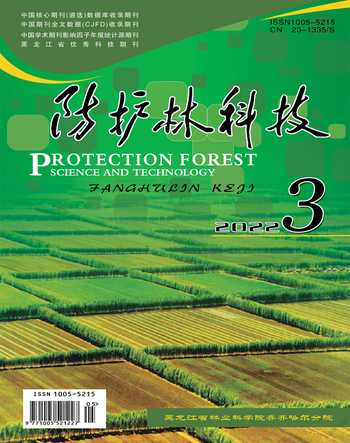不同技術措施對河岸帶治理效果的研究
李歡




摘要為更好地保護牤牛河兩岸林地資源,開展了“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相結合的生態治理技術體系研究,結果表明:2.0 m和3.0 m寬的梯形緩坡簡易壩體對河岸有效防護率較對照分別提高119.5%和136.6%,林木成活率和有效防護率均在90%以上;2.0 m和3.0 m寬的壩體樹木成活率、有效防護率、平均淤積深度、沖淤量均極顯著高于對照和1.0 m壩體寬度。“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比其他兩項技術平均淤積深度分別提高了0.29 m和0.96 m,治理效果顯著,其平均淤積深度和沖淤量極顯著高于其他兩項措施。通過應用“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對河岸帶進行治理,4年間累計沖淤深度1.51 m,沖淤量20.14萬m。
關鍵詞河岸帶治理;生物技術;簡易壩體;壩體寬度
中圖分類號:S727.26文獻標識碼:Adoi:10.13601/j.issn.1005-5215.2022.03.010
Study on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echnical Measures on Riparian Zone Governance
Li Huan
(Liaoning Ecological Experimental Forest Farm,Chaoyang 122000, Liaoning)
Abstract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the forest and land resources on both sides of the Mangniu River, the research of ecologic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system was carried out by combining “biotechnology + simple engineering technology”.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rates of the simple dams with trapezoidal gentle slopes at 2.0 m and 3.0 m width were increased by 119.5% and 136.6%, respectively, and the survival rate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rate were both above 90%;survival rate, effective protection rate, average deposition depth, and scour and deposition volume of dams with 2.0 m and 3.0 m widt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and dams with 1.0 m width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technologies, the average sedimentation depth of “biotechnology + simple engineering technology”was increased by 0.29 m and 0.96 m, respectively. Treatment effect was remarkable. The average sedimentation depth and erosion-sediment volum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two measures. The accumulated erosion and deposition depth was 1.51 m, and erosion-sedimentvolume was 201 400 min 4 years by“biotechnology + simpl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riparian zone.
Key wordsriparian zone governance; biotechnology; simple dam;dam body width
河流生態護坡是在保護、創造生物良好的生態環境和自然景觀的前提下,保證護坡措施具有一定強度和耐久性的同時,兼顧護坡工程的環境效應和生物效應,達到恢復生態環境、治理水土流失的目的[1-3]。傳統的河道護坡主要使用漿砌或干砌塊石護坡、鋼筋混凝土護坡等。這類護坡工程的造價相對較高,且是水下施工,日后維護工作難以實施。其最大的缺點還在于,它僅僅從滿足河流防洪、排澇、航運和引水等基本功能的角度出發進行設計施工,忽略了與河流同為整體的動物、植物及微生物的生存發展,很少考慮對環境和生態的影響[4]。近年來,以重建受損河岸生態系統為目的,同時融合防洪、生態、景觀和河流自凈效應為一體的生態護岸技術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并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與探索[1,4-6]。
牤牛河為大凌河支流,其水流急,來勢猛,兩岸多為沙質土壤,故河流侵蝕、沖刷嚴重,致使河道兩岸塌陷十分嚴重,經常引起河道堵塞[7,8]。牤牛河周邊多為村莊,農業種植和耕地侵占河岸帶現象普遍存在,植被覆蓋率低,生態緩沖帶較窄[9,10]。同時,項目區年降水量小,且多集中在6—8月,河床比較高,河床與河岸高差小,故河流轉彎處沖毀農田和林地現象已呈高發趨勢[10-12]。因此,如何以最小的治理成本,同時兼顧保護農田、林地等效益,以水體安全、順應自然為基本原則探索出適合牤牛河等鄉村河流兩岸治理保護新技術迫在眉睫[7,11,12]。為更好地保護牤牛河兩岸林地資源,本研究在對該河流基本特點、兩岸植被分布、河岸損毀程度等調查的基礎上,開展了“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相結合的生態治理技術體系研究。生物技術選用大徑階柳樹作為護岸樹種,以“品狀聚集模式”為主要內容;簡易工程技術以“梯形緩坡簡易壩體”為主要措施,并對栽植成活率、有效防護率、生長量、淤積深度和沖淤量等指標進行分析,以期為鄉村河流及小河流河岸帶生態治理和恢復利用提供理論依據和技術支撐。
1材料和方法
1.1試驗地概況
本項目試驗地設在遼寧省生態實驗林場新秋林班,位于牤牛河馬友營段河岸帶,基本無防護工程,沖刷嚴重,兩岸已無明顯岸坎。
1.2試驗方法
1.2.1梯形緩坡簡易壩體修建
利用河道內碎石、泥沙等,在河床與水位浮動區交界處,沿著河流方向,利用鉤機等機械,人工修筑1條梯形簡易壩體。壩體的高度直接影響了栽植區泥沙等淤積深度,太高容易造成淤積深度過大,泥沙淤積過厚,完全掩蓋柳樹;太低容易造成抵御水流沖擊強度差,起不到有效降低河流水速的作用,甚至導致栽植的柳樹被沖毀。因柳樹截干保留高度為2.0~2.5 m,故壩體的高度設置為截干留高的1/2,即為1.0~1.5 m高。
1.2.2調查方法
試驗地治理效果調查項目包括栽植成活率、有效防護率、當年生長量、沖淤深度和沖淤量。
(1)栽植成活率=成活株數/栽植株數×100%[13];
(2)有效株數=成活株數-傾斜株數[13];
(3)有效防護率=有效株數/栽植株數×100%[13];
(4)當年生長量(m)=用全株所有生長枝條的平均長度表示[13];
(5)以未治理的地段為對照(CK),各隨機抽取3個樣點,立標尺。以標尺與地表接觸面為零起點,測量各處理每年沖淤的深度,取平均值為H,用下式計算沖淤量(V):
V=(H+H+H+…+H)×M
式中:V為沖淤量(m);H為每年沖淤深度(m);n為測量年份;M為沖淤面積(m)[13,14]。
1.2.3不同壩體寬度對治理效果的研究
試驗設計梯形緩坡簡易壩體上底寬度分別為1.0、2.0和3.0 m 3個處理,以不設置梯形緩坡簡易壩體為對照(CK),每個處理設置3次重復,1年后調查栽植柳樹的成活株數、倒伏株數,計算出有效防護率;測量淤積深度,取平均值,計算沖淤量。
1.2.4不同措施治理效果分析
生物技術:選擇胸徑10~20 cm的柳樹,在干高2.0~2.5 m處截干,保留全部輔養枝,品字狀聚集栽植,頂端朝向上游來水方向。
簡易工程技術:在河床與水位浮動區交界處,沿著河流方向,修筑梯形緩坡簡易壩體,上底寬度≥2.0 m。
分別調查“生物技術”、“工程技術”和“生物技術+工程技術”3種治理措施的成活率、生長量,測量淤積深度,取平均值,計算沖淤量,分析治理效果差異。
1.2.5不同年度應用“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治理效果分析
自2018年開始采用“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進行治理試驗,治理面積13.3 hm。在河床與水位浮動區交界處,沿著河流方向,修筑梯形緩坡簡易壩體,壩體高度1.0~1.5 m,上底寬度2.0 m,壓實,不留缺口,靠近河流側的斜坡坡度<30°,選擇胸徑10~20 cm的柳樹,在保留干高2.0~2.5 m處截干,保留全部輔養枝,呈“品”狀聚集栽植,頂端朝向上游來水方向,每667 m挖栽植穴55個,深栽,埋至干基上0.5 m處。
連續調查2018—2021年各年的成活率、生長量,測量淤積深度,取平均值,計算沖淤量。
1.3數據處理分析
應用Excel、DPS等軟件對數據進行整理和分析。
2結果與分析
2.1不同壩體寬度對栽植柳樹成活率和防護率的影響
通過對不同梯形緩坡簡易壩體寬度研究結果表明,不設置梯形緩坡簡易壩體(CK)直接栽植柳樹,河流流速過快,22株出現了傾斜現象,有效防護率為41.0%;1.0 m寬的壩體損毀嚴重,成活率為79.0%,15株出現了傾斜現象,有效防護率為64.0%;2.0 m寬的壩體有輕微的損毀現象,壩體高度有所下降,6株出現傾斜現象,有效防護率為90.0%;3.0 m寬的壩體無損毀現象,壩體高度略有下降,3株出現傾斜現象,有效防護率為97.0%(表1)。2.0 m和3.0 m寬的壩體有效防護率較對照分別提高51.0和56.0個百分點。通過對不同處理差異顯著性分析得出,2.0 m和3.0 m寬的壩體成活率和有效防護率與對照相比差異極顯著(表1)。
2.2不同壩體寬度對平均淤積深度和沖淤量的影響
由表2可見,不設置梯形緩坡簡易壩體(CK),有效防護率低,平均淤積深度0.15 m,沖淤量為60 m;1.0 m寬的壩體平均淤積深度0.26 m,沖淤量為104 m;2.0 m寬的壩體平均淤積深度和沖淤量分別為0.47 m、188 m;3.0 m寬的壩體平均淤積深度和沖淤量分別為0.54 m和216 m。2.0 m和3.0 m寬的壩體平均淤積深度和沖淤量均極顯著高于對照和1.0 m壩體寬度(表2)。通過對不同處理差異顯著性分析得出,處理與對照、處理與處理兩兩之間差異極顯著(表2)。
2.3不同治理技術對平均淤積深度和沖淤量的影響
由表3可見,單獨使用“簡易工程技術”進行河岸帶防護,無法起到有效防護作用,平均淤積深度下降0.13 m,沖刷量大于淤積量,造成了嚴重的水土流失;單獨使用“生物技術”,平均淤積深度為0.54 m,沖刷量為3 601.8 m;而使用“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其防護效果最佳,平均淤積深度為0.83 m,沖刷量為5 536.1 m。“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比單獨使用“生物技術”平均淤積深度提高了0.29?m,比單獨使用“簡易工程技術”提高了0.96 m。通過對平均淤積深度和沖淤量2個指標差異顯著性分析得出,“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處理極顯著高于其他2項措施,因此,可應用“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對河岸帶進行治理。
2.4不同年度應用“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治理效果分析
由表4可見,自2018年開始采用“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在試驗地進行治理。調查發現,2018—2021年間,柳樹保存率略有下降,特別是2021年降雨量增大,河水水流增大,出現了個別柳樹被水沖刷而傾斜的現象,故保存率略有下降。隨著柳樹的成活,根系的逐漸生長,當年生長量逐年增加。平均沖淤深度和沖淤量第1年最大,然后逐漸減小,2021年河水增大后略有回升。4年后,累計沖淤深度1.51 m,沖淤量20.14萬m,說明應用“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對河岸帶起到很好的防護效果。
3結論與討論
對河岸帶治理來說,選用有效的河岸帶治理保護技術至關重要[5,7]。應因地制宜,根據生態建設要求選取相應的河岸帶生態治理方法,使河岸帶和水位浮動區顯現出極高的生態效益[7]。同時應充分考慮農村地區的經濟承受能力,控制成本投入[5,11]。前人研究結果表明:柳樹表層根系能夠在水中及土壤含水量很高的土壤中生發,且生長狀況良好,有足夠的耐水性;柳樹表層根系能夠匍匐在岸坡的土壤表層,形成1個毯式保護層,抵抗來自雨水和河水的沖刷,具有極好的保護功能[15];河流的水位往往具有浮動性,工程護岸位置相對固定,不能應對不同水位對河岸的沖刷,而柳樹能夠隨著水位的升降在近水處快速地形成表層根系保護層;相對于工程護岸,表層根系護岸有更好的生態效益,且費用較低[16]。
本研究表明:2.0 m和3.0 m寬的壩體對柳樹的有效防護率分別較對照提高51.0和56.0個百分點,成活率和有效防護率均在90%以上;而且2.0 m和3.0 m寬的壩體成活率、有效防護率、平均淤積深度、沖淤量均極顯著高于對照和1.0 m壩體寬度。“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比其他2項技術平均淤積深度分別提高了0.29 m和0.96 m,治理效果顯著;而且“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處理各項防護指標均極顯著高于其他2項措施。通過應用“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對河岸帶進行治理,4年間累計沖淤深度1.51 m,沖淤量20.14萬m。
綜上所述,河岸帶治理可應用“生物技術+簡易工程技術”,即生物技術選用大徑階柳樹作為護岸林樹種,以“品”字狀聚集栽植;簡易工程技術以“梯形緩坡簡易壩體”為主要措施。此項技術對加固河岸、控制水土流失和生態修復效果明顯。
參考文獻:
[1] 夏繼紅,嚴忠民.生態河岸帶研究進展與發展趨勢[J].河海大學學報,2004,5(3):252-255
[2] 張建春. 河岸帶功能及管理[J].水土保持學報, 2001,15(6):143-146
[3] 曹梅英,李東海.由治汾美化工程看生態河堤建設[J].山西水土保持科技,2001 (3):35- 36
[4] 夏繼紅,嚴忠民.淺論城市河道的生態護坡[J].中國水土保持,2003(3):9-10
[5] 張立波,于穎.遼河干流鐵嶺段生態治理探討[J].黑龍江水利科技,2013,41(4):180-182
[6] 呂晶,高甲榮,王穎,等.不同護坡植物對岸坡土壤性質的影響及效應分析[J].水土保持研究,2010,17(3):101-104,109
[7] 楊海全.喀左縣牤牛河存在的問題及其生態治理模式研究[J]. 黑龍江水利科技,2020,48(7):108-110
[8] 宮正.牤牛河匯流河段泥沙淤積特征及減淤措施研究[J]. 水土保持應用技術,2021(3):13-14
[9] 韓衛.牤牛河匯流段泥沙淤積特性分析[J]. 東北水利水電,2014,32(3):26-27,47
[10] 孫磊,劉福林.牤牛河河口交匯區泥沙沖淤試驗研究[J]. 東北水利水電,2016,34(4):51-53,72
[11] 馬海濱,鐘天鳳.牤牛河項目區小流域綜合治理經驗[J]. 北京農業,2013(12):231
[12] 李云生.牤牛河流域水文特性分析[J]. 現代農業科技,2011(8):237-238
[13] 劉瑛.土壤生物工程技術在河岸生態修復中應用效果的研究[D].北京:北京林業大學,2011
[14] 楊斌,石培賢.劉家峽水庫柳樹固岸林防護效應試驗[J].水土保持通報,2006(4):44-47
[15] 婁會品,高甲榮.京郊琉璃河河岸帶土壤生物工程的生態效應[J]. 西北林學院學報,2016,31(1):304-308
[16] 李書博. 牤牛河重點山洪溝防洪治理工程設計分析[J]. 黑龍江水利科技,2015,43(4):10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