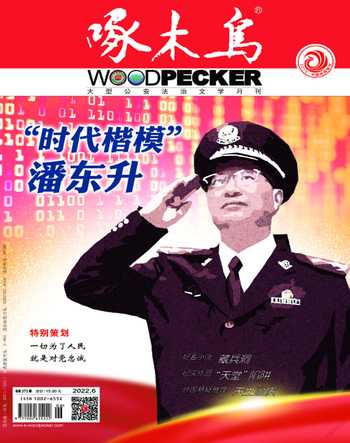五嬸的三拳兩腳(短篇小說)
高中倉

五嬸勤勉,早早起來清掃了門前院落,澆了花,喂了雞,洗了頭,還把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不一會兒,村東頭的劉娘進門了。
劉娘嬉笑著催五嬸去吃席:“他五嬸呀,咱悶子今兒娶媳婦您得早點兒過來呀,掌柜的說有您在禮房招呼他就放心。”五嬸笑呵呵地應承著,連聲祝賀侄兒悶子娶了個好媳婦。五嬸在村里可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當然得在禮房待著。五嬸的體面明面是人能干,頭腦活泛,背面或多或少依仗著她掌柜白玉敏在鎮上文化站大小是個人物的面子。
劉娘瞅著五嬸家新起的闊闊大大的門房和敞敞亮亮的兩座廂房,一色兒青磚藍瓦白墻,門窗上明亮潔凈的大玻璃反射著晨光,院子里越發顯得清新雅致,眼睛里流露出酸酸的羨慕,劉娘說:“都說咱吉祥學得好,一心考軍校,今年暑期可得喝你家的喜酒呢。”一提起兒子吉祥,五嬸臉上瞬間就像院子里的桃花,笑著說:“那是當然的,到時候一定得請他劉娘。”五嬸意猶未盡,接著說,“女子吉瑞成天說要學他哥,將來考個醫學院當醫生。娃們的事情,咱幫不了多少,由他們闖去。”話說得平常隨意,話里的滿意自豪味兒卻濃稠得像蜜。
五嬸與劉娘邊說邊走到門外,這當口兒,巷道里走來了村主任媳婦、快嘴快舌的青葉,青葉抬頭望著五嬸家高聳在門房上的一間脊樓稱贊不已:“嘖嘖,村里人都說你家玉敏是猴子托生的,腦瓜子空靈。這間脊樓在全村可是冒了尖,全鎮也少見,古色古香的,有個詞叫啥來著,想起來了,叫流光溢彩,你看看,四個角兒全翹起來,像鳥兒要展翅的樣子,嘖嘖,羨煞人了。”青葉在村里是一位多少有些文化的人,贊美起人來一套一套的,五嬸就壓低聲音在青葉耳邊說:“這是你玉敏兄弟給一位領導畫了一幅畫,領導特別喜歡,打招呼讓縣仿古建筑隊幫忙修的。”
晌午時分,村西頭的邢建立家呼呼啦啦來了十幾名鄰縣穿制服的法院工作人員,說因為邢建立家拉貨的汽車去年有一起交通肇事,一直沒有賠付到位,今天來強制執行,要把汽車拖走。西灘村偏僻,一下子來了這么多吃官飯的人,陸陸續續來看熱鬧的人就多了起來。邢建立的父親,一個八十歲的老頭兒,他躺在地上抱著車轱轆耍橫,死活不松手,等著在附近磚瓦窯上干活兒的三個兒子回家。法院的干部也不想硬整,索性就打算等一會兒,等老漢的兒子回來后講明利害,再扣押更穩當。邢家老太太顛著碎步,滿村道挨家挨戶敲門叩窗叫人幫勢。五嬸礙于蓋房時邢家的汽車幫自家拉運過水泥、沙子的情面,經不起別人攛掇,隨著劉娘、青葉擠進了看熱鬧的人群。
五嬸家所在的馬莊鎮西灘村,懶洋洋地睡臥在千年黃河灘地西邊陡坡下,東南北三面盡是一望無際的黃河灘涂,仰頭西望,是百余丈高的懸崖峭壁。相傳,西灘村的人來自九省十八縣,大多是明清兩代逃荒的、躲難的在這兒蝸居謀生,家族鄉土觀念甚烈,獨特的生存環境衍生出獨特的風土人情——耍橫斗狠,用拳頭講道理。平原村莊的人不愿意去西灘,西灘的人也懶得去塬上,漸漸地,鎮政府的管理就弱化了不少,不少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西灘村人就由著性子野。
膀粗腰圓的邢建立聽了來人添油加醋的學說,來不及更換踩泥抱磚一身泥漿的破衣服,跳上摩托車就飛奔回村。待邢家兄弟到家的時候,家門口已經圍攏了二三百看熱鬧的人。看到橫臥在地上一身灰土、滿臉鼻涕眼淚的父親,火暴的邢建立甚至沒有耐心聽完法院干部說明原委,一拳就把帶隊的干部打倒在地。法院的其他人還沒有反應過來,邢家另兩個兄弟也猛撲上去,打成一團。這時,人群中邢家的親屬故交,一些平時窩著私怨、憋著憤恨的人相互吆喝著也一齊參與進去,伸拳出腳,借機發泄。三名女法官奮力勸阻,卻被邢建立的妻子一幫人緊緊圍住了。人群中不斷有人大聲吆喝攛掇:“敢來西灘村抓人,打的就是你們,大家都上手打呀!”年輕的村主任媳婦青葉先上了手,劉娘也跟上伸出了腳,五嬸稀里糊涂地緊跟著,在女法官身上比畫著擩了三拳兩腳。這場打斗的結果,法院的十二名工作人員全部不同程度受傷,其中重傷一人,帶隊的法官嚴重腦震蕩;輕傷三人,五嬸、劉娘和青葉參與圍毆的那位女法官一根肋骨骨折;其余八人輕微傷。
事情惹大了。十里八鄉傳開了,驚動了縣上,驚動了地區。邢家三兄弟跑了,村上其他很多參與的人溜了。公安出動了,從當天晚飯時開始,警車一會兒進、一會兒出,警笛聲徹夜呼嘯。村里白天打人的現場被五六盞大燈照射了大半夜,十幾名警察圍著現場在拍照、繪圖,細致地搜尋撿拾相關物品,凡是白天在場的群眾被一一請去做談話筆錄。這時,頭腦活泛一點兒的人主動去投案了,村里傳言最多的就是誰誰誰又被抓走了,誰誰誰又去投案了。
以往西灘村的狗吠聲相當跋扈囂張,既給村里自己人壯膽,又給村外陌生人造成恐嚇,但自從警察開槍打死村主任家的大黃狗“威虎”后,村里再也沒有聽到一聲狗叫。次日一大早,村里電線桿上多年不響的喇叭響了,通知全村人都到村中廣場開會,宣布對昨晚在火車上抓獲的邢建立依法刑事拘留的決定。五嬸這才明白,這些人犯的法叫“暴力妨害公務”。
五嬸心臟劇烈跳動,想出村去她妹妹家躲幾天,可一見到村中巡邏走過的警察一個個全副武裝,頭戴防暴鋼盔,腳蹬防暴皮靴,手執警棍,五嬸嚇得腿一下就軟了。村里跑了的參與毆打的人員被陸續抓回,或依法拘留或依法逮捕,五嬸緊閉大門驚恐地蜷縮在家里沒了主意。掌柜白玉敏聞訊回來了,問清楚五嬸當時的情況后,氣得直哆嗦,臉一會兒煞白一會兒紫青,在院子里來回轉了幾十圈,嘴里只嘟囔著“犯罪了、犯罪了”。過了半晌,白玉敏不轉圈了,嘴里也不嘟囔了,他去村道里走了一圈回來后,就開始給五嬸收拾被褥碗筷,決定帶五嬸投案。五嬸十二分地不愿,她丟不下這個家,沒了她的家那還是家嗎?白玉敏強壓著沒有讓自己吼出聲來:“丟不下也得丟,村主任的媳婦青葉昨天已經投案了。自作自受,咎由自取!”五嬸一步三回頭,磨磨蹭蹭地跟著白玉敏走上了投案自首的道路。
辦案民警沒有為難五嬸。五嬸人實在,不說謊,記性也好,她一五一十地說清了自己的三拳兩腳,也悔恨自己不懂法,表示對自己參與毆打傷害的法院女干部誠懇道歉。問題已經交代清楚了,也悔改了,也道歉了,五嬸現在最關心的是她什么時候可以回家。家里的新房剛剛收拾停當,但新式馬桶還沒有安裝,洗澡用的太陽能熱水器也沒有安裝;兩個孩子周末回來她得給帶錢;蘆筍地承包的合同得續簽;還有五嬸想把娘家母親接來在她家新房住一兩個月,真急人呀。她催問過辦案民警,民警說:“現在才是偵查階段,還要經過起訴階段、審判階段,長著呢,耐心等吧。”
一天,五嬸的訊問室門外傳來爭執的說話聲,一陣高過一陣,五嬸能聽清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我保證不打她,你就讓我問問她,她究竟為什么要打我?這個問題我百思不得其解,睡不著覺呀。”訊問室的門打開了,走進來一位纖細柔弱的女青年,她拉開一張椅子,坐在五嬸面前,仔細端詳了五嬸一會兒,輕聲問道:“你就是楊靜,你認識我嗎?”五嬸搖搖頭,說不認識。女青年的聲音有點兒顫抖,問道:“我們有冤仇嗎?我傷害過你嗎?”五嬸繼續搖頭,堅決地否定。辦案民警插話說道:“楊靜你聽好,這位就是那天在西灘村被你們毆打的陳法官,在醫院住院治療半個月了,剛恢復不久。你們這幫人太不可思議了,連法官都敢打,暴力抗法,無法無天,豈有此理。”陳法官顯然有些激動:“楊靜,謝謝你們下手還不至于過重,我這條命才得以保住。我今天特意來見你一面,就是想問問,你為什么要打我?”
五嬸這才看清了被她們打傷的法官的真實模樣,一位細皮嫩肉、文文靜靜的女青年。陳法官看上去非常虛弱,面容憔悴,呼吸氣短,滿眼含淚,說話時需不斷停歇。這位前世與自己無半點兒冤仇、今生與自己無任何瓜葛的柔弱女人竟被自己打傷了,五嬸無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一條裂縫馬上鉆進去。她沒辦法回答對方的問題,沒有任何理由,沒有任何托詞,甚至沒有任何可以狡辯的空間和蒙混的余地。五嬸啞口無言,尷尬至極,臉憋得通紅,她只能一句接一句地說道:“對不起!真的對不起!我給你跪下吧!陳法官你狠狠地打我吧,打死我都行!”
見五嬸不愿正面回答,陳法官繼續問道:“楊靜,我再問你,你可以不替我考慮,但你應該為你的丈夫和孩子考慮呀。被你們毆打的法警中,有一位就是你丈夫的領導——文化站李站長的親外甥,你覺得你丈夫還有在文化站轉正的可能嗎?聽說你兒子學習很優秀,一心想報考軍校,你這暴力妨害公務的行為一旦坐實,你兒子還能上軍校嗎?你女兒將來還能上985、211嗎?”
如雷轟頂,五嬸這時才知道這次打人會有這么嚴重的后果,頓時頭腦發脹,耳朵嗡嗡直響,豆大的汗珠從頭上往下滾,一下子癱軟在訊問椅上。陳法官后面還說了些啥,五嬸一句也沒有聽清,一句也沒有回答,自從她知道自己的行為會給丈夫和孩子造成災難性后果的那一刻起,五嬸就打定了主意去死!只有這樣才能讓自己解脫。
看守所的十六號監室里關著八名在押人員,安全起見,夜晚睡覺時每個人輪值一小時,穿黃馬甲,坐著值班,瞪眼哨。五嬸思來想去,只能在自己輪值的一小時里想辦法完成死的愿望。凌晨三點,五嬸當值,放眼望去,四周沒有可以利用的物件,她站起身,正準備拿頭往墻上撞,監室的喇叭里就傳來嚴厲的喊話聲:“十六監室的三號押員!你干什么?坐下!”緊接著,監室門被迅速打開。值班民警從監控視頻里看見五嬸的異常舉動后立即啟動應急預案,一名民警喊話制止,兩名民警臨場處置,五嬸被帶走關進了禁閉室。
第二天,看守所王所長提解五嬸到管教室談話。王所長說話不緊不慢,和藹可親,他問五嬸:“押員楊靜,聽說你昨天晚上鬧騰著想死?”五嬸不知道該怎么回答。王所長繼續說:“這個容易,你家西灘村就在黃河邊,如果打定主意了,等你從監獄出去后,隨時可以實現,死一千次的機會都有。但在我們看守所,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保證不了全部押員的絕對安全,組織要我們這些人干什么?”五嬸靜靜地聽著。王所長察覺到五嬸愿意聽,而且能聽進去,就推心置腹地跟她聊起家常:“楊靜呀,你知道不,看守所一二號監室關押的都是重刑押員,宣判死刑后,全部上訴,希望上級法院重新審理后能夠改判,生的愿望相當強烈,沒有一個人想死。你犯的罪行并不嚴重,不值當去死呀。聽說你有一個特別讓人羨慕的家庭,丈夫有本事,兒女學習好,所以,你現在要考慮的不是怎么去死,而是如何好好活的問題。這次一時糊涂,經不起別人攛掇,參與侮辱毆打法官,已經違法犯罪,那就老老實實地接受法律懲處,然后端端正正地勞動改造,出來后重新做人。有你就有這個家,沒你這個家就倒了,你丈夫需要你,兩個孩子更不能沒有母親呀,你說是不是?”王所長的話,句句像重槌,結結實實地敲打在五嬸的心坎上。五嬸開始悔恨平生接觸這樣的人、聽到這樣的話語、學習這樣的道理的機會太少太少。如果以后……五嬸不愿意想以后了,她覺得自己的以后太遙遠、太虛幻了。
每晚躺在監室的大通鋪上,頭上是明晃晃耀眼的長明燈,耳邊是磨牙、放屁、說夢話、咳嗽的聲音,五嬸一宿一宿地失眠,她想得最多的一個問題,也是最折磨自己良心的一個問題,就是自己無緣無故的為什么要參與打人?究竟為什么呀?她問了自己千百遍,恨不得把自己的手腳剁爛。
五嬸的刑期為一年,她被送往一個專門做各種帳篷的工廠接受勞動改造。車間內一排排縫紉機呼啦啦地轉動著、嗚嗚地鳴響著,一捆捆帆布、棉布、網紗從外面運進來,加工成各式各樣的帳篷運出去,五嬸逐漸習慣了這里緊張而忙碌的生活,埋頭踩踏機器翻轉布料,心里默默地期盼著釋放回家的日子。
五嬸愛勞動,愛長時間高強度的勞動,因為在重體力勞動中可以麻痹自己的腦子,讓她不去想問題。五嬸害怕黑夜,長長的夜晚躺在床上難以成眠,思緒不由自主地飛到自己的家,經常幻覺她家的院子里荒草沒膝,野兔奔突;三座新房經風吹雨淋已經墻皮脫落,房間里塵土彌漫,鳥糞遍地。這時,五嬸不得不去想那個長久嚼嚙她心靈和拷打她靈魂的問題,為了一個毫不相干的人,做了一件毫無道理的事情,自己犯了罪,既傷害了無辜善良的好人,又搭上了自己兒女和丈夫的前途,還搭上了自己和和美美的日子。兒女的前程毀了,興旺的家庭毀了,自己的罪孽太深重了,五嬸懊悔到極點,深深地把頭埋進被窩。
同宿舍一個年輕的女人珍珠喜歡與五嬸拉家常,珍珠拉著五嬸的手仔細端詳了一會兒,說道:“五嬸呀,你這雙手白軟白軟的,人也看著慈眉善目,說你打人,我怎么都不會相信呀。”五嬸輕輕搖搖頭,嘆口氣,說道:“都怪我糊涂呀,就當時那亂糟糟的場面,礙于那家人曾幫過我家的情面,我只是輕輕比畫著擩了幾拳,我一個女人家,能打個啥嘛。不懂法害死人啊!”后來,五嬸跟珍珠越走越近,五嬸問珍珠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也不知道陳法官的身體恢復得怎么樣了,能不能正常上班?不會留下什么后遺癥吧?”珍珠當然也不知道,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給五嬸寬心:“放心吧五嬸,應該不會的。”
妹妹楊寧來帳篷廠探望過五嬸兩次,說了一些家里與村里的情況,妹妹盡可能挑好的方面說,但五嬸總是從壞的方面去猜想。掌柜白玉敏受不了鎮文化站同事的閑言碎語,到南方闖蕩去了;兒子吉祥考上了北方的一所礦業學院,沒有上成他一心向往的軍校;女兒吉瑞也轉到妹妹楊寧家附近的學校上高中了。五嬸小心翼翼地問妹妹:“吉祥、吉瑞怨恨我嗎?”楊寧沒有正面回答她的話,只說了句:“自己的兒女恨什么恨呀,走到天盡頭,你還是他們的媽呀。”這卻勾起了楊寧對吉祥不能報考軍校那件事的回憶,吉祥嗚嗚地大聲哭著,頭使勁兒往墻上撞,楊寧的心是一擰一擰地疼,可這些,只能爛在肚子里,不能給姐姐說呀。聽說村主任跟老婆青葉離了婚,五嬸就試探著問妹妹:“你姐夫說沒說過離婚這話?”楊寧給五嬸吃了個定心丸:“姐夫你又不是不了解,刀子嘴豆腐心,他能離開你,他能舍得吉瑞、吉祥嗎?姐你就把心踏踏實實放肚子里吧。”
話題扯到西灘村,妹妹楊寧興奮地給五嬸說起了村里的變化,楊寧說:“姐呀,你離開的這一年時間,你們西灘村的變化可大了,聽說縣里很重視,給村里選派了駐村干部,縣里好些單位都給村里投錢、投項目,新修了一條幾丈寬的通村柏油馬路,村道也變成了水泥路,聽說還要給村里新建一所學校、一個休閑廣場和一個老年人照顧中心。上次我去你們村代你領糧食直補,碰見你們村的新村主任,精精神神、正正氣氣一個青年人,他讓我轉告你,村里歡迎你們這些一時糊涂的人回來。”五嬸問:“那新村主任知道我?”楊寧嗔怪:“當然知道呀,人家村主任跟我說話時一句一個楊靜;還有,你家蘆筍地的合同村主任已經替你續簽了,怎么能不知道你呢?”楊寧繼續說,“那青年村主任還說,你們村有溫泉,能養魚,打算開辦養魚場、蓮藕養殖場、魚宴酒店什么的好幾家企業呢,村里的人都可以入股參與,包括你們這幾個即將回來的新人,姐呀,村主任說你們是新人。”五嬸眼睛里閃爍出希望的亮光,嘴角微微動了動,想說什么卻又沒有說出來,楊寧卻來了勁頭兒,盯著五嬸的眼睛鄭重其事地說:“姐呀,咱可得好好改造,把遵紀守法刻到咱的心上,以后好好過咱的日子,為咱自己,也為貼心貼肺對你好的親人呀。”五嬸嘴角又翹了翹,仍然沒有說出什么話來,只是用力地點著頭。
閑暇的時候,五嬸總是想那位被自己傷害的陳法官,她身體恢復得怎么樣了?五嬸清晰地記得那天在訊問室跟她談話時,陳法官臉色泛白,說話時呼吸短促,身體虛弱搖擺。一想到這兒,五嬸內心就感到深深的歉疚和不安,有時像貓抓似的慌亂和錐刺似的疼痛。骨子里其實很善良的五嬸漸漸產生了一個念頭,從這里出去后,她要去看望那位被自己無辜傷害的陳法官,當面向她鄭重道歉,誠懇地發自內心地說一聲對不起!無論陳法官原諒不原諒,她都要去,只有這樣,以后的日子吃飯才能踏實,睡覺才能安穩。
五嬸把她的想法說給珍珠聽,她擔心陳法官會怨恨她,不見她。珍珠替五嬸分析說:“人家是法官,境界比咱高得多,她怨恨的是你不懂法,并不是你這個人。你徹底改造好了,成為一個新人站在她面前,她自然會歡迎的。”五嬸還在尋思,說:“如果陳法官身體真的有了后遺癥,我想去她家做保姆伺候她,你覺得咋樣?”珍珠笑著說:“這就沒有必要了。以后,陳法官跟你、我,包括所有人,都平靜地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后來,這個念想愈來愈強烈,而且愈來愈迫切了。五嬸每天都在思謀著如何道歉,她已經積攢了一筆不少的津貼和獎金,她一定要置辦一件像樣的禮物,給陳法官帶上;最好穿上家里衣柜里那件黃藍粗格外套,既素凈也穩重,更顯對陳法官的尊重。五嬸對自己去看望陳法官并向她道歉的主意很滿意。她在帳篷廠的日子,就這樣在急切的盼望和等待中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