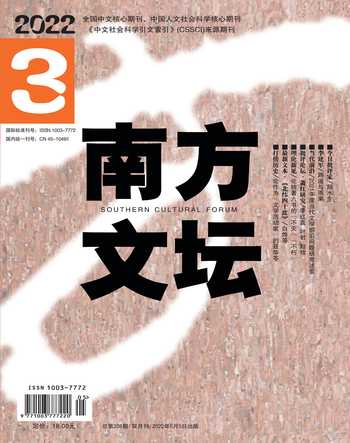論中國當代災難文學創傷敘事的情感表達
創傷敘事包括歷史、文學、影視等多種表達形式,它是個體或集體對戰爭、疾病、貧窮、災難、家庭暴力等的承受和記憶,作為一種表現個體或民族心理、情感創傷的敘述,具有強烈的生命抒寫和崇高的悲劇美學特征。感覺是心理的來源與基礎,災難襲擊時所造成的一個短暫、迅速、封閉的時空,切斷了人對過去和現在的歷史連續性,身體感官承受了外界災難事件的深刻撞擊,留下了強烈的情感記憶和心理創傷,這種創傷情感具有應激反應的特質,并在人的潛意識心理中長期存在。情感表達是災難文學敘事的核心,小說的情感表達策略決定了小說敘事的時間、空間、角度等,作者對創傷情感體驗的深度、廣度、個體體驗的差異性,是創傷敘事的出發點,由此決定人物的性格、命運、生存方式、價值取向、人生理想,筆者試圖以疾病、地震等集體創傷和個人情感、心理創傷為中心,選取阿來長篇小說《云中記》、張翎短篇小說集《余震》、畢淑敏長篇小說《花冠病毒》為例考察創傷敘事的情感表達策略。
一、身體經驗與創傷情感的發生
魯迅小說《祥林嫂》中的主人公祥林嫂逢人便訴說兒子阿毛的悲慘故事,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婚姻、家庭的沉重打擊后,再次來到魯鎮的祥林嫂“手腳已沒有先前一樣靈活,記性也壞得多,死尸似的臉上又整日沒有笑影”,泣不成聲的祥林嫂在反復的傾訴中消磨了魯鎮人對她的同情和憐憫,這是遭遇疾病、貧窮、失去親人的一連串不幸而引發身體上的應激反應,突出的是人物精神內核的改變以及對創傷記憶的反復表達。創傷敘事作品中的人物無論是親歷者、幸存者、見證者,都承受著身體至精神的雙重苦痛,這種苦痛的情感記憶會長期伴隨著人物的命運。
(一)疾病、死亡預兆與悲情
《花冠病毒》第十三、十四兩節敘述了女主人公羅緯芝在感染病毒之初到惡化的身體反應及對死亡預告的恐懼。首先是身體的疼痛,“就在她準備以身相許的時刻,突然胸口一陣劇痛,一種非常特殊的從未經歷過的內在之痛,從椎骨前方深處生發出來,利劍一樣刺透了她的肺腑”①。這種疼痛“仿佛一臺馬力強大的切割機,以鋒利的刃口,螺旋著掃過她的肺葉”,還有刀絞般的腹痛、不停息的咳嗽、咳血、喘息、全身蜷縮等。其次是情緒的悲觀。小說在描述羅緯芝為了判斷自己是否真的發燒,用了一段很長的文字來表現人物在遭遇疾病襲來時心理時空的延宕。“繼續等待了一千年,她死死盯著表,在過去了10分鐘之后……她顫抖著手抽出了體溫計,目光灼灼看過去,這一次,紅蛇攀上了38℃。”②這是人對疾病乃至死亡的萬分恐懼時感覺到時間的停滯與沉重。再次,作者表現了人物在預知生命大限之時對生的眷戀和希冀。小說通過羅緯芝拼命忍住悲痛與母親的電話別離,以及人物的內心獨白中對臥病母親的擔憂、對未來婚姻的憧憬、對為人妻母的期待、對百草的交代、對未來的寫作規劃等一幅幅生動畫面的展現,體現出鮮活的生命渴求以及細膩的母女悲情。
(二)肢體的分離與情感的克制
“創傷記憶中的情感具有無時性、傳染性,這意味著創傷不僅發生在過去,也發生在現在,每一次創傷回憶過程中被喚起的個體情感反應,都是創傷的復現。”③《云中記》從一個單腿姑娘央金的視角敘述了幾個片段。片段一:五年之后重回廢墟的央金在那個特定的時刻扔掉拐杖的單腿舞蹈。小說用“身體向左”“身體向右、向前”“單腿起跳、再起跳”“身體震顫”“身體彎曲”“蜷縮”“雙手緊抱自己”來表達人物的“憤怒、驚恐”“絕望的掙扎”。由于過去的創傷情境的復現,使得姑娘找回了在排練廳里無法表現出的舞蹈的生命力量,這是情感的升華。片段二:輪椅上的央金在廢墟中緩緩向前,淚流滿面。盡管之前一直控制不讓自己看見云中村。當云中村一出現,她的情緒就完全失控了。片段三:(插敘)被斷梁斜插進膝蓋,一條腿實際上已經被切斷了,只剩一點筋肉連著的央金“忍受著極端的痛苦閉上眼睛一言不發”。片段四:在周圍的人無法施救的情形下,央金自己切斷腿爬出來。片段五:回到房子的廢墟前,叫了一聲“媽媽”,央金霎時完全忘記了無人機和事先的排演,“身子一軟,就昏過去了”。作者反復讓人物在控制情緒、控制流淚到瞬間失控,來強化創傷情境的再現對創傷情感記憶的強烈沖擊,體驗生命的荒蕪與憤激。
阿來筆下以極其凝重的筆墨刻畫了突如其來的地震災難對人們身體的戕害,人們來不及體驗和說出驚恐:
現在,他們都大張著嘴,還沒有發出聲音。有人茫然地看著自己的腿在墻的另外一邊。有人驚訝地看到自己懷抱著一塊沉重的石頭,血從胸腔里涌出,像是想要淹沒那塊石頭。沒有受傷的人,從地上爬起來,腦子嗡嗡作響。有人發現自己好好活著,旁邊人已經死了。所有這些人,他們就要發出撕心裂肺的聲音了。但現在,他們的嗓子發干,聲帶僵直,即便把嘴巴張得再大,也發不出聲來。④
作者采用了第三人稱、旁觀者的敘述視角,這種看似冷靜的筆調,使得人物與自身、作者與人物、讀者與人物的體驗產生了一個審美距離,蘊含著人與身體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物的聯結、人與群體的關聯、人與自然的關系等。創傷起因于一次震驚,實際上它無情地切斷了人們頭腦中時間的連續性。這種災難的震撼性、突發性,在人物的情感上則是以一種延遲的方式來表達,“茫然”“驚訝”“嗓子發干”“聲帶僵直”是情感爆發之前的力量蓄積,這樣的描寫比呼天號地潑墨般的傾瀉,更符合創傷的即刻性與延時性。
(三)視覺、聽覺、觸覺、幻覺多種感官的聯動與情感體驗
描寫人物遭遇槍擊、饑餓、性侵等傷害時,通常會通過身體的各種感官來表達復雜的情緒和情感。比如《余震》中小燈遭遇繼父性侵,內心的驚恐和怯弱、猶豫、憤激,是通過“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說,推開他,推開他”“身體卻癱軟在……動彈不得”,以及“小燈的心和身體劇烈地扭斗”“突然狠狠地伸直了腿”等來表現不幸少女的身心掙扎與反抗。《空巢》里的田田和秦陽被困在電梯里,忍受饑餓的刺痛、唾液的干枯,愈來愈昏沉,被救時打開電梯門那一剎那看見“眩目的白光”,聽到“遙遙”的聲音。《向北方》里的中越被槍擊時“肩膀麻了一下,有股溫熱的東西”,他扶著的達娃“如抽了筋剔了骨似的軟綿”,他耳朵里看到了裘伊的跌跌撞撞,身體笨重地落下。感官體驗是創傷情感體驗的基礎,通過眼、耳、口、鼻、身等與外界接觸過程中形成的痛感、質感、量感等,使人所經歷的事、物、環境在生理和心理上形成一種巨大的陰影,繼而升華為愛、恨、懼、失落、絕望等復雜的情感體驗。
二、創傷敘述的情感言說類型
“在創傷敘事中,創傷敘述者努力地以一種個性化的,以經驗為根據的敘述方法來擴展讀者對于創傷的認識。這種敘述方法突出強調描繪創傷記憶帶來的痛苦矛盾情緒,并且警示我們,如果不加以留意,創傷可以自我產生。”⑤創傷敘述將讀者帶入人物的回憶中,跟隨人物去重新體驗創傷的情境,在人物的矛盾、困惑、絕望與掙扎中反思創傷,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來加工或者建構新的創傷情感體驗,而創傷敘事將個人的創傷記憶外在化、具體化,通過不斷地閱讀與反復呈現,最終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的、潛意識的心理記憶。
(一)獨白式
內心獨白是創傷敘述的一個典型形態,在災難敘事的小說文本中,人物的創傷情感獨白可以有多種形式,比如喃喃自語,《云中記》中的阿巴在決定上山給謝巴家的亡魂做一場法事的時候,先用骨頭卜了一卦,小說寫道:“他閉著雙眼,說:請為我顯示清晰的兆頭,我要上山去為村里人作法,我不要碰見地震,我不要山石把我砸倒在路上,我要平安回來。……不要讓我倒在上山路上。”⑥在阿巴上山途中,他一直在祝禱,將他的心愿向裂縫訴說,向山神訴說。作者還以意識流的方式,反復描述阿巴在災后目睹村民的慘狀時,心里不斷地對著山神哭喊,回到廢墟的阿巴在對一家又一家亡魂安撫的祭事中的悲痛自語,對消失的云中村無限的眷戀、回憶和淚水。有時,作者采用夢境敘述的方式來表達人物的內心愿望,比如阿巴夢見自己從容不迫地端坐在云中村,在明亮的世界中和村子一起向江水中滑墜。還有《余震》里小燈在淺淺的睡意中隱約聽見了腳步聲和水聲,看到了一個年輕的女人,一輛女式自行車上坐著一個瘦小的女孩。這就是小燈心底那個推不開的窗戶,是童年的母女快樂的時光。夢境以一種創傷自我修復的方式呈現。除此之外,書信、日記、字條等文體的運用,也是直接呈現人物內心情感的一種方式,比如《向北方》里陳中越給女兒小越的書信,《余震》的篇末小燈寫給亨利醫生的那句話。
(二)傾訴式、問答式
更多的人物創傷記憶是通過傾訴的方式來表達的,傾訴的對象可以是戀人、師長、親人、朋友、心理醫生,甚至是動物、植物等自然界中的事物。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心理學上的精神分析療法便是采取自由聯想、分析夢境、自我闡釋、認識自我等方法,使病人將長期壓抑在潛意識中的精神創傷表達出來,以消除其情感上的癥結,減輕情緒上的壓力。《余震》開篇是小燈被轉診至心理治療科接受全面評估,作品用心理醫生接診、病人自愈作為一個完整的敘述框架,將小燈丟失了的母愛、童年畸形的性侵、成年艱難的愛情等用回憶的方式進行敘述。整部小說就是一個傾訴的故事,童年遭遇的創傷生生切斷了小燈與外界情感溝通的橋梁,從此在走向自閉、孤獨的末路上痛苦掙扎,人物沒有主動的傾訴,包括沃爾佛醫生的治療,小燈也是被動且抗拒的。小說中心理醫生與病人的治療只能稱之為問答式。《向北方》中的中越與達娃也是類似這樣的情感克制的狀態,兩人始終都沒有將各自婚姻中的矛盾、痛苦、癥結向對方傾訴,達娃生前唯一的傾訴是“裘伊和尼爾是我今生今世的債,我欠了別人的,也只有這樣慢慢地來還了”。因為誰都不能治療對方的傷,語言是無力的,中越用輕輕地擁抱來表達對達娃的安撫。《云中記》中的傾訴比較多,如仁欽向舅舅的傾訴,央金向云丹和阿巴的傾訴,阿巴向亡魂、山神、鹿、裂縫、石雕、大樹、鳶尾花等的傾訴。傾訴是一種治療,阿巴承擔了幸存下來的村民們向不幸死去的親人們傾訴的中介,阿巴的祭事就是傳達村民們對亡魂的哀思、傾訴、寄托、安撫。
(三)重復回顧式
創傷的主題使得小說在結構、情節、語言、人物設計等諸多層面產生了相應的變化。對于受創者來說,創傷敘述是對死亡危機、生存危機或者人的身體、精神主體尊嚴遭遇強烈的沖擊時無法承受的敘述,“創傷代表著一種‘基本的錯位’,它不只是一個病理的概念,而且也是心理和現實聯系的一個謎。延宕使創傷具有一種歷史力量,它并不僅僅是在忘記創傷之后創傷的重復再現,而且也是指在通過忘記或在忘記之中,再次遭遇如同第一次的創傷打擊。創傷的歷史性潛伏在經驗的不可理解之中”⑦。創傷敘述中常見的手法是重復,一是災難的重復,比如《云中記》中的地震之前的水電站滑坡、一分二十八秒的地震、之后的余震、裂縫的擴大、再次滑坡直至云中村墜入江中整體消失,整個故事的講述才形成一個完整的災難敘事的框架。這種自然災難的演進,有各種不同的征兆,發生之后還會繼續演進。而人為的創傷,比如《余震》中的小燈,新婚的第一夜,便如同重復遭遇少女時被性侵。《向北方》中的達娃堅定地認為裘伊就是那個“鐵打的男人”,自己為了償還前兩任丈夫的債,必須忍受裘伊一次又一次的暴虐,這種暴虐越來越尖銳,直到最后以結束達娃的生命而劇終。《花冠病毒》中無處不在的病毒威脅,從于增風、羅緯芝、陳天果、蘇雅等一個個被感染的患者敘述中,不斷地重復著病毒的無窮威力和人類的束手無策。
因為小說在情節、結構的設置上呼應了這種創傷潛伏的歷史性、再現性,所以作者會安排人物在不同的時間反復地經歷創傷,使得創傷成為敘事的一個隱藏的線索,《云中記》全書反復地描述地震發生的那天,阿巴一次又一次地想到了妹妹生前的情景,地震災難分解為無數個碎片覆蓋到小說整體的敘述過程中,與人物的所有行動、思想、心理、情緒、情感都緊緊融合在一體,每一個人物身上都能看到與災難的聯結。而隨著時間的推進,在重復的創傷回顧的敘事中,情節呈螺旋狀發展,從云中村、移民村再到云中村的廢墟、即將滑坡的廢墟等。而仁欽、阿巴、央金、中祥巴等不同的人物身上不僅親歷和見證了創傷,而且還體驗著創傷的互相治療和自愈。重復的敘述帶來重復的閱讀、重復的體驗,就如同一組一組主體類似而角度、構圖相異的圖像,阻斷了讀者對整個作品的直入性的整體認識,而不得不深入每一個回顧性的創傷畫面中,捕捉不同的細節,這些直面死亡的重復畫面構成了極大的情感效應,成為全書情感表達的焦點。
三、創傷情感的核心元素
“創傷敘事將文章節奏、順序以及創傷經歷的不確定性內在化,使它們蘊藏于潛在的情感結構中。這種敘事方法揭露了與創傷經歷者進行交流時的一些障礙:諸如創傷經歷者在交流時表現出的沉默,伴隨沉默產生的沒有反應、否認、分裂、反抗以及抵制等。”⑧在創傷敘述中,不論何種災難形式,自然災難抑或社會災難、人為災難,在創傷延宕期都會形成情緒創傷或情感創傷,“情緒創傷( emotional trauma)指由于情緒壓力或情緒上受到打擊而導致情感的失調。任何一種引起強烈不愉快情緒,都可造成情感創傷。人的正常情感需要被剝奪,也可產生情感創傷。情感創傷的表現有消沉、憂郁、自卑、失眠、健忘等,重者可形成情感失調”⑨。這種情感失調,有時甚至發展到無法正常地處理人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的關系。然而災難敘事的深邃和崇高就在于它表達了人類從恐懼災難、逃避災難到成長為直面災難、承擔災難的情感升華與治愈過程。
(一)孤獨
孤獨是創傷敘事中的核心情感元素,《花冠病毒》中于增風生命彌留之際的遺書,既是他解剖尸體的病理報告,也是他對瘟疫的職業思考和他在病毒入侵時肌體的痛苦煉獄的心理記錄,這是一個抗疫領袖與病毒誓死的孤獨抗爭。張翎短篇小說集《余震》中的主人公,或者因為童年失去雙親、父母情感的異化而自閉,或者因為曾經歷過苦難的童年而孤獨地成長,或者因為愛人的自殺、出軌、暴力等婚姻的種種不幸而獨自療傷,在小說的敘事中都表現為孤獨敏感的心理世界。對孤獨的抒寫幾乎貫穿了整部作品,張翎在書的前言中自述“天災把生存推到極限,在這樣的極限中一個七歲的靈魂過早地看見了人生的狐貍尾巴。見識了真相之后的王小燈,再也沒有能力去正常地擁有世上一切正常的感情”⑩。從小燈的轉診報告突出的“失眠”“頭痛”“自殺”的字眼,到醫生見到的病人“雙手圈住兩個膝蓋”“臉上兩個黑洞似的眼睛。洞孔大而干枯,深不見底”開始,小說便設置了一個“孤獨”的敘事黑洞,而小燈醒來之后狠命扔掉的書包意味著她與溫情的世界從此隔絕。小燈的孤獨表現為多種生理和情感失調,如生理上的失憶癥、受害妄想癥、長期失眠、陣發性的頭痛,人際關系中的緊張、焦慮和因為時時害怕失去的驚恐。《空巢》中的田田在離婚后一直緊閉著情感的大門,直到電梯停電的那一段黑暗的時空,生命的渴求將兩顆敏感自衛的心真正地結合在了一起。《向北方》里中越和達娃從始至終都在孤獨的情感旅途中,小說設置了孩子的角色,中越對小越、達娃對尼爾,是兩人孤獨黯淡的情感世界中的明燈。
《云中記》中的阿巴從擔任祭師被村里評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開始,他的生命就與山神、亡魂緊密相連,他回到即將隨山體滑落的廢墟,與逝去的亡靈為伴,王金勝認為“阿巴是阿來崇高美學的獨特史詩英雄形象”,小說“并不著意凸顯聲嘶力竭和決然而起的抗爭,它通過生命場景和細節的定格,捕捉緘默中的內在力量”11。阿巴堅持選擇自己的信仰和使命,從面對死亡的困惑、哀憐、痛苦和恐懼,到莊重與肅穆的精神世界的重塑與升華,阿巴在孤獨的廢墟之旅中,依靠大自然的巨大力量將心靈與大地融為一體,坦然而莊嚴。在這里,“孤獨”成為對創傷體驗、創傷情感的一種緩慢治愈,如果沒有阿巴遠離移民村的現實生活,重回廢墟與大自然的對話,沒有阿巴的堅持孤獨、反思孤獨、享受孤獨,史詩般的英雄形象則失去了強大的內心力量的依托。
(二)疼痛
作為疾病敘事的《花冠病毒》,毫無疑問是以疼痛為身體敘事的出發點,尤其是在羅緯芝、陳天果、蘇雅生命最垂危的時刻,疼痛侵襲了他們身體的每一個細胞。由于這疼痛,他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事業、愛情、親情、生命和理想。張翎說:“《余震》是關于疼痛的。一種天災帶來的,卻沒有跟隨天災逝去的心靈疼痛。一直到我寫完最后一個字,我依舊沒有找到緩解這種疼痛的藥方。結尾處小燈千里尋親的情節是我忍不住丟給自己的止疼片。真正忍不住疼痛的,其實是我自己。”12創傷敘事是作者跟隨人物感受疼痛、體驗疼痛、治愈疼痛的過程,“疼痛”成為敘事的原點,小燈的震后反復的頭疼,導致種種工作的中斷,既是遭遇重擊的后遺癥,也是心靈的余震。小燈只有兩種生存狀態“疼和不疼”,每一次的疼痛,就是創傷的重復和再現。小說通過這種真切的肉體的疼痛,來表現“余震”給人們帶來的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創傷。由于疼痛,她的情緒和情感變得“突兀”“清醒而慌亂”。《空巢》中何淳安目睹李延安自殺之后的慘景,“腕上的傷痕如鋸齒般參差不齊”,這是剛烈之后的綻放,畫面似乎無關疼痛,只留下一長串的落寞、不甘、掙扎和絕望的逃避,卻是疼痛的另外一種符號。
《云中記》中的“疼痛”由每一個個體的疼痛點輻射和擴散,最后凝聚為一個村子的集體創傷。疼痛在每一次情景再現的時候發生,比如央金悲痛地屈服于公司將她坐在輪椅上穿行廢墟的視頻作為背景畫面而舞蹈,終于她“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接著“央金病倒了,發燒,陷入噩夢”。而阿巴在撫摸父親的祭師服裝的時候,回憶隨水電站滑入江中的時候,在每次安撫亡魂的時候,這些悲痛的災難性的畫面都會重現。“創傷敘事中的‘強迫性重復’(repetition compulsion),指敘述者(包括作家)不由自主地重復某一段話、一個意象、一張圖片,乃至一個動作等。”13疼痛作為一種由神經感官所經歷的感受,在創傷敘述中通過淚水、哭訴、噩夢、禱告等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呈現為隱性或者顯性的情感敘事。
(三)悲憫
災難文學是作家悲憫情懷的寫照,無論是從集體、民族的宏觀角度來反思災難,還是從個人化的敘事來書寫災難,都是作家在人道主義視閾中對現實苦難及生存倫理、生命意義的表達。這種“悲憫”意味滲透到小說敘事的人物、情節、語言、意象等各個方面,表現為詩化的心靈、直面災難的勇氣、參悟生死的曠達和物我合一的超然。《云中記》是一部詩化的小說,小說用詩化的語言細細描繪出祭師阿巴與云中村、神靈、亡魂的對話。村子里的一切,樹木、小溪、泉眼、花草、園子、石碉、馬、鹿群、鳥、雪山都具有鮮活的生命,它們的精神世界都是相通的。比如村子里的人請求阿巴作法救救村子的風水樹、神樹,努力祈禱的阿巴“哭了”,他將老柏樹的枯葉和樹皮放在祭臺上燃燒,讓焚燒后的青煙向山神訴說,“有什么話就跟山神說去吧,我不懂您的心意,您就跟山神說說為什么非死不可吧”14。重回廢墟,想到云中村的即將消失,小說反復描繪祭拜山神和撫慰亡魂的阿巴心中充滿“哀憐之情”“悲愴之情”,回想從前祭山神的喧鬧熱烈,一個人的祭山儀式讓他“倍感凄涼與哀傷”。
《余震》中的沃爾佛醫生有著類似于阿巴的悲憫胸懷,沃爾佛醫生給小燈的生日寄語是“雪梨·小燈·王:接近完美的作家,不太合作的病人,一直在跌倒和起來之間掙扎”。作為心理醫生的他從一開始就給小燈停止藥物,改為安慰劑,一直鼓勵小燈誠實面對自己,鼓勵流淚,鼓勵小燈推開心底那扇封閉的窗。《花冠病毒》在展開抗疫前線采訪的敘事中還穿插了李元和羅緯芝的生死之戀,即使是愛情,也不能改變他們為病人消耗最后一滴鮮血的決定,擁有抗體的羅緯芝經過無數次的抽血、輸血,纖細的手臂“針孔疊著針孔”,李元把去傳染病院給病人試用“白娘子”作為“使命”。作者在小說的封底留下寄語:“這本書里,滲透了我人生的結晶。……我當醫生搶救垂危病人時對心臟的每一次按壓。我對鮮血從恐懼到習以為常的每一分鐘目不轉睛。我面對瀕死者臉龐溫和凝視的告別……”白衣天使救死扶傷的崇高職業道德,使得小說災難抒寫的悲憫情感具有了厚重的立意和高尚的智慧。
四、象征——災難敘事的情感凝結
所有的創傷只有在受創人能夠將創傷視作個體生命的一個過程,逐漸從自憐、痛苦、憤恨、屈辱、不平、悲哀,走向平靜、慈悲、寬容,接受過去,并且面向未來的時候,創傷才能逐漸自愈。如何將身體的、心靈的疼痛化為具象的、外在可感的形象,創傷敘事通常用的方法是隱喻和象征。這種象征性的隱喻,表現為一種場景、意象或者畫面、聲音。《向北方》里的中越雙手撫摸著達娃的墓碑高低不平的碑文,他仿佛看到了“陽光”“草地”“金黃色的蜜蜂”“漫山遍野的格桑花”。小說以中越和尼爾組合為父子畫面而緩緩落幕,格桑花是達娃美好的生命、對愛情畢生的追求的象征。《余震》中的“最后的那扇窗戶”是小燈的情感世界最初被擊潰的地方,她到最后終于推開了它,流浪多年的心靈終于找到了回家的路。《空巢》中的田田與秦陽在與世隔絕的黑暗逼仄的空間里完成了生死的情感考量,愛情與利益的分界線就變得不那么分明,“人行過了死蔭的幽谷,仿佛只是為了成全一段艱難的姻緣”。黑暗的電梯就如同一個“幽谷”,成為愛情的空間隱喻,將一切世俗的利益摒棄,剩下的只有生命和愛。
《云中記》中村民們對山神、苯教的信仰,都凝聚為那一座晶瑩的雪山,而阿巴在隨著滑坡體一起下墜的時候,他感受到的是“飛翔”,他和他的法器、馬、干涸的泉眼與水渠、死去的老柏樹、寄魂樹、荒蕪的園子和廢墟都融為了一體,一起沉入深淵,這些意象作為象征,是他心靈的寄托,是他作為祭師最后的家園。在這個身體下墜、靈魂升騰的那一刻,祭師的情感世界也升華為一種悲憫而崇高的英雄情懷。如同《花冠病毒》篇末于增風最后的字跡:“我。病毒。星辰。海水。恐龍。共棲。久遠。無敵。龐大。渺小。……”對病毒的思考與宇宙、人類、歷史融為一體。創傷敘事觀照人的心靈、想象與現實、災難的關系,思考人類的命運和自然界的關系,反思個體生命的價值,它是對災難的文學想象,這種強烈的情感表達最終凝聚為深刻的象征和隱喻,從而成為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的原型。
五、結語
災難文學是作家悲憫情懷的展現,“疼痛”是創傷敘事的原點和動力,我們乘坐著創傷記憶的火車駛向人性美好、自我修復、溫情互助的未來,在旅程中反思、審查、直面內心的勇敢與怯弱。在災難小說中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英雄或平民,男人或女人,都必須作為普通人來抒寫他們面對災難、抗爭災難、治愈創傷的復雜情感歷程,在情感表達中展現人性的深邃莫測。創傷敘事的情感具有特殊的歷史價值、文學價值、美學價值。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災難文學記錄和表現了人類抗擊災難的心靈歷程,它凝鑄和磨礪了承受災難的人們修復創傷情感的能力,呈現了家庭、民族集體記憶傳遞、接受、認知生命意義的過程。災難文學表達了深刻、悲愴、純凈和崇高的悲劇情感,塑造了具有悲劇美學價值的文學意象,審視創傷敘事的情感表達和情感特征,可以闡釋不同災難圖像的重復變化與身體經驗的整體比照,以此把握小說的情感邏輯和象征體系。
【注釋】
①②畢淑敏:《花冠病毒》,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第119、120頁。
③王欣:《創傷記憶的敘事判斷、情感特征和敘述類型》,《符號與傳媒》2020年第2期。
④⑥14阿來:《云中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第102、297、7頁。
⑤⑧李曼曼:《20世紀美國少數族裔小說創傷敘事研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7,第26、25頁。
⑦王欣:《創傷、記憶和歷史:美國南方創傷小說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13,第42頁。
⑨于守洋等主編:《現代預防醫學辭典》,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第330頁。
⑩12張翎:《余震》,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第3、4頁。
11王金勝:《一個人的總體性文學想象——論阿來〈云中記〉》,《南方文壇》2020年第3期。
13孔瑞:《“后9·11”小說的創傷研究》,北京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第67頁。
(高明月,長沙師范學院文學院、湖南大學與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聯合培養在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