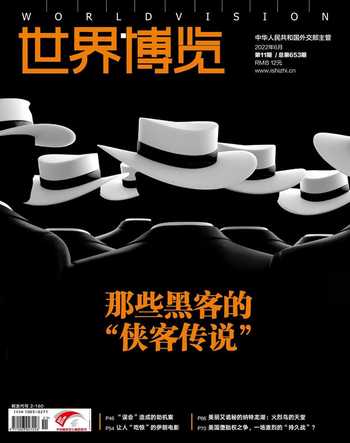疫情下的“鄰里效應”
悠悠我心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英國多塞特郡,一名歌劇演員在家門口為鄰居演唱。
看過韓劇《請回答1988》的人都會感到被治愈,劇中鄰里關系的煙火氣令人羨慕。這也代表了我們曾經的時代——在過去長久的歲月中,人際、鄰里間的相處簡單真摯,在我的記憶中,鄰居間端著盛滿飯菜的碗邊吃邊串門的畫面比比皆是。但如今,你知道左鄰右舍的名字嗎?在生活節奏日益加快、“信任危機”四處販賣的當下,防盜門、電子監控、門禁卡,我們就像套中人,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生怕暴露一點真實。淳樸的鄰里情,成了鋼筋水泥叢林里的稀缺品。
是因為鄰里關系變得不重要了嗎?在我們一度這么懷疑時,這幾年鄰里關系突然火速升溫,開始了一場“破冰之旅”。受疫情影響,不少城市經歷過不止一次的封控管理。當封閉在家,我們會不得已退縮成一座座“孤島”。好在患難見真情,小區里團菜有團長,送菜上門有志愿者,各種瑣事有居委會,柴米油鹽互通有無。很多人通過業主群、互助群正式見面、互相幫助,邁出了社區身份認同的第一步。原來“點頭之交”“咫尺難辨”的鄰居變得熟絡起來,守望相助、共同抗疫。在經歷了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疫”之后,鄰里之間又多了一種奇妙的連接,每一座“孤島”之間的互動,構成了一道道新的風景線,讓“鄰里效應”在疫情下有了新的體現。
“鄰里”不單指鄰居之間,而是廣義的社交關系,指占據一定空間區域,形成一個具有共同感情、傳統和歷史的地區,受到一系列生態、文化和政治力量影響的人和機構,構成社會和政治組織的基礎。鄰里效應,指地方社會環境的特點可以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方式。
桑普森在《偉大的美國城市:芝加哥與持續的鄰里效應》中列舉了犯罪、貧困、兒童健康、社會抗議、公民參與、房屋止贖、利他行為、未成年產子、流動性、社區效能和移民等文化現象,認為人們居住的地方決定性地影響了人們的生活。
關于鄰里效應,社會心理學家也有過一系列實驗研究。美國社會學家巴薩德在上世紀20年代研究了費城的5000份結婚申請書,發現三分之一的夫婦婚前住在5個街區之內的范圍中。而后,3位社會心理學家對麻省理工學院17棟已婚學生的住宅樓進行了調查。統計結果表明,居住距離越近的人,交往次數越多,關系越親密。另有一名社會心理學家在警察專科學校也做了研究,他把學生們的名字按字母順序排列起來,然后再按這個順序安排教室座位和宿舍房間。6個月后,要求學生說出3個最親近伙伴的名字,結果,學生們的朋友都是在名字字母順序上和自己相近的人,確切的數據是平均相差四五個字母。
好鄰居值千金,咱們古人早就深諳此道。孟母三遷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而在《南史》上也記載了這么個故事:有個叫宋季雅的人,為了有個好鄰居,情愿出十分昂貴的房價買下一幢房子。有人說太貴,宋先生卻說:“不貴,這100萬元買屋,另外1000萬元是買鄰的。”宋先生認為,有了好鄰里,等于為自己增添了左膀右臂。
每個人都不是孤島,都與身邊圈子有著或深或淺的關系。人們普遍存在一種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的期望,努力和鄰近者友好相處,避免出現不愉快。同時,人們在互動過程中,都會力圖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回報。這些都為“鄰里效應”的產生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鄰里效應”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甚至人生走向。
疫情期間,一個小伙子從蘇州搬家到上海,第一天進入業主群后就被強勢“圍觀”,大家紛紛驚嘆他是“華夏第一勇士”“勇得離譜”。但玩笑歸玩笑,左鄰右舍特別熱心,在群里進行各種指導解答,幫助他盡快融入新圈子。
在大家的一貫印象里,業主群平時基本是“我忙著呢,別煩我”的狀態,日常遇見最多點點頭,彼此之間不聊天、不打聽、不八卦。但如今局勢發生了變化,暖心的故事每天都在全國各地上演,雙向的守護,成為疫情下鄰里情最自然的流露。
在山西太原,連吃了兩天泡面和面包后,司女士在社區群忍不住“吐槽”:“明天蒸包子吃吧。”鄰居們馬上在群里回應。一上午時間,鄰居們就蒸了100多個包子,免費送給有需要的人們。網友紛紛點贊:“這樣的好鄰居,請給我來一打。”
在上海,裝修工人劉師傅因為疫情滯留小區半個月,居民們接連送來食物、被褥、洗漱用品……隨后,他當上了小區臨時“配送員”,他說:“大家幫助我,我也要給小區作貢獻。”
上海的高小姐對門住著一位九旬阿婆,小區封控后,高小姐擔心阿婆的生活,在阿婆門口貼了一張紙條詢問她的需求,沒想到阿婆在紙條上回復說:“我們物資充足門口掛著蔬菜,你隨意取用。”
不少人曾熱衷于詩與遠方,忽略了身邊的鄰里關系;曾熱衷于個人自立,淡化了相互幫扶;曾彼此心存戒備,笑問“鄰”從何處來。但在抗疫過程中,一度消失的鄰里關系又回來了,志愿輪流值班,搬運食品物資,照顧老人孩子,共享疫情信息,贈送抗疫物品。這種特殊時期的鄰里關系讓一棟棟居民樓成為抗擊疫情的一座座堅固堡壘。
武斷、冷漠、自私,遠比病毒本身更可怕。保護世界的不一定是超人,也可能就是你身邊的人。而疫情下的“鄰里效應”新面貌,也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發。聽過一句冷笑話:出來“混”,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出來”。
要想有好的“鄰里效應”,首先要“走入”,這就需要我們“打開”自己。有個有趣的寓言故事:一只小狗走進宮殿,宮殿有1000面鏡子。它一走進就看到鏡子里有一只狗很兇,而1000面鏡子里有1000只狗都在對它面露兇相。于是它馬上對著鏡子里的小狗狂吼,結果1000面鏡子里的小狗都對著它狂吼。當它發現四周的狗都這么兇,它更加不甘示弱,最后它累得精疲力盡,發不出一點聲音。這時,所有的吼叫聲都停止了,小狗很好奇,慢慢爬起來,看著這“1000只”小狗,它也不再吼叫了,沖它們笑了,于是所有的小狗都對它笑了。
這就叫“如是因,如是果”。其實世界就是我們心境的反映,鄰里也是我們自己的折射。越是留意自己的聲音,才能聽到別人的聲音。如果我們以惡對人,就像鏡子回照一樣,身邊必然也是以惡回應。反之,我們若能與自己和解,以溫和積極示人,也能收獲良好的鄰里效應。
網上流傳著一個帖子:囤了足夠多可樂的上海業主孫先生,在小區微信群里宣布,自己在樓下架子上放了一箱可樂,已用酒精擦拭過,想喝的鄰居可以去自取。很快,有鄰居用辣椒醬換走一聽可樂,隨后有人用一瓶牛奶換了可樂。漸漸左鄰右舍都來了,架子上的東西越來越多,啤酒、方便面、咖啡、汽水……大家都拿出自家富余的物品換到食品柜上。孫先生說,當時看到有鄰居想喝可樂,就搬了一箱下去,沒想到一場無償的可樂分享最終演變成了暖心的鄰里換物。
這些舉動讓我想起《請回答1988》中鄰里之間互換美食的搞笑畫面:晚飯前,家里孩子端著菜去鄰居家“換菜”,這家一盤沙拉換了一碗米飯和一些蘿卜泡菜,那家一盤青椒牛肉換到一籃橘子,另一家一盤青菜換來一盤海苔。于是大家的餐桌上,很快從冷清的一兩個菜變成一桌豐盛大餐。以物易物就像縫隙里照進來的光,讓我們看到抱團取暖、守望相助的力量。
除了物品的互換互補、想他人所想,在人格尊嚴的對待上,我們更應該做到尊重,重他人所重。一個女孩在一家肉類加工廠上班,因下班前在冷庫例行檢查,門意外關上,她被反鎖在冷庫,大聲呼救卻無人聽見。正當她在瀕死邊緣,工廠保安奇跡般打開冷庫門,救出了她。她問保安:“你為什么會來開門,這不是你的日常工作啊?”保安解釋道:“我在這里工作了35年,每天幾百名工人進出,你是唯一一個每天早晨上班向我問好、晚上下班跟我道別的人。今天你像往常一樣來上班,和我說‘你好’,但下班后,卻沒聽到你跟我說‘明天見’。沒聽到你的告別,我隱約感到可能發生了一些事。”這是幾年前的一個真實報道。女孩給了保安尊重,保安給了她第二次生命。

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么,但當我們用愛去面對世界,世界會反過來用愛來擁抱我們。有句話說得特別好:“以金相交,金耗則忘; 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敗則傾;以權相交,權失則棄;以情相交,情斷則傷;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遠。”合伙做事也好,人際交往也好,我們都應以誠相待,以心相交,這樣就能必得善果。
叔本華講過一個寓言故事:一群豪豬因為寒冷群暖,越靠越近。可是身上的刺毛卻在互相攻擊,讓它們痛得難受,只好各自跑開。天氣越來越冷,它們又靠在一起想要互相取暖,不一會兒又嗷嗷叫跳著離開。如此循環往復,最后才找到一個不遠不近的距離,相處既溫暖又沒有刺痛感——它們找到了適當的距離。
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們的交往頻率與喜歡程度的關系呈倒U型曲線。也就是說,過低與過高的交往頻率都不會使彼此的喜歡程度提高,唯有中等交往頻率時,彼此關系提升速度最高。我們在日常中與周邊相處要把握好度,既要古道熱腸,又要親密“有”間,才能讓“鄰里效應”走入“可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
很多人說:經過這次疫情,要去多買幾個冰箱冰柜,以備不時之需;也有人感慨:遠親都是浮云,近鄰才是剛需。其實,我們不僅需要冰箱的冷藏儲備,更需要“鄰里效應”的溫暖輻射。西方有句諺語:“養育孩子需要一個村莊。”這折射了“鄰里效應”的真諦——我們的人生需要溫馨有愛的生態圈。不管你見或不見,理或不理,“鄰里效應”就在那里,不聲不響,不離不棄。
(責編:南名俊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