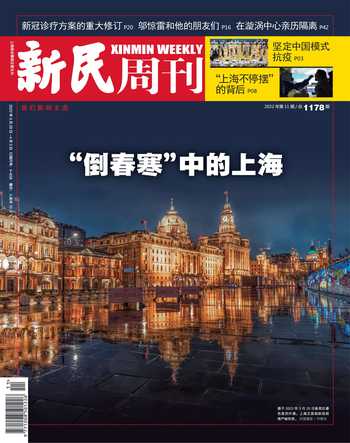沒搪過爐子的人,不足以在胡同里談人生
白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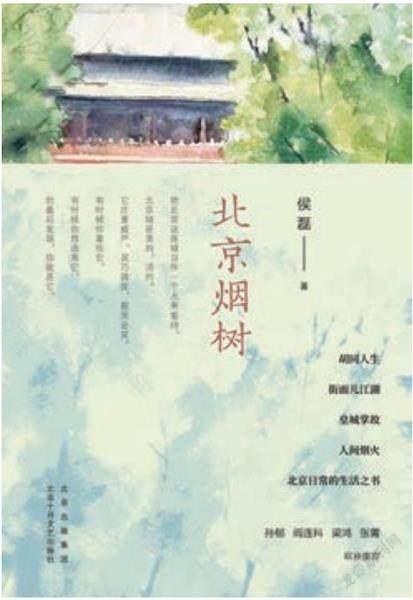
讀《北京煙樹》,讓我想到三百多年前明人的《帝京景物略》,寫燕京名勝,紅塵白日,芳林隱榭,綠水平橋,歌聲如潮;又讓我想到二百多年前清人的《帝京歲時紀勝》,寫舊都年節,尤其是吃食,江米白酒,冰盞桂花,爆竹之聲,相為上下;還讓我想到近百年前鶴見佑輔《北京的魅力》,這篇經由魯迅先生翻譯的文字里寫道:“在北京的街上走著的時候,我們就完全從時間的觀念脫離。這并非僅僅是能否趕上七點半鐘夜飯的前約的程度;乃是我們從二十世紀的現代脫離了。眼前目睹著悠久的人文發達的舊跡,生息于六千年的文化的消長中,一面就醒過來,覺得這是人生。”將這些文獻連綴起來,千年也好,百年也好,層疊于時光中的北京,具有永恒性。侯磊筆下的北京,向上,汲取了這種層疊的光芒;往下,有著幾代人共同生活的底色,是滲透在骨子里的,他寫中軸線上宮殿的宏大敘事,也寫胡同生活,從買貨泡澡到取暖搪爐子,把人間世寫得熱氣沸翻,回腸蕩氣。他在《胡同生靈》里說:“一座古城除了有文獻、文物的層面,也更有‘靈’的一面。我們生活的院子里,街巷里,一棵古樹,一座老屋,哪怕只是一塊雕鏤裝飾,顏色趨于牙黃的古磚,他們都注視過你的祖父、父親還有你本人。”一座城市,它所承載的不只是厚重的歷史,還有與人之間的回響。在這座城市生活,同時也意味著與這座城市的傳說一起生活。我們不應輕率地否認超出我們認識和理解范圍的事,而應懷著開放的心態,接受更多可能,與萬物萬靈共存。如作者所言,“胡同里的人有樸素的護生思想,這談不上什么平等博愛,而是發自內心的善良。……地球上的水,食物和空氣一樣,本應大家共享,不應有任何生物因凍餓而死,這是地球運行的基本法則,否則便是逆天。我對它管吃管住,它只是我生命的同行者。”
侯磊《北京煙樹》中寫,北京是理想之城,精神故鄉。這座無數人共同生活的城市,最終的落腳點,不過是“吾心安處是故鄉”。當然,北京不只是各類精英和文青的北京,更是普通人的北京,混街面的、擺地攤的、買舊書的,各類游走于灰色地帶乃至于顏色不清楚的人物,都有著各自的傳奇與辛酸,在侯磊的筆下,有褒貶,但詩意可見。他寫工薪階層的父母年輕時戀愛,父母各騎一輛自行車約會,母親穿著大花長裙,燙著波浪頭,腳蹬白色小皮鞋,結果卻在等紅燈的當兒與父親走散了。父親找半天沒找著,想著都二級車工了,還能找不著家嗎?母親當然是回去了,不過是抹著眼淚回去的。母親第一次去找父親,父親正在一個大鋁盆里洗衣服,搓的搓板上都是黑泥湯子。母親便想“這人挺能干活。”然后就嫁給了他。這一段寫得特別動人,足以和所有偉大的文學作品里的細節媲美。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書寫既是記憶,也是發現。
他在《懷念半條胡同》中寫:“個人記憶有時并不很牢靠。如一陣風,足以使得上百年的歷史消逝。我抬頭望見那林立的高樓,眼前浮現出胡同的幻影。”人的記憶,一定是在當下生活之上的疊影。對于書寫者而言,更是將觸須深入到了文化血液中,而這已超過了自身的體驗,有了更高的維度。他寫北新橋的變遷,從劉伯溫和孽龍的故事說起,貝勒王府、商行煙館、簪纓世家,幾條街,幾個人,演繹成一篇傳奇,如同舊時說書人,故事講完了,搬個小馬扎各自回家。“夕陽下山,人影散亂,我已忘記夕陽從胡同中走過。”
作者聚焦并追蹤北宋時期,詞如何從宴飲助興的表演文本——歌詞,歷經創作、傳唱、抄寫、結集諸過程,最終衍變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并逐漸取得與詩歌并舉的正統地位。
宇文所安一方面從表演實踐、文本傳播、作者問題、詞集編纂與流變等全新角度將詞史看成“詞集史”而非“詞人史”;另一方面又對代表性詞人如柳永、晏幾道、蘇軾、秦觀、賀鑄、周邦彥、李清照等人的作品進行文本解讀,分析他們各自不同的風格特征及相互之間的關聯與影響,力圖從多個層面呈現詞的歷時性發展及其作者化、風格化和經典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