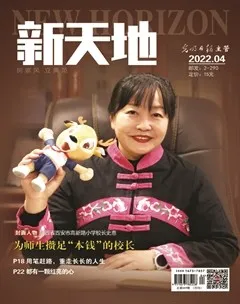難忘家鄉山歌小戲
王散木


今年春節期間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舊朋老友,親情聚會,久違的鄉音,兒時的記憶,故土的風習,還有家鄉的五句山歌和人人都能哼幾句的地燈嗨子戲,都又鮮活地呈現在眼前、回響在耳畔。
五句山歌是豫南民歌中的典型代表,內容多為情歌。語言通俗,敘述簡練,風趣俏皮。年近八旬的二哥,抓住我的手激動得老淚縱橫:“老九啊,要常回來!哥老了,牙豁了,口齒還清楚,知道你喜歡家鄉的這些玩意兒,哥給你唱幾段,保證還是那樣有滋有味——”
芝麻多了要流油/
山歌多了擠破喉/
三餐俺用歌拌飯/
睡覺俺用歌枕頭/
干活俺用歌加油。
(眾和:干活俺用歌加油。以下各段末句均為眾和)
日頭出來往東游/
隔河看見秧吃牛/
小雞摟著黃狼子睡/
干魚倒給貓枕頭/
反唱四句解憂愁。
高高山上一塊田/
郎半邊來妹半邊/
郎的半邊種甘蔗/
妹的半邊種黃連/
半邊苦來半邊甜。
大河漲水小河渾/
打漁船兒往上撐/
打不到魚兒不收網/
攆不到乖姐不收心/
攪得黃河水不清。
姐在房中繡香袋/
屋上吊下蜘蛛來/
茶哥派它來牽絲/
根根情絲吐出懷/
魂魄來了人沒來。
小時候,我們家鄉很窮。家家都缺吃少穿,生活窘迫,精神文化生活更不用說了。然而,就是在這種境況下,窮人也有窮人的樂呵。給我留下最深刻記憶的是叔叔大爺們在農閑和冬季里,自發合伙玩地燈、演嗨子戲。
嗨子戲是固始縣一個具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地方民間戲種。嗨子戲(亦稱“花籃戲”“燈戲”“地撲籠子戲”“咳子戲”),嗨子戲因在每句起腔前先“嗨”或“咳嘛”后再唱,唱句間也用“咳”作虛詞甩腔而得名。是由當地燈歌演變發展而成的民間戲曲,源于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結合地——河南省固始縣,流行于固始及其周圍的淮濱、商城、潢川、息縣、光山以及安徽省沿淮地區的阜南、阜陽、霍邱、壽縣、潁上和六安、金寨、鳳臺、懷遠縣等部分地區。嗨子戲為鄉土小戲,沒有科班和專業劇團。由于該戲服裝道具簡單,只需要兩只精致的花籃一挑就能趕集串鄉流動演出,因而群眾叫它“花籃戲”,鑒于它的演出活動多和“地燈”相結合,一般規律是白天和傍晚玩“花會”(玩燈),晚上下地場(指演嗨子戲),因此當地群眾又有叫“燈戲”的。由于嗨子戲生活氣息濃郁,表演形式活潑,唱腔音樂樸實優美,加之唱、白均為鄉土語言,更加具有濃厚的大別山地區特色,因而為群眾所喜愛。其行當分生、旦、凈、丑。唱腔板式分4種:一是苦嗨子,常用于敘事抒情;二是喜嗨子,用于表現歡快的情緒;三是平嗨子,多用于陳述性的唱段;四是花嗨子,也叫曲牌或雜調,多反映民間風俗。演出有正本戲和雜調3類。嗨子戲音樂體系由唱腔和打擊樂兩部分組成。唱腔以板腔為主,曲牌為輔,幫腔合聲,打擊樂間奏,唱、幫、打三位一體。嗨子戲的曲牌音樂亦叫雜調,是直接采用民歌舞《地燈》的音樂,共30余種,常用的有鳳陽調、彩調、打長工、開門調等。樂隊由3人或5人組成。鑼鼓四五件,還有配以笛簫的。記得小時候常聽的曲目有《大鈀缸》《三打桃花》《王三姐坐寒窯》等。我大叔王殿忠人高馬大,挑著一副大籮筐,亮開大嗓門唱起《游鄉》《大鈀缸》來,能把十里八村的大姑娘小媳婦吸引得忘記回家做飯洗衣服;二叔趙錫恩、三哥王國喜,花旦扮相那個俊啊,真是千嬌百媚,脆生生、綿柔柔的花腔一出喉,所有聽戲的男女老少都如癡如醉。記得二叔、三哥聯袂出演《三打桃花》,二叔演惡二娘,三哥演受氣的桃花,二人合作默契,活靈活現,戲里人物全讓他們演活了,所有聽燈的人都被他們帶到了劇情里……至今,“王大娘,來鈀缸”“鈀破舊缸賠你新缸”“咿呀吭呀咿吭,呀吭呀吭咿呀吭……”都還時常在耳畔回響。
(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主題歌《好漢歌》的旋律就是根據《大鈀缸》的曲調改編的,其曲調最早流行于河南、山東、安徽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