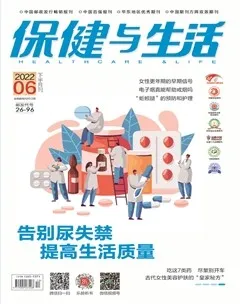古之“碧筒飲” 消夏亦陶情
李金鋼
盛夏時節,荷張翠蓋,蓮豎紅幢,清香溢遠,沁人心脾。文人雅士臨風賞荷,快意消夏,飲酒賦詩,寄情明志,乃為時令雅事。
天長日久,人們觸景生情,借物逞巧,賞荷消夏便演繹出了新花樣:以新鮮荷葉為器具飲酒解暑。據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載:曹魏時期,濟南歷城北有一處名為“使君林”的精美園林。魏正始年間,齊州刺史鄭愨每每于三伏之際,率賓僚來此游賞避暑。“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吸之,名為‘碧筒杯’。”此項盛事得到了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稱謂——“碧筒飲”。
以荷葉做器具飲酒,別有韻致,堪稱技為美、情至上。那一刻,酒順荷葉、荷梗緩緩而下,或多或少地帶著荷的藥效與清香。荷液、酒液混為一體抵達舌尖,口感特別,清涼怡人。一如宋代詩人蘇軾所言:“碧筒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元代陸文圭寫了數首詩詞對此倍加贊賞:“綠盤擎重盛珠露,碧管虛中溜玉漿。象鼻卷風隨手曲,良臍入水透肌香。”“聞得鼻端香馥馥,流從舌底味森森。”“尤勝朱櫻煎作蜜,何須紫蔗壓為漿。”
中醫認為,夏氣與心氣相通。夏宜食苦,苦養心。《本草備要》載:“苦者能瀉燥火。”荷葉,味甘、苦,性平,歸心、肝經,有清暑利濕、健脾升陽之效。荷梗能清熱解暑、生津止渴。酒,為糯米或黍米、酒曲所釀之發酵物,可開胃提神。荷之苦,于養生保健有所裨益。此外,酒透荷香,荷酒共飲,也會起到沉靜祛燥的作用。神定氣閑,心靜自然涼。
盛酒的荷葉,亦稱“碧筒杯”“荷葉杯”“象鼻杯”“荷盞”等。后人根據“碧筒杯”的原理和形制,創制了金、銀、玉等不同材質的荷葉吸杯。清代乾隆年間,“犀角碧筒杯”面世,珍貴且具保健作用。20世紀70年代初,我國考古人員在陜西西安何家村出土了唐代文物“鎏金銀荷葉吸杯”,轟動一時。元代陸文圭對“碧筒杯”的首創者、功能、寓意及其后世的仿制作了概括性描述:“樽疊自古宴嘉賓,末世風流意轉新。筒葉卷來由鄭氏,杯荷制出始唐人。一時花草空傅玩,他日寶僚但飲醇。外直中通比君子,輪他光霽滿懷春。”
“碧筒飲”傳為佳話,并成為古人避暑消夏的“保留節目”承襲下來。
唐代戴書倫詩云:“茶烹松火紅,酒吸荷杯綠。”白居易詩贊:“石榴枝上花千朵,荷葉杯中酒十分。”曹鄴詩曰:“乘興挈一壺,折荷以為盞。”趙麟《因話錄》載:“牟少師與賓僚飲宴,暑日臨水,以荷為杯,滿酌,密系,持近人口,以筋刺之,不盡則重飲。”
宋代民間盛行“碧筒飲”。人們賞荷、納涼、飲荷葉酒,直至皓月當空才泛舟而歸。清代趙翼再現了當時的情景:“帶得余香晚歸去,月明更醉碧筒杯。”宋代蘇軾曰:“唐人以荷葉為酒杯,謂之碧筒酒。”據說,蘇軾被貶海南儋州期間常飲“碧筒酒”消夏。明代高啟《碧筒飲》云:“綠觴卷高葉,醉吸清香度。酒瀉正何如,風傾曉盤露。”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被人們視為高尚品德之化身。賞荷,來一杯“碧筒飲”,不啻是一項消夏盛事,也成為一種精神寄托和審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