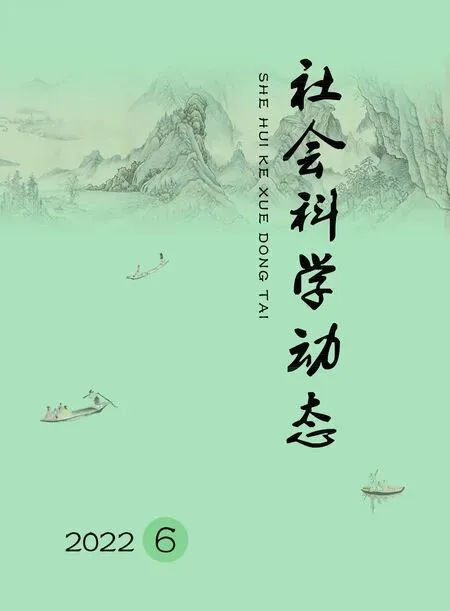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及其應用
鐘玉婷 鐘 堅
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與廣泛應用,使人工智能迅速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最具通用性和滲透性的新型技術,不僅產業融合度高,而且能夠有效提高產業效率,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世界各國紛紛加快制定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出臺相關支持政策,以捕捉新一輪技術革命與產業變革的機遇。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國政府將人工智能發展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2015 年5 月,黨中央、國務院著眼全球視野和戰略布局,立足我國國情和發展階段作出了實施《中國制造2025》 的戰略決策。 《中國制造2025》明確提出,加快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技術融合發展,把智能制造作為兩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著力發展智能裝備和智能產品,推進生產過程智能化,培育新型生產方式,全面提升企業研發、生產、管理和服務的智能化水平。2017 年7月,國務院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明確提出到2030 年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的發展目標。2020 年11 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O 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領域,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為了貫徹實施上述文件精神,各地政府也不斷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積極布局人工智能產業,建設人工智能產業園區;各高校不斷新設相關學科專業,足見我國各地對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視。
然而,就整個行業而言,全球范圍內人工智能技術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在此背景下,客觀判斷我國人工智能的發展水平,有利于準確把握我國人工智能行業在國際市場的實際競爭能力,有利于推動人工智能行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的設計與研究,無論是對相關政府部門還是學術界而言,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 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基于數字技術的機器學習不斷突破推動了人工智能產業快速發展,人工智能設備通過機器學習完成了大量人類難以企及的工作任務。當前,中國人工智能領域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主動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發展情況、發展水平及發展方向,對中國戰略層面的研發布局至關重要。而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和決策者的重視也使得人工智能成為新的研究熱點,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圍繞這一主題開展了研究。曹靜等通過分析人工智能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人工智能發展提升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但也加劇失業①,類似觀點還存在于陳楠、蔡躍洲的研究成果中②。陳彥斌等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對人工智能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展開討論,認為衡量人工智能發展水平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使用已經實現自動化的生產任務占所有生產任務的比重反映人工智能發展程度③,郭凱明、程承坪、王瑞瑜等的研究成果支持類似觀點④;二是假設人工智能發展使生產函數中出現了與普通資本不同的智能資本,然后通過智能資本及其變化來刻畫人工智能的發展程度,如陳利鋒、黃旭與董志強、程惠芳等的研究成果⑤。
一些專業機構和學者則聚焦于人工智能發展測度問題從不同視角展開研究。烏鎮智庫發布的《全球人工智能發展報告》,自2016 年起連續多年從產業、技術、應用場景3 個維度匯總人工智能發展數據;2018 年,清華大學中國科技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18》,從科技產出與人才投入、產業發展與市場應用、發展戰略與政策環境、社會認知與綜合影響等4 個維度對國內人工智能發展水平進行測度;2019 年,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指數》,從基礎支撐、創新能力、融合應用、產業運行、環境保障5 個維度對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情況進行綜合評價。相比之下,學者們的研究則更加細化與學術化。李旭輝等嘗試構建人工智能產業自主創新能力測度指標體系,運用縱橫向拉開檔次法、非線性規劃法對人工智能產業自主創新能力進行測度⑥;呂榮杰與郝力曉通過熵權法,從制度環境、基礎設施、技術創新與生產應用4 個維度測度2003—2018年中國省際人工智能發展指數⑦;顧國達與馬文景則構建了以環境力、知識創造力、產業競爭力為主的人工智能綜合發展指數體系,運用組合賦權法和時序加權平均算子對2010—2018 年中國、美國、歐盟、日本、韓國、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的人工智能發展水平進行量化評估⑧。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發現,現有研究成果更多采用較為單一或相對簡單的指標對人工智能發展水平進行替代研究,也有學者針對相關問題嘗試構建測度指標體系。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學術界對人工智能發展水平的測度,尚未構建相對科學的指標體系,導致人工智能發展的相關研究缺少量化分析基礎。由于人工智能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統計數據稀缺,更是加大了評估難度,適用于該領域發展水平測度的指標體系仍有待于進一步歸納與提煉。
為了更好地對相關學術問題進行深化與探索,本文圍繞人工智能發展的表征與影響展開分析,著重考察以下問題:第一,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的對象是什么?第二,測度指標體系設計思路是什么?哪些指標更適合衡量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狀況?第三,指標體系整體適用性怎么樣?具體來看,首先考察的是人工智能概念內涵與外延的界定,回答了何謂人工智能;其次,結合人工智能以無形資產為主的基本特征,本文重點關注其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的構建;最后,本文分析了指標體系的數據獲取、權重測算等應用問題。
二、 測度對象的界定
人工智能作為技術進步的一種具體形式,指“賦予計算機系統具備正常執行需要人類智慧的任務的能力”,是基于電子信息技術的自動化設備,與生物智能相對應;而斯圖爾特·羅素等認為,人工智能是擁有類人類行為、類人類思考、理性的思考和理性的行為的人造工具⑨,其發展大致經歷了孕育、誕生、早期熱情與現實困難等孵化階段。當前人工智能發展還處于早期階段,盡管研究人工智能的相關文獻逐漸增多,但當前研究多以人工智能的應用、影響以及發展趨勢為主,鮮少關注到人工智能發展水平的測度問題。此外,人工智能多以無形資產為主。以阿爾法狗為例,人工智能不再簡單呈現為自動化機器設備,而是基于算法和數據且具有學習能力的智能數據處理系統,無形中加大了對人工智能資產價值進行衡量的難度。實質上,對某一領域發展水平測度的研究,明確測度對象需要用哪些指標來衡量其發展水平尤為重要。
基于此,本文將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明確測度人工智能發展水平的對象和相關衡量指標,以期能夠科學全面地對我國人工智能發展水平進行測度。
(一) 宏觀測度對象
鑒于人工智能發展離不開科技發展環境支持和社會包容,因此選擇測度對象的首要考量是人工智能發展的宏觀環境,具體細分為政策環境、經濟環境與創新環境。
一是政策環境對人工智能發展的支撐。政策環境作為支持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外部環境,其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人工智能的發展狀態,尤其是各級政府出臺的政策對技術進步或新興產業發展存在較強影響的情況下,如何科學、合理地評估政策環境,對衡量人工智能發展水平尤為重要。首先,在政策環境評估的具體政策選擇方面,應包括方向引導、融資扶持、稅收優惠及業務支持等相關主題;其次,在政策內容評估方面,應聚焦于相關支持政策數量、金融扶持政策數量以及人工智能專項資金扶持。無須諱言,政策環境評估結果也反映出政府部門對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視程度。
二是經濟環境對人工智能發展的適配。一方面,由于技術進步最終呈現在軟件(網絡) 服務或硬件設備上,因而人工智能發展離不開信息技術產業發展,同樣也離不開相關硬件產業發展,脫離產業基礎空談人工智能發展顯然是不現實的;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發展離不開經濟能力與經濟結構的支撐,區域經濟總量尤其是二、三產業總量對人工智能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因此,測度人工智能發展水平必然需要考察信息技術產業發展、區域經濟總量及二、三產業發展水平,且經濟環境作為承接人工智能外部發展的重要基礎,對其進行評估亦有著重要現實意義。
三是創新環境對人工智能發展的孵化。創新環境是創新系統的內部基礎條件,支撐著人工智能創新系統內各主體的良性運轉,不僅是效率改善和能力提升的關鍵,而且技術創新也離不開創新環境的孵化。因此,在不考慮科技創新輸入的情況下,區域科技創新活力和自主創新能力不僅是技術創新的基礎,也是服務于科技創新活動和促進科技進步的重要保障。相關技術孵化平臺或產業園區作為技術創新的繁育土壤,既是創新能力的重要體現,又是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資源。因此,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考察的一個重點應為區域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孵化平臺數量及人工智能產業園區數量。
(二) 微觀測度對象
微觀層面的考察側重于社會主體的投入產出情況,具體細分為微觀主體、創新成果與成果應用。
一是微觀主體積極性。微觀主體是人工智能技術創新的載體與實踐者,同時也是人工智能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支撐,具有整合科技資源、開放共享、支撐和服務科技研發活動的功能,其主體包括與人工智能產業相關的企業、研發機構及相關高校等。另外,微觀主體對技術創新的參與積極性,將直接推動區域人工智能發展水平的提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也是創新活動中最為活躍、最為積極的因素⑩。顯然,高素質的科研人才數量也是衡量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相關測度的重點應為研發人員數量、人工智能企業數量、研發機構數量、高校相關一流學科數量、研發經費投入及固定資產投入等。
二是創新產出能力。主要體現在創新成果和創新效益兩個方面,創新成果是指由于實施創新活動而產生有形或無形的成果,既是科學技術進步的最終結果,又是驅動過程的開端資源1?,其成果數量還是創新產出力的表征。創新效益作為衡量創新驅動發展過程中創新產出能力的關鍵因素,既是評價創新產出能力的量化標準,還能為人工智能產業進行再創新提供技術與資金支持。從最終表現看,創新成果和創新效益都是影響創新產出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考察人工智能發展水平的核心是對創新成果數量和創新效益的衡量。根據對當前人工智能發展水平的分析可知,人工智能產出具體表現為技術發明、研究突破及行業產出,因此,相關測度重點應為發明專利數、研究論文數量、相關會議/論壇數、相關產業產值等。
三是成果應用貢獻度。科技創新最終要應用于社會經濟實踐,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創新,才是科技成果社會價值的有效呈現。當前,人工智能發展成果應用主要表現為消費場景、生產場景與軍事場景三個方面的應用,其中,消費場景應用指消費類智能電子設備或軟件的使用,如學習機器人、掃地機器人、智能化翻譯軟件等;生產場景應用指生產自動化設備或軟件的使用,如智能化管理系統、自動化生產線、自動生產輔助設備等;軍事場景應用指軍用智能化裝備的使用,如軍用機器人、軍用無人機及其他智能輔助設備等。因此,相關測度重點為發明專利轉讓、消費類智能化設備或軟件企業銷售、自動化設備或軟件生產企業銷售、智能化軍用設備銷售等。
三、 指標體系設計
基于上述分析,利用單一指標對人工智能發展水平進行變量替代的做法,已經對該領域學術研究形成制約。因此,本文在明確宏觀考察對象與微觀考察對象的基礎上,梳理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的構建思路與秉持原則,進而對測度指標體系進行設計。
(一) 指標體系設計思路
結合前文對測度對象的界定,借鑒李旭輝等的研究中關于指標體系構建的思路?,按照事物發展“事前—事中—事后”的邏輯順序,提煉我國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設計的基本思路。初步擬定指標體系的整體框架為“三層四維”,具體而言,縱向分為一、二、三級指標,由三級基礎指標向上逐層支撐;橫向則將我國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歸納為創新支撐、技術成果、成果應用、創新實踐四個維度。
一是創新支撐,指直接或間接參與到創新活動過程中的因素,既是人工智能技術創新的軟硬件基礎,又是維系和促進創新活動開展的保障與基礎。因此,創新支撐維度更側重衡量人工智能創新的趨勢及持續性能力,測評指標設計則應考慮對政策環境、經濟環境及創新環境的承接。測度內容可歸納為政策環境、產業基礎與創新環境等三個二級指標。
二是技術成果,指人工智能技術創新成果輸出,由于技術轉化形式包括直接和間接兩種,考慮到間接技術轉化的衡量難度較高,因而此處特指直接技術成果。之所以將直接技術成果納入到測度指標體系,就在于創新技術輸出的直接成果不僅是創新技術的物化顯示,也是作為引領創新驅動發展的主要載體,代表先進技術的發展方向。因此,技術成果維度應側重測度人工智能創新的直接研究成果,測評指標設計要考慮相關企業、科研機構及高校的發明專利與科研論文輸出。測度內容可歸納為技術發明與科研論文兩個二級指標。
三是成果應用,指人工智能技術成果的社會價值。由于知識創造與技術創新最終要服務于社會實踐,由社會實踐統一實現其社會價值。因而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工智能發展水平進行測度,不僅要考慮人工智能發展所依托的創新環境、創新質量,還要明確人工智能的知識創造、傳播和應用貢獻度。因此,成果應用維度應側重衡量人工智能創新成果的場景使用即技術轉化情況,測評指標設計要考慮相關研究成果的生產轉化或消費場景轉化。測度內容可歸納為應用轉化與產智融合兩個二級指標。
四是創新實踐,指人工智能發展的投入產出。投入與產出作為人工智能技術發展過程的重要一環,其資源投入多少會直接影響人工智能發展水平,且人工智能技術產出又是人工智能發展水平狀況的直接表現。換言之,即可通過資源投入來考核產出大小,借此判斷人工智能發展水平?。因此,創新實踐維度應更側重測度人工智能創新實踐的投入產出,測評指標設計則要考慮社會創新參與主體、實際創新投入及經濟產出情況。測度內容可歸納為創新主體、創新投入與創新回報等三個二級指標。
(二) 指標選取原則
結合人工智能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構建思路,本文立足于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與指標測度的有效性,圍繞我國各地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基礎,提出以下三級指標的選取原則。
一是匹配性原則,即三級指標需要與測評內容相匹配。一方面,各維度指標需要與相應二級指標測評內容相匹配,支撐二級指標的測評目的;另一方面,三級指標作為測度指標體系的基礎層,內容設計需要考慮與現實社會活動的匹配性。
二是適用性原則,即三級指標需要適用于我國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一方面,考慮到指標體系的測度范圍,要求三級指標需要適用于我國宏觀層面及省域中觀層面;另一方面,考慮到人工智能發展的技術特征,要求三級指標選擇需要能適用人工智能軟硬件結合的技術特點。
三是可獲得原則,即三級指標測度所需數據可以通過搜集整理獲得。鑒于人工智能仍處于早期階段,很多數據尚未進行有效統計,因此,測度指標選擇的一個重要原則為測評數據的可獲得性。一般來講,數據來源于政府部門公開發布的網站或者社會認可的權威機構,如《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指數》等;但部分難以獲得的指標數據可采用互聯網數據處理技術、擬定算法進行抓取與解析。
(三) 指標體系
盡管目前學術界對如何構建人工智能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尚未形成一致結論,但相關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結合前文人工智能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構建思路與指標選取原則,本文借鑒《中國成長型AI企業研究報告》 《2021 人工智能發展白皮書》 《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20》 《中國區域科技創新評價報告2020》等及相關指標體系,設計了包含4 個維度(一級指標)、10 個二級指標與32 個三級指標的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具體指標內容如表1 所示。

表1 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
由于不同指標的度量單位存在差異,因而在后續測度計算過程中需要對相關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本文測度的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及各省《統計年鑒》等,部分指標數據來源于《自主創新年度報告(2012)》等學術成果。
四、 測度應用分析
為了更好地開展數據搜集與分析工作,確保采集的數據能夠科學有效地反映測度對象的真實情況。本文將根據前面的指標體系設計,對指標體系的特征與適用性進行闡述,以便指導所設計的指標體系在后續人工智能測度研究中得到合適的參照與應用。
(一) 指標體系特征
本文提出的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的測度范圍涵蓋了整個人工智能領域,具有覆蓋面廣、指標數量少、客觀性強等特征。具體來看:第一,基礎層即第三層級的指標覆蓋面廣,基本涵蓋了人工智能領域的宏微觀環境、技術創新、創新應用及產出回報等全生態鏈條;第二,指標數量精簡,指標設計充分考慮了測度相關性,不以指標數量多少衡量指標體系的全面程度,以降低測度工作難度;第三,不設計主觀評價指標,全部指標體系均可通過第三方數據庫獲取數據,以增強評價工作的客觀性。
(二) 適用性分析
從地域范圍看,本文構建的指標體系主要圍繞區域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需要展開,空間適用范圍較廣,既可用于國家層面的發展水平測度,也可用于區域、省域、都市圈以及大都市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在指標體系使用過程中,結合地域具體情況,可對指標體系部分內容進行數據替代,但不建議減少指標數量。從時間范圍看,本文構建的指標體系較適用于年度發展水平測度,考慮到動態變量影響,部分指標可采用年末靜態時點數據作為年度測度數據。總體來看,本文構建的指標體系適用于宏觀的區域性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而不是適用于微觀的行業發展或企業技術發展測度。
(三) 權重測算工具
關于三級指標體系的權重確定問題,逐步分化為基于截面數據的靜態綜合測度與基于面板數據的動態綜合測度。對于截面數據,常見方法是因素分析法和熵權法。其中,因素分析法是通過因子分析法或主成分法計算指標權重,而熵權法則常用于計算分項權重,近年來相關研究中也較多采用此類方法。對于面板數據,常見方法為縱橫向拉開檔次法,即針對時序立體數據的動態測度方法,基本原則為最大化立體數據來體現各評價對象之間的差異,采用求解非線性規劃問題思路來逐層確定指標權重,利用指標權重測度各區域人工智能發展的評價指數。在指標體系實際應用中結合數據搜集,進一步確定采用的權重計算方法。
五、 結語
本文從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研究現狀入手,借鑒學術界現有的研究成果與思路,構建了適合我國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的指標體系。綜合來看,本文主要有如下學術貢獻:第一,圍繞人工智能發展構建了適用于中國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的指標體系,其中三級指標32 個,覆蓋面較廣,彌補了國內關于人工智能發展研究局限于理論推演的缺憾。第二,從測度對象分析入手,確定指標體系構建的思路與指標選取原則。其中,匹配性、適用性與可獲得性三大原則的確立,為人工智能發展水平測度工作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視角。第三,本文提出的“三層四維”指標體系為人工智能的相關實證問題的測度計算奠定了基礎。
注釋:
①曹靜、周亞林:《人工智能對經濟的影響研究進展》,《經濟學動態》2018 年第1 期。
②陳楠等:《人工智能影響就業的多重效應與影響機制:綜述與展望》,《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21 年第11期;蔡躍洲、陳楠:《新技術革命下人工智能與高質量增長、高質量就業》,《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 年第5 期。
③陳彥斌、林晨、陳小亮:《人工智能、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經濟研究》2019 年第7 期。
④郭凱明:《人工智能發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與勞動收入份額變動》,《管理世界》2019 年第7 期;程承坪、陳志:《人工智能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機理——基于理論與實證研究》,《經濟問題》2021 年第10 期;王瑞瑜、王森:《老齡化、人工智能與產業結構調整》,《財經科學》2020 年第1 期。
⑤陳利鋒、鐘玉婷:《人工智能發展的宏觀經濟效應:動態隨機一般均衡視角》,《上海金融》2020 年第1期;黃旭、董志強:《人工智能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提升?》,《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9 年第11 期;程惠芳、陸嘉俊:《知識資本對工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實證分析》,《經濟研究》2014 年第5 期。
⑥1??李旭輝等:《三大支撐帶人工智能產業自主創新能力測度分析》,《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0 年第4 期。
⑦郝力曉、呂榮杰:《人工智能影響工資水平的機理研究》,《工業技術經濟》2021 年第11 期。
⑧顧國達、馬文景:《人工智能綜合發展指數的構建及應用》,《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1 年第1 期。
⑨ [美]斯圖爾特·羅素、諾文:《人工智能:一種現代的方法》第3 版,姜哲等譯,人民郵電出版社2010版,第1—11 頁。
⑩韓民青:《論習近平科技思想的理論創新》,《東岳論叢》2017 年第4 期。
?李旭輝、鄭麗琳、程靜靜:《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創新驅動發展動態評價體系研究——基于二次加權動態評價方法》,《華東經濟管理》2019 年第3 期。